《神醫魔后》 第621章 蘇原祭司的手段
銀子跟北齊的宮說:“聽聞北齊的新君還未大婚,那想來后宮也沒有妃嬪了。”
宮點點頭答道:“您說得沒錯,如今后宮就兩位太后管著,還有一些先帝的太妃們也住著,只不過都住在相對偏遠之,一般況下是不會出來走的。”
銀子點點頭,“等我們休整一番,便去拜訪拜訪太后娘娘吧!”
宮笑笑沒說話,倒是夜紅妝對拜訪太后一事生出了期待。特別想見到李太后,想看看李太后如今是個什麼態度,也想弄清楚李太后到底知不知道現在的六殿下是假的。
如果不知道,那就能跟李太后站在同一條戰線上。
如果李太后知道,那就得弄清楚現在這個六殿下跟真正的六殿下到底是什麼關系,也得弄清楚李太后是決定放棄以前那個兒子,還是依然想念著以前那個兒子。
手里還有一張王牌,是被夜飛舟藏起來的那個懷孕的子。蘇原太子救下之后并未直接進臨安城,而是拐了道往夜飛舟藏人的莊子里去了。那莊子在哪里夜紅妝早就跟夜飛舟問了出來,如今人已經被蘇原太子控制住,放在一個的地方,隨時等著去用。
那是真正的六殿下唯一的孩子,只要李太后還想念著那個兒子,就不可能對那個孩子無于衷。只等著那子把孩子生下來,再與李太后好好談談。
據宮說,客居的宮院已經快到了,再往前走一段路,拐個彎就能進客居宮的巷子。
而就在這時,夜紅妝看到了一個人,那人雖也是丫鬟,但卻沒穿宮服飾。因為不是皇宮里的丫鬟,而是一品將軍府四小姐邊的近侍。
夜紅妝心里犯了合計,墜兒怎麼會在這里?難不夜溫言進宮了?
Advertisement
開始發慌,雖然已經易了容,還照過鏡子,是在確保連自己都不認得自己的況下才安心進宮的。可是只要一想到夜溫言也在宮里,就控制不住地害怕。畢竟如今那夜溫言的手段已經不同于凡人,帝尊大人給了太多超乎尋常的本事,已經斗不過夜溫言了。
走在前面的銀子突然停了下來,轉回頭看了夜紅妝一眼,又順著夜紅妝飄忽不定的目看向不遠正在行走的墜兒。領路的宮走著走著就發現后頭沒有人跟著了,也停下來回頭問道:“怎麼不走了?是不是想歇歇?也是,北齊皇宮很大,雖然奴婢沒去過蘇原,但也聽說過蘇原國土不多,想來姑娘是沒走過這麼遠的路,那咱們就停下來歇歇。”
銀子冷哼一聲,以此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卻也沒有同一個宮計較太多,只是朝著墜兒所在之指了指,“不是說后宮里沒有年輕主子麼?總不能那個十幾歲的姑娘,是北齊先帝留下來的小妃子吧?早聽聞北齊皇帝后宮佳麗三千人,想必那姑娘也是其中一個。”
小宮聽得直皺眉,立即糾正道:“所謂后宮佳麗三千,不過就是那麼一說,怎麼可能真的有三千人,請姑娘不要把蘇原人的喜好代到北齊這邊來,我們跟你們那是不一樣的。至于您說的那位姑娘,可不是后宮主子,是外面邸里的丫鬟。”
“丫鬟?”銀子不解,“何以邸的丫鬟都能隨意在宮中行走?”
宮又道:“因為是一品將軍府四小姐的近侍丫鬟,四小姐是未來帝后,將來也是要住進炎華宮的,所以的人行走在宮中很正常,就像炎華宮的宮人也會在宮里行走一樣。”
“哦。”銀子點了點頭,也算是理解了夜紅妝的恐慌。但是并不打算回避這份恐慌,反而是沖著也往這邊看過來的墜兒招了招手,“姑娘,過來說話!”
小宮急了,“您這是干什麼呢?您是客人,客人就該守客人的禮數,奴婢現在是領您到客居宮去休息,怎麼您還反客為主,隨隨便便人說話?”
銀子冷哼,手往小宮的手臂上拍了拍,“你別急,我只是與人說說話,不礙事。”
小宮也不怎麼的,就是被這麼一拍,竟也覺得不礙什麼事,連帶著態度都了下來。甚至還幫著沖墜兒喊了一聲:“墜兒姑娘,您來一下,我們與您說說話。”
對墜兒說話是很客氣的,可雖然客氣,卻還是幫了銀子的忙。
墜兒不明所以,納悶地走了過來,才走一半就覺出不對勁。因為銀子散過來一種味道,正是之前在宮車里與那輛奇怪的馬車肩而過時,順著窗子飄進來的那種香味兒。
想起夜飛舟和三殿下說的話,蘇原人。再看看不遠那個銀子,深目高鼻,明顯不是中原人的樣子。原來這就是蘇原人?可蘇原人干什麼?
朝著對方走過去,一直走到那銀子跟前,毫不畏懼地將仔細打量,同時也打量起后跟著的兩名侍。那兩名侍也同銀子有一樣的外貌特征,只是其中一人眼窩陷得沒有另一人那麼深,看起來平和許多,上的味道也更淡一些。
這是第一次見到蘇原人,只除了樣貌與北齊人不同之外,倒也看不出其它問題來。
看過之后,墜兒沖著們俯了俯,禮貌地道:“雖不知尊駕是何人,但還是要問聲好。”
銀子沖著笑笑說,“我是蘇原國的大祭司,人們都我阿蔓。”
墜兒微微詫異,但還是又問了一聲:“大祭司好。”
阿蔓點頭,也不客套,開口就問:“聽聞你是一品將軍府四小姐的近侍丫鬟?怪不得沒穿宮人的裳。夜四小姐如今名滿天下,人人皆知是帝尊大人親點的未來帝后,也人人皆知是臨安第一人,不知阿蔓能否有幸見上一面。這位姑娘,夜四小姐也在宮里嗎?”
墜兒聽著阿蔓說話,也不怎麼的,竟一點點的從最開始的排斥,到后來的逐漸接。看著阿蔓的眼睛,越看越覺得這阿蔓生得實在是很好看,特別是配上這一銀閃閃的子,就像一位仙子,讓人總忍不住想要親近,想多看幾眼。
阿蔓還在沖著笑,越笑墜兒就覺得好,越笑就越覺得自己有一肚子話想要和說。可是這種念頭剛剛興起,又立即被一大力給推了回去,有一瞬間的清醒,雖然很快又陷到阿蔓的世界里,卻也再沒有興起想要跟阿蔓說很多很多話的念頭。
不過對于阿蔓先前的問話,還是做了回答,說:“我家小姐并不在宮里,只有我一人進宮,是跟著炎華宮的連時公公一起進來的。剛剛往虞太后那里去了一趟,這會兒正要回炎華宮去。不知蘇原的大祭司,您我過來是有何事?”
阿蔓笑著說:“也沒有什麼事,就是見姑娘比其它宮人特別,心生好奇,便你過來說說話。或許這就是緣分吧,幾句話間我竟覺得與姑娘十分投緣,不知姑娘愿不愿意隨我一起到客居宮去坐坐,喝盞清茶,閑聊幾句。我們初來乍到,有許多北齊的規矩禮節都不懂,姑娘若不嫌煩,便與我說上一說,也省得我在宮里這幾日因不懂禮數而做了丟臉的事。”
墜兒聽了這話立即點頭,“很樂意為您效勞。”
說完,跟著阿蔓一行人就往客居宮走了。那個領路的宮毫沒有覺得不妥,倒是夜紅妝心頭大駭,沒想到蘇原人竟這麼厲害,幾句話間就把這墜兒給迷了魂,竟是說什麼都聽了。
可太知道墜兒對夜溫言的忠心程度了,如果蘇原這個大祭司能有辦法讓墜兒反水,從墜兒口中套出話來,那麼們將得到很多有價值的信息。
只是還沒想明白,這個阿蔓到底是用了什麼手段控制的墜兒?總不能說幾句話就能讓人服從吧?那這天下豈不是要任行走了?這豈不是堪比帝尊的本事?
款待蘇原太子的午膳還在繼續,墜兒跟著阿蔓去客居宮了,此時的夜溫言跟師離淵二人正一步一步的往山下走,對于京中之事全然不知。
而此時在臨安城里,也有一十分熱鬧,那就是肅王府。
夜家二小姐帶著五小姐上肅王府了,這事兒已經讓城的人談論了一上午。且不只是閑在家中的眷們談論,連那些今日不上朝的老爺們也參與其中,紛紛開始分析為何一直沒什麼關注度的夜二小姐,竟也竄到了大前方,開始討伐肅王府了。
這事兒還得從今日清早說起。
已經變夜連綿的夜四小姐,一大清早就把夜楚憐從被窩里給挖出來了,盯著洗漱換,換完裳就給拽出了東宅,早飯都沒讓吃就直奔著肅王府去。
夜楚憐心里那個苦,想說昨晚上我就沒吃飯,今早你還不讓我吃飯,這位姐姐你該不是剛復活就想把我給整死吧?的命怎麼這麼苦,以前心心念念的想跟四姐姐一起玩,四姐姐都不帶。現在不想跟這個不知道四還是二的姐姐一起玩了,可為啥甩都甩不掉?
猜你喜歡
-
完結810 章
鳳謀天下:王爺為我造反了
「我雲傾挽發誓,有朝一日,定讓那些負我的,欺我的,辱我的,踐踏我的,淩虐我的人付出血的代價!」前世,她一身醫術生死人肉白骨,懸壺濟世安天下,可那些曾得她恩惠的,最後皆選擇了欺辱她,背叛她,淩虐她,殺害她!睜眼重回十七歲,前世神醫化身鐵血修羅,心狠手辣名滿天下。為報仇雪恨,她孤身潛回死亡之地,步步為謀扶植反派大boss。誰料,卻被反派強寵措手不及!雲傾挽:「我隻是隨手滅蟲殺害,王爺不必記在心上。」司徒霆:「那怎麼能行,本王乃性情中人,姑娘大恩無以為報,本王隻能以身相許!」
150.5萬字8 82602 -
完結1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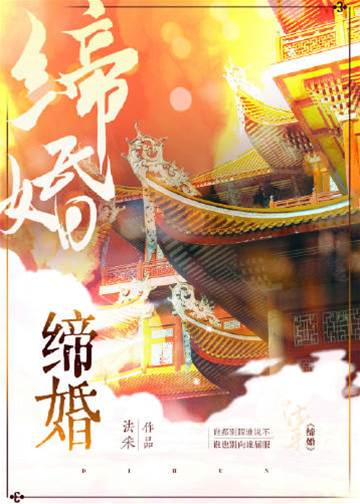
締婚
家敗落之後,項家老爹成了人人喊打的奸佞,項宜帶著幼年的弟妹無依無靠、度日艱難。 她尋來舊日與世家大族譚氏的宗子、譚廷的婚約,親自登了譚家的門。 此事一出,無人不嘲諷項家女為了算計、攀附譚家,連臉面都不要了。 連弟弟妹妹都勸她算了,就算嫁進了譚家,...
45萬字8.33 82137 -
完結136 章

重生之窈窈再愛我一次
謝令窈與江時祁十年結發夫妻,從相敬如賓到相看兩厭只用了三年,剩下七年只剩下無盡的冷漠與無視。在經歷了丈夫的背叛、兒子的疏離、婆母的苛待、忠仆的死亡后,她心如死灰,任由一汪池水帶走了自己的性命。 不想再次醒來卻發現自己回到了十七歲還未來得及嫁給江時祁的那年,既然上天重新給了她一次機會,她定要選擇一條不一樣的路,不去與江時祁做兩世的怨偶! 可重來一次,她發現有好些事與她記憶中的仿佛不一樣,她以為厭她怨她的男人似乎愛她入骨。 PS:前世不長嘴的兩人,今生渾身都是嘴。
27.1萬字8 266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