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王追愛:萌妃輕點寵》 第四百八十九章 火焱的勝利
祁耀一邊想,一邊在不經意間蹙起眉頭,冰冷的話語在慕容輕舞的耳邊響起:“你是不是激錯了人?火焱是在我的命令下才一路保護你摘草藥的。”
慕容輕舞抬頭看著這個不按常理出牌的男人,正常況下,他不是應該關心眼前的戰況嗎?他跟自己在這較什麼真?
看著慕容輕舞的眼中溢滿了驚訝和匪夷所思,祁耀正解釋,卻聽王英在旁邊縷著胡須傲地說:“姑娘說的不錯,那兩只鉗的確連通著金蛙背后的毒腺。”
祁耀抿著的雙微不可察的翹起了一弧度,眼神中流出了一譏誚,心想:“看在老東西還算忠實的份上,讓火焱多玩一會吧。”
祁耀背手而立,冰冷的眼眸注視著前方的戰況,不咸不淡地問王英:“金蛙除了這對鉗和毒素還有什麼過人之嗎?”
王英用那渾濁的眼眸看了祁耀一眼,面對男人深不可測的實力,他聰明的只會驕傲的展示自己的養蛙絕技,卻絕不敢對他不恭不敬。
王英看著前方一時難分勝負的戰況,不清祁耀的用意,但還是誠實地說道:“金蛙的可以隨著周圍的環境而變。”
祁耀聽了王英的話,面上依舊冷漠,沒有一多余的表,仿佛沒有聽到王英的回答。
慕容輕舞的眼眸中染上一抹疑心想:“難不金蛙的祖上還是變龍?到底是苗疆的制蠱手法改變了青蛙,還是金蛙本的種屬就與普通青蛙不同呢?”
老頭子一邊憂心忡忡地看訓練場中火焱和金蛙的決斗,一邊悄悄地和老婦人探討:“這金蛙也算有點本事,可以與火焱打個平手。”
老婆子雖然不了解火焱和金蛙的實力,可這麼多年照料祁耀,讓對祁耀多了一份了解,趴在老頭子耳邊悄聲說“看主連一眼神都沒有變化,明顯就是想讓火焱玩玩的。”
Advertisement
老頭子聽了老婦人的話,不由瞪大了雙眼,質疑老婦人道:“這麼大的手筆,只為讓火焱玩一玩?”
老婦人鄙夷地看了老頭子一眼,堅定不移地說道:“主和火焱多年未見,也想著看看它的實力唄,順便再讓火焱吞個金蛙也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事。”
老頭子聽了老婦人的話,冷汗直流,心中暗想:“復出主的腹黑真是更勝過從前啊,他之前的表現讓心隨侍的自己和老婆子都為火焱擔心不已,但王家卻沒有毫流出一反叛之心,看來這王英也是一只老狐貍。”
與老頭子的心思不同,老婦人的目從前方的決斗現場,慢慢轉移到了與祁耀并肩而立的人上。
只見子一淡藍的衫,翠綠的玉釵輕輕挽起了烏黑如墨的秀發。
的雙眸似乎盈滿了一汪清泉,卻又帶著淡淡的冰冷與輕愁。
似乎能看一切,卻又偏偏沉靜、斂,不多說一句話。
老婦人心中不由暗嘆:“真是一個妙人,如果能和主湊一對真是再好不過了,只是這子的心卻似在別。”
察覺到老婦人對邊子的打量和窺視,祁耀淡淡朝老婦人掃了一眼,那眼神雖然不顯山不水,卻飽含威和震懾。
老婦人乖順地低下了頭,徹底放下了暗害慕容輕舞的心思:“既然主心意已決,自己便不好自行其事了,大不了屆時幫助主留下。”
中午時分,驕似火,火焱和金蛙整整爭斗了一上午。
祁耀對金蛙和火焱的實力心知肚明,轉頭看著邊明顯擔心火焱,變得要沒有耐心的人,冷聲吩咐道:“讓金蛙亮出絕技吧。”
王英看著一淡定從容,一點不為猩紅大蛇擔憂,還繼續吩咐金蛙進攻的男人,默默了頭上的冷汗心想:“幸虧自己沒有對他不恭順啊,看來這圣實力果真深不可測啊。”
慕容輕舞聽了祁耀的吩咐,恍然明白自己之前都白擔心了,心中暗惱。
此時,祁耀低沉暗啞的聲音卻在慕容輕舞的耳邊悄悄響起,充滿了極致的:“金蛙的毒一定是你想要的東西,它可以解百蠱。”
慕容輕舞震驚地朝男人去,只見他早看向了訓練場中的決斗,似乎剛才的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慕容輕舞的心中雖然有著對祁耀的話的質疑,但又深深相信著,古語有云:“世間萬事萬,相生相克。”金蛙有著至毒的毒腺,能對所有的蠱毒起制作用,也在理之中。
王家的家主王英吹響了長笛,笛聲尖銳,清亮,一聲急過一聲,一聲比一聲高。
祁耀修長、瘦削的手也從懷中掏出了一只翠綠的簫,但他卻沒有著急吹響,而是不不慢,饒有興趣地看著金蛙的表現。
只見金蛙伏地,肚皮一鼓一鼓的,周的皮瞬間變了,一眼去竟不知金蛙去了哪里。
王英的長笛聲越發的嘹亮、急促,金蛙卻讓人無跡可尋。
突然慕容輕舞發現了火焱的背后出現了三道褐的短短的條紋,再一細看那里還有一個小山般的凸起,原來金蛙早已趴到了火焱的背后,而且還變了與蛇一般的猩紅。
慕容輕舞看著面前男人的運籌帷幄,雖然料定了火焱不會輸,但也不自地為它了一把汗。
苗疆蠱毒最是狠毒,而讓人束手無策,而這只金蛙還貌似是毒的佼佼者,不知火焱不小心中了金蛙的毒會怎樣?
一旁王英的心緒卻不似祁耀的淡定沉穩,更不似慕容輕舞的憂心忡忡,他的額上不可控制的冷汗直流,只有他知道金蛙在變的時候,毒腺的顯現其實意味著這幾條毒腺早已崩潰,里面已經沒有毒的蓄積。
王英用笛聲控金蛙釋放了三次毒素,而且他也確定金蛙的毒素注了火焱的,可是火焱至今卻屹立不倒,這樣的結局讓王英的心中被恐慌占據。
王英的氣息有點不穩,他停下了笛聲,眼神膽戰心驚地看著祁耀,目掃過男人手中的簫。
祁耀涼涼的看了一眼王英,云淡風輕的態度配上俊的外表,仿佛天邊的謫仙降臨人間,可他說出話,讓王英差點驚嚇地給祁耀跪了下去:“還有五。”
王英放下長笛,恭順地跪倒在祁耀的側,沒有了之前介紹金蛙時的驕傲,只剩下為金蛙求一條活路的滿腔熱,他老淚縱橫地請求道:“主,這只金蛙與我從小一起長大,如兄弟。如若不是主吩咐,我都不會把它派出來應戰啊,請主手下留,放它一條生路。”
祁耀冷峻的眼神劃過了一不可置信,他踢了一腳王英,蔑視地問:“你養蛙一生,難道不知道毒腺就是蠱蟲的命脈?毒腺一毀,即使活著也是茍延殘,相信你的另外幾只金蛙也不會放過它。”
此時的王英沒有了之前的恭順、膽小,只剩一份悲戚:“我知道,只是我與它從小長大,還念著那份……”
祁耀抿住的輕佻,眼神中浮現出一抹了然,嘲諷地道:“不如用它的一毒腺,換你剩余的兩只金蛙,你看如何?”
王英聽了祁耀的話,震驚地愣住了,他呆呆地看著面前猶如神祇的男人,面容苦,眼神悲戚,艱難地從地上爬起,絕地吹響了手中的長笛。
待金蛙上的八條毒腺全部顯現,祁耀也在第一時間吹響了手中翠綠的簫,簫聲圓潤,厚重,沒有笛聲的尖銳,但也聲聲耳,讓人到一風雨來風滿樓的氣息。
火焱聽到祁耀的簫聲,豎瞳展現,猩紅的蛇信快速地發出“沙沙”聲,一記漂亮的蛇擺尾就輕輕松松地把金蛙摔落在地。
金蛙失去了傍的毒腺,又遭到火焱的重創,恐怕兇多吉了。
王英顧不上對它的憐惜和哀痛,在他的心中用一條金蛙的命換回剩下的兩只金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
他聰明地恭順地再一次跪倒在祁耀的面前說:“王家謝主,保留王家基。”
此時的慕容輕舞和王家眾人才真真切切地到火焱的實力,明明白白到火焱之前對金蛙的戲弄和輕視。
慕容輕舞看著面前做小伏低地男人,心中暗嘆:“能能屈,識大局也為一個人。”
祁耀的冰眸著訓練場上小小的金蛙軀,想起它對于王英的意義,不無慨地說:“失去毒腺雖生猶死,不如給它一個痛快。”
王英聽了祁耀的話,心中明了這只被自己奉若珍寶的金蛙是被火焱輕而易舉地摔死了……
王英的心中沒有多怨言,他深知祁耀說的話深有道理,沒有毒腺的金蛙死了反而比活著痛快,他深深地趴在了地上,久久沒有起。
回到房間,老頭子嘆服地吹起祁耀的馬屁:“主的這一招,用的妙極,此后王家肯定誠惶誠恐、鞍前馬后誓死追隨主。”
猜你喜歡
-
完結3392 章
女神夫人別想離婚
超颯女霸總宋初九穿越了,穿越到一個慫包的身上。身邊不但多出了一個渣男老公,還有一個狗皮膏藥似的綠茶白蓮花。宋初九變身全能女神,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手撕小三,狠虐渣男,將曾經傷害過她的人全都狠狠踩在腳下。然而,這個男人怎麼回事,說好的渣破天際呢?她當著渣男老公的麵,狠狠打臉綠茶白蓮,渣男老公卻一把握住她的手,關切的問道:“手打疼了冇有?”她又欺負了渣男老公白月光,挑釁道:“你的白月光被我欺負了。”渣男老公卻一把將她拉入懷中:“你纔是我的白月光。”她忍無可忍,“我要和你離婚!”男人將她按在牆上,貼近她耳畔低沉道:“想離婚,這輩子都冇有機會了。”
297.9萬字5 92061 -
完結5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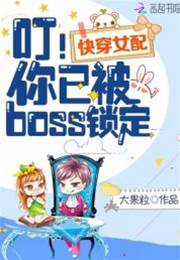
快穿女配之你已被boss鎖定
阮綿綿隻想安安分分地做個女配。 她不想逆襲,也不想搶戲,她甘願做一片綠葉,襯托男女主之間的純純愛情! 可是為什麼,總有個男人來攪局?! 阮綿綿瑟瑟發抖:求求你,彆再纏著我了,我隻想做個普通的女配。 男人步步逼近:你在彆人的世界裡是女配,可在我的世界裡,卻是唯一的女主角。 …… (輕鬆可愛的小甜文,1v1,男主都是同一個人)
103萬字7.83 14294 -
完結752 章
太後孃娘今天洗白了嗎
(雙潔、甜寵、1v1)沈紅纓玩遊戲氪金成癮,卻不曾想穿到了自己玩的古風養崽小遊戲裡……成了小皇帝崽兒的惡毒繼母當朝太後,十八歲的太後實屬有點牛批,上有忠國公當我爹,下邊宰輔丞相都是自家叔伯,後頭還站了個定北大將軍是我外公!氪金大佬穿成手掌天下權的惡毒太後,人人都以為太後要謀朝篡位,但是沈紅纓隻想給自己洗白設定好好養崽,誰曾想竟引得宗室藩王癡情追隨,忠臣良將甘拜裙下;莫慌,我還能洗!容恒:“太後孃娘要洗何物?”沈紅纓:“……洗鴛鴦浴?”【小劇場片段】人人都說國師大人聖潔禁慾不可侵犯。卻見太後孃娘勾著國師大人的下巴滿目皆是笑意道:“真漂亮,想要。”容恒:……世人咒罵太後惡毒,仰仗權勢為所欲為。後來,燭火床榻間那人前聖潔禁慾的國師大人,如困獸般將她壓入牆角啞聲哀求:“既是想要,為何要逃。”【禁慾聖潔高嶺之花的國師x勢要把國師撩到腿軟的太後】
66.3萬字8 61973 -
完結42 章

反派:皇爺爺,我要造反!
謝恒宇穿越到一本曆史小說裏,但他的身份不是主角。爺爺是開國皇帝。父親是當朝太子。作為皇太孫,未來的皇位繼承人。自己卻選擇一個看不上自己的假清高女主。親眼見證男主篡位成功,取代自己登上皇位,和女主鸞鳳和鳴!好!既然自己是反派,何不將反派進行到底。女主不要退婚嗎?男主不是要造反嗎?退婚要趁早。造反也要趁早!趁著男主還沒有崛起的時候,謝恒宇毅然走上了天命反派的道路,在造皇爺爺反的路上越走越遠。
7.7萬字8.18 12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