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書后我推倒了暴躁男二》 第195回:侯府要逆流而上
又至互市大集日,丁易一大清早就帶領手下人在邊境集市里巡查。
手下們均有些萎靡不振,打眼過去,總覺他們缺點潑皮的蠻橫勁兒。
丁易自己也是勞筋苦骨的,近來委蛇在建晟侯府、邊軍和錦縣各方勢力之間,他是累壞了子碎了心。敢“從良”真他娘的難!
張昆自長街另一端蹬蹬蹬跑到丁易旁,先是哈腰作揖,接著從懷里掏出兩張熱乎乎的卷大餅。
“爺,是延邊街老陳家的,小的順路買了來,還熱著呢。”張昆說著塞進丁易手中。
丁易還真沒來得及吃朝食,也沒跟張昆客氣,舉起來便咬下一大口。
“味道還吧?”張昆跟著丁易,笑嘻嘻地問道。
丁易腳下步伐未停,里大口大口的嚼著,說:“你真給人家錢了?”
張昆一個勁兒點頭,道:“給了,給了呀!依著丁爺的吩咐,咱現在可是遵紀守法的大良民。”
丁易滿意地笑了笑,手中的兩張卷大餅沒一會兒的工就都下了肚。
眾人在一米鋪門臉前停下腳步,丁易瞧了兩眼上面的招牌,方知這家米鋪屬于夏家控的。
“爺,今兒這大集,這一溜米鋪大抵都不會開門做營生。他們都是串通好了的,現在價格故意得低,誰家開門誰家就會被人瘋搶,不賠個都走不出這集市。”張昆在旁嘆道。
“前面不是還開了兩家麼?”另一手下指向前方,說道。
張昆扭頭翻了那手下一眼,說:“老牛啊老牛,這些日子你是白去常老板地里干活了。怎麼著,挖土豆挖傻了?還沒緩過乏來嘛?”
前面開門的兩家米鋪,分別在集市長街的兩側,一面是東野的,一面是北黎的。東野那家與其說是米鋪,倒不如說它是雜貨鋪,售賣粟、麥的同時,還賣些東野特產,比如各種風干的野。
Advertisement
這些食賣的偏貴,比較錦縣這邊的有錢人家青睞,畢竟北黎有,以稀為貴嘛。
那家鋪子算是東野最屹立不倒的一家,關于它有不傳言,最扯淡的一則便是:它背后的老板是東野皇室員。
丁易不信那些,不過這家鋪子極為低調,屬于悶聲賺大錢的那種,在東野眾商戶里極為見。
“大赤虎。”丁易了下,念出那家鋪子的名字。
在大赤虎對面,便是他們的老朋友了。桑梓米鋪的分號就開在這里。
門面依舊不大,也沒正兒八經賣過糧食。是夏季那會兒丁易幫金生賃下的,那時候他們往集市這邊捯弄海魚。短短幾個月,賣出去不錢。
正是這份營生,讓丁易和手下眾人賺了不。大家見到了實惠,才心甘愿地“從良”,知道跟著常老板能喝酒吃。
算來算去,恐怕今日的大集里,北黎這邊只有桑梓米鋪開了門。丁易在心里把汗,這麼做,就算公然跟夏家唱反調板了。糧價定的又這麼低,保不齊真有人會來瘋搶,這一關,染到底要如何闖過去?
桑梓米鋪,金生挑簾進室中,為隋端來一壺滾熱的馬茶。
“侯爺來之前怎麼沒打個招呼?鋪子里也沒什麼能招待的。”金生倒了兩杯,一杯奉于隋,一杯遞給侯卿塵。
隋照舊易了容,坐在狹小的室里,覺兩條長都沒法子直。他吹了吹熱氣,飲下一口,說:“味道不錯,跟我之前在赤虎邑喝到的一個味兒。”
侯卿塵喝下一口后,卻有點喝不慣,他將杯子送回桌幾上,“需好好適應才行。”
隋側首笑道:“塵哥喝不慣便罷,有什麼可適應的?”
“我現在喝不慣,不代表以后喝不慣,說不定以后我會很喜歡呢。”侯卿塵了眼窗外,估著快到開市時間了。
侯卿塵斂住笑,沖金生正道:“捻指算算日子,東野那邊該有靜了。要是他們今日再不現,下一個大集便是在十日之后。十日,會有很多變數。我們不可能在東野這一棵樹上吊死。”
“這話是了,最近常有百姓登門買糧。我們借口稻谷還未來得及舂米,便薦他們買些土豆回去。土豆同樣易存放,一家囤個一二百斤,方可度過這個冬季。”金生一五一十地述道。
就算沒有東野,這些土豆的銷路也不愁。
“可與夫人定好價格?”隋喝下一整杯馬茶,與金生確認道。
金生欠應道:“夫人說對北黎百姓還按去歲的價格出售,對東野那邊就按去年的價格漲兩賣。”
“縣上百姓沒有怨言?畢竟現在的市價頗低。”侯卿塵追問道。
金生擺了擺手,解釋說:“如今糧食市價是低不假,可關鍵是幾乎沒有米鋪開門買糧啊。我們開門做營生,價格是比市價高些,但我們給的承諾是今年不漲價。”
“之后也不漲嗎?”
“夫人說了,不漲。”
金生恐侯卿塵沒弄清楚其中就里,又細細說來:“靠海那片荒地不在錦縣的丈量冊,那本就是一塊無法耕種的地方。”
“原來如此。”
“但苗刃齊怎麼可能便宜我們?雖說土豆大收的消息被咱們著,可那些存放土豆的倉庫都在明面上,苗刃齊想弄清楚產量也不是件難事。他本想按十五稅一要桑梓米鋪繳稅。”
“十五稅一?虧他想得出來。”
“可不,那意思還是照顧咱們呢,朝廷下發的策令可是十稅一。”
隋不不慢地說起話:“是康鎮站出來了吧?”
“侯爺英明,康將軍說咱們已為邊軍提供那麼多糧食,還繳什麼稅?這筆錢本來就是苗刃齊想貪囊中,被康將軍這麼一斥責,嚇得再不敢打主意。所以侯府是占了便宜的。”
侯卿塵頓了頓首,說:“侯府后面的田地沒有賦稅,靠海那片荒地咱們亦沒有賦稅。如此一來,怎麼賣,咱們都是穩賺不賠的。”
“正因如此,夫人才決定不漲價。我們要賺錢不假,但也得為侯府賺下好名聲。”
三人還在低語,米鋪外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敲鑼聲,大集開始了。
金生掀簾走出去,在柜臺前不聲地觀起來,心嘆,今兒這大集比平素的人流還。他心里不免有些焦急,幾位主子料想的到底準不準呢?
隋和侯卿塵都沒有著急,二人在不大的桌幾上鋪開棋盤。
隋執白,侯卿塵執黑。
下棋是侯卿塵的強項,隋以前連棋譜都看不大懂。要他老老實實地坐在棋盤前,一待就是半個時辰一個時辰的,他本坐不住,心里跟長了草似的。
是雙殘了之后,他才慢慢琢磨上。只是照比侯卿塵,還是遜許多。
侯卿塵拳抵邊咳嗦兩聲,見隋還沒有反應,只好手替他毀了一步棋。
“阿,下在這里,你就輸了。”
隋將那枚棋子又落回原,灑笑道:“輸就輸,悔棋算什麼本事。”
言落,卻見金生神惶然地跑進來,還沒開口言語,卻見侯卿塵抬了下手,示意他先不要講話。
其實這盤棋隋已敗局,但侯卿塵又妥妥地拖了一炷香的時間,才把最后那步棋給落下來。
隋心下明白,侯卿塵這是在替自己“擺譜”。
東野那邊定是來了人。
“是誰?”隋慢慢抬眼,問道。
“是松針,后還跟著幾個人。”
侯卿塵急忙道:“是男是?”
“是男子。”
隋面上沒有任何變化,不管凌恬兒出現與否,對他來說都沒甚麼關系。他視就如街上陌生人一樣。
反倒是侯卿塵稍稍出失之表,他是真想瞧瞧那位傳說中的蠻橫郡主。那凌恬兒就是再混賬,還能有清王殿下混賬麼?他自覺只要比不上清王殿下,他都能想到解決問題的法子。他一定要替隋解決掉那個大麻煩。
和松針同行的是郎雀,余下幾人便是隨行的扈從。他們皆作東野百姓裝扮,混跡在人群里也不顯得太突兀。
狹小的室再進來松針幾人后,便有些仄了。隋恣意地坐在圈椅上,侯卿塵則立在他后。
松針甫一見到隋,先是一怔,之后才笑起來,“叔叔,你怎麼又換模樣了?”
“看心。”隋微狹起眼,打量著松針和郎雀二人。
松針是與隋稔了,但郎雀卻覺得這屋子里涼意甚濃。隋給人一種強勢、迫的覺。在他手上死去的西祁韃子不計其數,郎雀想到這里,不由得打了個冷戰。
這樣的人被踩在泥淖里,還能從泥淖里爬起來,不為東野所用,就是東野的禍患。趁其羽翼還沒有滿之前,東野該早做打算。
以前郎雀不清楚隋和東野之間的淵源,因著這次過來購買糧食,他才斷斷續續知道些幕。國主怎麼就沒有把他說服呢?要是東野能有他這麼一位將領,還愁訓練不出一支勁旅?
眼前的松針就是最現的苗子,他只要把松針帶出來,松針以后必一員猛將。可惜他只管文班院,護衛府的事不在他的職責之。
郎雀向隋行了禮,之后退回到松針旁。
松針爽朗一笑,湊到隋跟前套起近乎,說:“叔叔,咱們雖說親兄弟明算賬,但……”
松針話猶未了,隋已臂將他推開。他不容置否地說:“不還價。”
猜你喜歡
-
完結1409 章
農門小醫妃
再次醒來,曾經的醫學天驕竟然變成了遭人嫌棄的小寡婦?顧晚舟表示不能忍受!直到……因緣巧合下,她救下生命垂危的燕王。他步步試探,她步步為營。亂世沉浮中,兩人攜手走上人生巔峰。
253.1萬字8.18 62446 -
完結609 章
神醫毒妃權傾天下
“本王救了你,你以身相許如何?”初見,權傾朝野的冰山皇叔嗓音低沉,充滿魅惑。夜摘星,二十一世紀古靈世家傳人,她是枯骨生肉的最強神醫,亦是令人聞風喪膽的全能傭兵女王。素手攬月摘星辰,殺遍世間作惡人。一朝穿越,竟成了將軍府變人人可欺的草包四小姐,從小靈根被挖,一臉胎記醜得深入人心。沒關係,她妙手去胎記續靈根,打臉渣男白蓮花,煉丹馭獸,陣法煉器,符籙傀儡,無所不能,驚艷天下。他是權勢滔天的異姓王,身份成謎,強大逆天,生人勿近,唯獨對她,寵之入骨,愛之如命。 “娘子,本王想同你生一窩娃娃,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實施?”某人極具誘惑的貼在她耳後。生一窩?惹不起,溜了溜了。
110.5萬字8 65819 -
完結585 章
小公主又幫母妃爭寵了
穿書成了宮鬥劇本里的砲灰小公主,娘親是個痴傻美人,快被打入冷宮。無妨!她一身出神入化的醫術,還精通音律編曲,有的是法子幫她爭寵,助她晉升妃嬪。能嚇哭家中庶妹的李臨淮,第一次送小公主回宮,覺得自己長得太嚇人嚇壞了小公主。後來才知道看著人畜無害的小公主,擅長下毒挖坑玩蠱,還能迷惑人心。待嫁及笄之時,皇兄們個個忙著替她攢嫁妝,還揚言誰欺負了皇妹要打上門。大將軍李臨淮:“是小公主,她…覬覦臣的盛世美顏……”
105.9萬字8 170382 -
完結492 章

春宴渡
她只是一個農家的養女,貧苦出身卻不小心招惹了一個男人,被迫做了人家的妾,她委曲求全卻也沒能換來太平安逸的日子,那就一鼓作氣逃離這個是非之地。她拼了命的逃離,卻在窮途末路之時,看到他,她本以為他會披星戴月而來,卻不想他腳踩尸骨,跨越尸海擋在自…
90.6萬字8 15285 -
完結546 章
王爺您的醫妃有點狂
穿越成丑顏農女,空間隨身,神泉在手,丑怕什麼?逆天異能為伴,芊芊玉手點石成金,真是太好了!趕娘倆出府的渣爹想認回她?門都沒有!她的夢想,是建立一支屬于自己的異能部隊,掠殺天下黑心狼,虐盡天下渣與狗!誰知,一朝風云變幻,她看上的男人,他要反-朝-庭,立-新-國!好吧,既然愛了,那就只有夫唱婦隨,一起打天下嘍!這是一個你做獵戶,我是農女,你做皇帝,我是女王,最終江山為聘,獨愛一生的暖寵故事!
102.8萬字8 58725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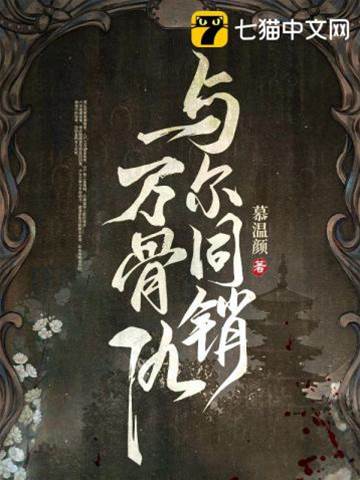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18 822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