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書后我推倒了暴躁男二》 第172回:就要你不得不服
且表隋抬就是一腳,直接將門簾下擺的木棒給踹斷了,生怕旁人不知道他那雙“殘”已變得有多麼強勁。
染被唬了一跳,自羅漢榻上直起,訝然地睇向他,說:“侯爺要干什麼啊?”
先前,隋沒能阻止住染去大興山和凌恬兒見面那次,他一時氣急,反手就把霸下洲的房門給敲出一條裂。即便事后修補好了,但那隙仍有跡可循。染心下郁悶,他是不是不破壞點東西就心里難?
隋卻不管那麼多,眸盯著染,見面泛紅,稍稍有些倦意,但絕對沒有哭泣的痕跡。他再定睛一瞧,方知是紫兒那個小丫頭跪在染腳邊搭搭地掉淚。
“沒事。”隋輕甩風袖,面容稍稍舒展開,“娘子先忙吧。”說著,就往東正房里走去。
侯卿塵和范星舒向染揖了揖,也隨著隋往里面走去。染重新坐回羅漢榻上,輕紫兒的頭頂,說:“這事咱們沒完,夫人定為你討回公道。”
紫兒瑟瑟地抬起頭,兩只眼睛哭得跟桃兒似的,蚊吶道:“夫人……”
夏日天長,已用過晚膳,外面的天際還沒有徹底落幕。隋手里握著一本書,從西正房那邊走回來。
“大今兒是怎麼了?跟丟了魂似的?是不是這兩日心里還記恨我呢?”
染坐在妝奩前,指揩過鬢邊的碎發,道:“我兒子才不那麼小心眼兒。”
隋挪來一把椅子坐到染旁,順著的纖指過鬢邊,承認道:“我是不會教導兒子,頭次當爹沒甚麼經驗。”
染側首瞟了他一眼,沒好氣地說:“一個你都教不明白,我看大本不用再添弟弟妹妹。”
“那怎麼能,一回生兩回!”隋急赤白臉地道,他捉住染的臂腕,“我們……”
Advertisement
染急忙把他推開,蹙眉道:“熱得慌……我有正事跟你說,你快坐好了。”
“什麼正事也抵不過給大添弟弟妹妹。”隋拉懷,“娘子啊……”
“你兒子被人欺負了。”染把他的臉推扭過去,“紫兒那丫頭讓那幾個混賬王八羔子占了便宜。”
隋臂彎一僵,眼眸里出兇,“怎麼回事?”
“這事兒我也有責任。”染從他懷里退出來,“大來府那陣兒咱們過得太窮,沒顧得上立什麼規矩章法的。無論是誰,都只喚那孩子一聲‘大’。知道的老人從不多問,偏我忘了咱們侯府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投奔。”
“是塵哥那幾個手下質疑大不是我兒子?”隋五指攥拳,指節里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
“我就是事先跟你打個招呼,若因此事得罪下侯兄長,侯爺得自己收拾爛攤子。”
隋倒是氣定神閑,只稍慍地說:“娘子為我收拾過多爛攤子?我不得替娘子收拾一回。”
染了眼窗外,見天已暗下來,便詼說道:“那侯爺過一會兒就隨我一同去看戲吧。”
過去不至二刻鐘,卻聽屋外傳來咚咚地腳步聲,須臾,鄧媳婦兒推門而,急聲道:“夫人,事了。”
染長舒一口氣,朝隋福了福,道:“侯爺,隨妾一并過去吧?”
隋頷首,跟著染一同走出霸下洲。鄧媳婦兒在他二人前引路,躬道:“就在后面稻田地里呢。”
“我認得路。”染走出垂花門,水眸瞥向金甲塢,“去里面支會侯卿塵一聲,他要是有意愿,你便帶他過去。”
隋已曉得染要唱哪一出了,他邊護著染走夜路,邊苦笑道:“娘子把事計劃的如此周,哪還有什麼爛攤子可言?我能表現什麼?我啊就是當背景的料。”
“調戲我的丫頭,我非錘死他們不可!”染咬了咬,以為自己義憤填膺得很。
可在隋眼里,他這娘子就算發火都是的,像一只小花貓似的。
紫兒很會挑地方,沒有鉆進稻田深,一是擔心那倆畜生再傷到莊稼地,二是怕寧梧等人未能及時趕到,再不容易逃。故而把地點定在那一排果子樹下。
老趙和大洋憋了兩日沒有得手,今日忽見紫兒主來找他們,樂得早忘了形,約好掌燈之后在侯府后面果子樹下見,便守時守點地趕過來。他們才將紫兒的影兒瞧清楚些,寧梧已帶著后院的媳婦兒、丫頭們把他們倆給合力圍住。
其實寧梧對付這二人簡直易如反掌,但染得做戲給侯卿塵看,不能讓侯卿塵覺得侯府在仗勢欺人。寧梧也是第一次和一群娘們兒做事,當們一窩蜂沖過去撕打老趙和大洋時,寧梧真想一頭撞進稻田地里。但又止不住地發笑,原來不靠打也能將人制伏。
“呸,你們這倆臭不要臉的貨,我們紫兒丫頭才多大,你們倆就起這個歪心思!”
“管不住自己的下流胚子,就應該剁了喂狗!”
“白眼狼!活畜生!”
大洋和老趙被們抓花了臉,上也是青一塊紫一塊的。起初二人死命掙扎,口里還不斷地狡辯。等到了后來,他們本說不出話,只知道護頭蹲地扛著一群娘們兒的拳打腳踢。
寧梧見染和隋走過來,終于下令讓大家住手。寧梧提著燈籠照亮他們,嘲諷地笑道:“侯爺和夫人來了,你們倆還不打算起來麼?”
大洋和老趙鬼哭狼嚎地匍匐過去,一口一個“是被那小賤人設計所害”,不斷磕頭說他們倆是被冤枉的。
與此同時,侯卿塵亦隨鄧媳婦兒快速趕過來。染余瞅見侯卿塵,終于掀道:“你們的意思是說,我們侯府上下這麼多雙眼睛都在說謊?們跟你們二人都有仇?紫兒是我兒子的婢,大晚上不在霸下洲里待著,竟跑出來要跟你們倆行茍且之事?”
“就是勾引的我們呀!夫人,你得明鑒,明鑒啊!”老趙和大洋二人憋屈到了極點,他們倆居然教一個小蹄子給算計了!
“紫兒。”染將喚到邊,問道:“你怎麼沒有待在霸下洲里陪大?”
“夫人!”紫兒撲通跪倒在地,眼淚汪汪地說,“如今是伏天屋中太悶熱,大要小的出來打些涼水回去子。可我才走出霸下洲就被這兩個混賬東西給捆住綁來,不然這黑燈瞎火的,我一個小姑娘干什麼要來這里?”
紫兒一面說一面嗚咽,匍匐到染腳邊,接著道:“他們倆明明就是信口雌黃,夫人,退一萬步說,就算是我讓他們倆來稻田地的,他們倆若是正人君子怎麼會來?更何況有這麼多嫂子、姐姐們為我作證!”
寧梧恰到好地走上前,欠道:“夫人,紫兒所言句句屬實。”
“那你是怎麼來的?”染刻意道,他這話就是問給侯卿塵聽的。
“鄧家的打發我過李老頭這邊問些事,大家都在后院里納涼,聽到有人喊救命,還是在咱們府的地盤上,自然要追出來相救。何況這丫頭還是咱們上院的人。”
“你們建晟侯府可真會算計人啊,這明明就是要坑死我們兄弟二人!”老趙和大洋跪爬到侯卿塵跟前,央及道,“塵爺,你快說句話救救我們吧,干脆這侯府我們不留也罷。塵爺,塵爺,咱們都是清……”
老趙快被氣瘋了,口上沒有遮攔,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差點說出“清王府”三個字。
侯卿塵早就看明白了這場戲,這分明就是染做的扣,大可以不用如此費盡周章。在知道老趙和大洋作出那些劣行之后,就可以以建晟侯府當家主的份懲治他們倆。
但染沒有這麼做,而是演了這出戲,來給侯卿塵一個代。這二人是他們自作孽不可活。侯卿塵及時踹了老趙一腳,他瞬間從口中迸出一口鮮,嚇得旁邊的大洋再也不敢多說話。
染有些意外的看向侯卿塵,他和隋不愧是兄弟啊,這咋出手都上腳呢?而且踹人的方式還很相同,要是范星舒此刻在場,只怕口又得一陣劇痛。
“你們倆還狡辯什麼?那丫頭才幾歲,你們倆是禽嗎?”侯卿塵真的太恨鐵不鋼了,他們僥幸逃命,來到建晟侯府放著安生日子不去過,非要往這種不恥行徑上走。
侯卿塵向染鄭重一揖:“夫人,請按侯府家法置他們二人,卿塵絕無半點怨言,是他們自己咎由自取!”
染斂眸緩笑,說:“侯兄長,你若相信他們是無辜的,咱們可以把這件事下來,黑不提白不提也可,這個面子我能給你。”
侯卿塵趕搖頭,繼而向一直一言不發地隋叉手道:“侯爺,這件事不是小事,一定要讓夫人按照侯府的規矩懲治,絕對不能姑息!”
隋當了一晚上的背景墻,終于到他說話了,卻倍無奈,他拭了拭濃的劍眉,道:“侯府大小事宜皆由夫人做主。”
這都快了隋的口頭禪,隔三差五就得講一遍,他能有什麼法子,這些規矩皆是他自己定下的。
染略略揚起下頜,擲地有聲地道:“既如此,把他們二人押回正院里,每人各打三十板子,以儆效尤!”
猜你喜歡
-
完結847 章

穿書後,我嬌養了反派攝政王
(章節內容嚴重缺失,請觀看另一本同名書籍)————————————————————————————————————————————————————————————————————————————————————————————————————棠鯉穿書了,穿成了炮灰女配,千金大小姐的身份被人頂替,還被賣給個山裏漢做媳婦,成了三個拖油瓶的後娘!卻不曾想,那山裏漢居然是書里心狠手辣的大反派!而那三個拖油瓶,也是未來的三個狠辣小反派,最終被凌遲處死、五馬分屍,下場一個賽一個凄慘!結局凄慘的三個小反派,此時還是三個小萌娃,三觀還沒歪,三聲「娘親」一下讓棠鯉心軟了。棠鯉想要改變反派們的命運。於是,相夫養娃,做生意掙錢,棠鯉帶着反派們把日子過得紅紅火火!後來,三個小反派長大了。一個是位高權重當朝首輔,一個是富可敵國的大奸商,一個是威風凜凜的女將軍,三個都護她護得緊!當朝首輔:敢欺負我娘?關進大牢!女將軍:大哥,剁掉簡單點!大奸商:三妹,給你遞刀!某個權傾朝野的攝政王則直接把媳婦摟進懷。「老子媳婦老子護著,小崽子們都靠邊去!」
145.2萬字8.33 120041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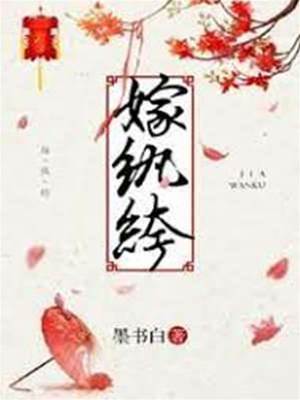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2012 章

戰神王爺是妻奴
一朝穿成被人迫害的相府癡傻四小姐。 從死人堆里爬出來,隨身攜帶醫藥實驗室和武器庫。 對于極品渣渣她不屑的冷哼一聲,迂腐的老古董,宅斗,宮斗算什麼? 任你詭計多端,打上一針還不得乖乖躺平! 絕世神功算什麼?再牛叉還不是一槍倒! 他,功高蓋世,威震天下的戰神王爺。 “嫁給本王,本王罩著你,這天下借你八條腿橫著走。” “你說話要講良心,到底是你罩我,還是我罩你呀?” “愛妃所言極是,求罩本王。” 眾人絕倒,王爺你的臉呢?
362.3萬字8 380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