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傾天下:夜王的小祖宗野翻了(月清音夜北冥)》 第270章 本王不能吃醋?
潤的熱氣呼出,在琉璃簪子上印出幾分薄霧,又緩緩消散而去。
月清音眼有些出神,似乎沒想到夜北冥讓把簪子取下來,免得扎到自己,便猝不及防了開啟了夜的另一種打開方式……
腰肢有些發酸發脹,下意識想下子休憩片刻,腰間滾燙的大掌卻似乎不容在這場深的流中有哪怕片刻的缺席。
努力抑著噴薄到間的意,想起那日他們二人在隔壁傳來的說話聲,月清音便不免得紅了臉頰。
哪怕已經極力克制,可是有些聲音,不是克制就行的……
“夫、夫君……”
“唔。”
不過輕輕啟齒,便仿佛有洶涌的意要噴薄而出。
的臉比素日來每一個夜晚都紅,連帶著上這層紅翡般的艷,也是除了新婚夜之外有的景。
任由縱橫著本能馳騁,看見細弱的荑中握著發簪,像是忍,又像是著久違的承歡。
夜北冥第一次有些控制自己,不要太過多去想的……
久違的酸楚和怒火在無聲無息中帶著幾分發泄的意味。
看著不堪一握的羸弱腰肢,仿佛經不住今夜的狂風暴雨就要催折一般。
夜北冥結滾,啞聲道:
“清兒……”
“嗯。”
月清音想要應答,卻只能用咽行使原本屬于的權力。
要臉的,王之彥就在隔壁,夜北冥怎麼……怎麼今夜如此狂放。
Advertisement
幾日來,若不是顧及著王之彥的,兩人只怕是也不至于努力的控制著心中的旖思。
可是今夜的夜北冥卻仿佛被什麼忽然引燃了一般,又像是陳釀的酒開啟的一瞬間近乎要膨脹而出的熱氣噴薄而來。
聽著他的嗓音從遙遠縹緲,逐漸來到的耳邊。
滾燙的大掌所過之,冰涼節節敗退,翻涌而上的是屬于他的熾熱溫度。
“清兒,以后休要再提夜景煥的名字。”
夜北冥的語聲說不上平靜,卻不知他只因這一句話,短短景煥兩個字,憋了一天的悶氣。
努力抑著不想發泄出來,直到此刻將擁懷,恨不得骨,才能帶出幾分強裝的平靜來。
“夫君,我……啊……”
痛苦的仰起脖頸,猝不及防之中險些驚呼出聲。
突然來到邊的大掌卻準確的截住了那一聲突兀的嗚咽。
到在懷里戰栗,他鬢角也微微滲出薄汗,冰涼的在滾燙的脊背烙下輕吻。
“我知你心意,我知道……”
他不知道這句話是說給誰聽的。
但房間里只有他們二人,更大的可能是說給他自己。
不得不承認,久違的惶恐席卷而來,他怕口中再吐出他無法承的字眼。
之前剛親的時候,夜北冥還在每日給自己做接隨時可能離開的心理建設。
可是不知道多久開始。
或許是幻想和共白頭的時候。
或許是幻想和孕有一子的時候,雖然他更希是孩,像或是像自己都好。
或許是牽著的手,走過每一條悉或陌生街道的時候……
心里所鑄的防線在無聲無息中土崩瓦解。
夜北冥以為自己足夠堅強,刀山海他不怕,手刃敵人或是被敵人圍剿他不怕,保家衛國拋頭顱灑熱他都不怕。
但此刻……唯獨怕再說出刀鋒般銳利的字眼來。
將他好不容易捂熱的心一刀捅碎,就像那年被他摔碎的定親玉佩。
而這次,再也粘不起來。
無聲的流在夜中悄然進行,今夜的月不夠徹,落在的上卻仿佛遠不如圣潔。
滾燙的大掌躍的仿佛隨時都要超掌控,他想要握,卻換微微白了臉。
落在他肩頭的荑用不上力氣,卻徒勞的拍了拍,希他能稍微收斂一些近乎潰堤的癲狂。
一番酣戰過后,指尖仍止不住有些輕。
被他握在掌心,月清音的臉卻紅的快要滴……
親這麼久以來,不論是哪一次似乎都不如今夜的灼熱。
仿佛快要融化了煉紅的鐵水,安靜的躺在鑄造兵的模之中,任他打磨任何形狀。
做他的刀,做他的劍,亦或是只是掛在他腰間做一枚裝飾,皆可。
“清兒。”
“嗯。”
這次的對話,相較來說平靜了許多。
月清音躺在他懷里,目癡然的看著被夜風輕吻的帳幔,聽著耳畔振聾發聵的心跳,到熾熱的溫度散發到的每一表面。
灼燒著每一寸空氣,久久不曾平息。
雙至今都在發,虛無酸的無力洶涌而來,想要翻過將在夜北冥的腰上,一個不知何時養的不雅睡姿,夜北冥卻縱容到了現在。
合上眼眸,只覺得自己快要化雨化風,總之連都快爛水,就要蜿蜒到地上去。
被他的大掌牢牢錮住,仿佛才能覺得安心……
“我你。”
夜北冥沒意識到,這三個字宣之于口的時候,或許已經彰示出他的淪陷。
都說智者不河,此刻的他,卻不愿做智者。
“我也你,夫君。”
仿佛能到熱氣在兩人之間升騰,又隨著夜風散。
“我心里沒有夜景煥,真的沒有……”
著氣,哪怕是努力平復,再說話時也難免帶著幾分氣微微的樣子。
“逢場作戲而已,沒想過你會難過,對不起。”
月清音的歉然來的坦誠而又滾燙,仿佛比今夜的熾熱更加灼人。
夜北冥抿了抿,大掌一,第一次面對的對不起,沒有說不是你的問題。
或許這種無聲的接,讓月清音不知不覺間意識到了夜北冥生氣的重點。
“就兩個字,你竟然能醋一天?”
語氣中帶著幾分驚奇,似是無奈,又似是好笑,倒頭來竟然又微微的笑出聲來。
夜北冥只覺得窘迫,像是詭的心事被人撞破。
他抿了抿薄,瞪著懷里笑得花枝的人,第一次覺得男人也是要面子的!
“你還好意思笑。”
他說著,出手著的臉頰,迫使不得不仰首看向他。
彎月牙的眸中,依舊有遏不住的笑意。
“怎麼,本王不能吃醋?”
夜北冥的醋仿佛摻了不蜀南的紅椒,連酸都著幾分辛辣的意味。
“可以可以。”
月清音哪敢說不,瞇起眼看向他微抿的薄,似有不快的意味。
出荑,輕輕落在他的邊,無意識的輕挲。
“清兒只是覺得,夫君的醋,讓人甘之如飴。”
猜你喜歡
-
完結205 章

香妻如玉
凝香從冇想過自己會嫁給一個老男人。可她偏偏嫁了。嫁就嫁了吧,又偏偏遇上個俏郎君,凝香受不住俏郎君的引誘,於是甩了家裡的老男人,跟著俏郎君跑了。不料卻被老男人給抓了個現行!“你殺了我們吧!”凝香撲倒郎君身上,勇敢的望著老男人。老男人冇殺她,給了她一張和離書。然後,然後就悲劇了....俏郎君負心薄倖,主母欺辱,姨娘使壞,兜兜轉轉的一圈,凝香才發現,還是原來那個老男人好。突然有一天,凝香睜開眼睛,竟然回到了和老男人剛成親的時候。可這一切,還能重來嗎?--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42.4萬字8 11515 -
完結591 章

帶著千億物資穿成大奸臣的炮灰前妻
穿成大反派的作死前妻,應該刻薄親生兒女,孩子養成小反派,遭到大小反派的瘋狂報復,死后尸體都被扔去喂狼。 看到這劇情走向,俞妙云撂挑子不干了,她要自己獨美,和離! 手握千億物資空間,努力發家致富,只是看著這日益見大的肚子,俞妙云懵了,什麼時候懷上的? 不僅如此,大反派體貼化身寵妻狂魔,小反派乖巧懂事上進…… 這劇情人設怎麼不一樣?
103.7萬字8 99967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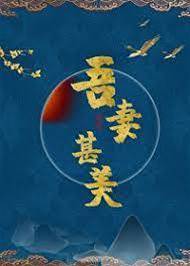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