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德侯府》 143.第 143 章
宣宏道被他這聲「對了」得背後發寒。
果然,下一刻,他就聽長子與他道:「我想過會去看看母親,您看可行?」
宣宏道的鼻翼一下就猛張了起來,他看著長子,神帶著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哀求,可是,在長子異常平靜的神當中,他最終垂下了肩,低下了頭,「你去罷。」
去罷,他也攔不住了。
「多謝父親。」宣仲安的眼又回到了在他懷中安睡的康,神淡淡:「還有要告訴您一件事……」
「那個人沒走,還在侯府,不過,他不在前府,也不在沁園和府別的地方,」宣仲安看著呆若木的父親,「現在,就只有聽軒堂兒子沒有挖地三尺了,等會兒子要是查出點什麼來,您別見怪。」
宣仲安說罷,抱著兒子站了起來。
出門的時候,他聽到了老父低沉痛苦的嗚咽聲,宣仲安的腳步未停,抱著兒子邁出了腳步……
屋外,雲鶴堂的梅花開了,宣仲安踩在那些凋落在地上的花瓣上走出了雲鶴堂,他後,被碾碎的花瓣狼藉一片,再也找不到它們昔日掛在枝頭上的絕花容。
**
這一日的侯府安靜又恐怖至極,只有沁園尚還有行走的下人,全府所有的人都被勒令呆在屋中不許邁出屋門一步。
直到傍晚,在一陣刀劍相博的干戈聲過後,被勒令呆在屋裏的下人才被告知可以出門各司其職。
下人們出門后,晚霞已至,五彩十的霞讓侯府的下人們不自抬頭,見周圍景沒有變化,邊的人還是以往的那些人,才把提在嚨里的那顆心鬆了下來。
Advertisement
而這廂,許雙婉也從來跟稟事的阿參裏知道從聽軒堂里搜出了一個不是這個府里的人來,這人本是一個在聽軒堂掃了一輩子院子的掃灑,但不知道什麼時候被潛進府里的暗諜殺了假扮了他。
「長公子說,您要是神尚可,就去一趟聽軒堂聽一聽來龍去脈,他在那邊等您。」阿參把他們這一日所查的事朝夫人稟明后又道。
聽軒堂啊?許雙婉沉默了下來。
「夫人?」
「好。」又一陣長長的沉默過後,許雙婉還是點了頭。
許雙婉到后,沒想到,在聽軒堂的大堂里,首先見到的人是雯兒。
披頭散髮的雯兒上被裹了一層遮的麻布,聽到是那個人來,遮著的麻布了起來,在下面的雯兒用還尚存的手掌著地,飛快抬起頭來,朝人了嗚嗚地了起來:「姑娘,姑娘……」
的舌頭因酷刑被剪掉了,「姑娘」被出來,只有含糊不清的幾聲嗚嗚聲,伴隨著裏的而出。
「夫人。」虞娘用的子攔住了那麻布的一邊。
但許雙婉轉過了頭,對上了雯兒鮮淋漓,慘不忍睹的臉,還有那雙帶著深深哀求的眼……
對上那雙眼后,就別過了臉。
「嗚。」用盡最後所有力氣抬起頭來的雯兒在心裏嘶了起來,賤人,死賤人,死的為什麼不是?
長公子,您難道沒看到,這才是許賤人的真實臉孔啊!您喜歡的只是個虛有其表的賤人啊。
雯兒倒在了地上,想去看長公子一眼,想親口告訴他,深他重用寵的所謂妻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可沒有力氣了,雯兒絕地哭了起來,可在深深的絕與害怕當中,又狂喜了起來。
長公子從來不正眼看一眼,沒事,有鄭郎,鄭郎,喜,為了,鄭郎寧肯死,也要幫報復那個就因為運氣好,就得到了夢寐所求的一切的許賤人,還是有人喜的,而且死了,死得也不冤,鄭郎說了,死了,但做的那些正確的事,正確的話,絕對會讓這些人最後不得好死的,們姑娘就是沒死在手裏,最後也會死在世上最清俊華貴無雙的長公子的手裏……
死在長公子的手裏,看還怎麼囂張,雯兒想著,高興得哭了起來……
雯兒就像一塊爛在麻布里抖著,這時候的聽軒堂大堂,本沒有人注意,只有邊,先前與一道遭嚴刑問過來的喬木恐懼地看著那張恐怖扭曲的臉。
雯兒瘋了,想。
要是沒瘋,怎麼不去恨毫不留就下令斬手指,割舌頭的長公子?卻在長公子下令后瘋狂大肆辱罵姑娘,詛咒姑娘不得好死?哪怕到現在,眼裏藏著的都是對姑娘的恨意……
至於眼裏的狂喜,那種瘋狂的迷眼神,喬木瞥到后,噁心得快要把腸子都吐出來了,飛快地扭過了頭,不敢再多看一眼。
怕再看一眼,都要瘋了。
從來不知道,那個對著長公子一句話都不說整齊,膽小如鼠的雯兒,原來本來的樣子,是這般的讓人膽寒。
而這廂,許雙婉走到了丈夫的面前,看向了丈夫邊不遠的那張椅子裏,此時扭著頭不看的婆母。
「來了,坐。」宣仲安嗓子沙啞,他清了清嚨,朝出了手。
許雙婉在他邊坐下。
「這是從母親床頭的暗箱裏搜出來的,給你看看……」宣仲安從擱在桌子上盤子裏拿出一個穿著的木偶,「這臉看著不?」
木偶上著一又一細細的繡花針,細針麻麻,從頭頂到臉還有腳,無一不滿……
許雙婉看不出細針下的臉,但卻看出了木偶上穿的那襲華貴端莊的,與的誥命服一樣……
那是丈夫封相后,為得來的誥命服,曾穿著它,在榮宮主持過皇后的婚事,也曾過它幾次,參加過兩次皇後主持的宮宴。
這襲誥服很襯,就像與生俱來就該穿在上一樣,去年過年要參加皇後主持的宮宴,在穿上這襲誥服后,長公子如是對說。
這一襲要穿到老,甚至要穿到墳墓里去的誥命服,許雙婉想認不出都難。
「是我。」許雙婉怔怔地看著木偶,遍生寒的整個腦袋一片發白,一時之間恍然不已,認不清這是在哪,是在人間,還是在煉獄。
「這是鄭鈎,霍家的死士,他說我們夫妻倆最後會被天下唾棄,千刀萬剮,死後烹油……」宣仲安朝妻子道:「我你來是想讓他看看,你是怎麼想的。」
許雙婉出手,住了他的涼手握了握。
朝被押跪在地上的鄭鈎看去,神不再迷茫,慢慢地變得清明了起來。
片刻后,看著滿臉漬,滿眼恨意死盯著的鄭鈎,緩緩清晰地開了口:「你到了地下,替我告訴霍文卿一句……」
猜你喜歡
-
完結315 章
冷帝在上,傲嬌皇後求休戰
一朝穿越,冷羽翎隨還冇搞清楚狀況,就被成親了! 他是萬人之上的皇帝,高冷孤傲,“我們隻是假成親。” 成親後,冷羽翎感覺自己被深深的欺騙了! 為什麼這個皇帝不僅要進她的香閨,還要上她的床 這也就算了,誰能告訴她,為什麼他還要夜夜讓自己給他生娃呢!
53.9萬字8.8 66122 -
完結260 章

流放路上炮灰寡婦喜當娘
許柔兒萬萬沒想到,自己竟然穿成炮灰寡婦,開局差點死在流放路上!不僅如此,還拖著個柔弱到不能自理的嬌婆婆,和兩個刺頭崽崽。饑寒交迫,天災人禍,不是在送死就是在送死的路上。但許柔兒表示不慌。她手握空間富養全家,別人有的我們也有,別人沒有的我們更要有!“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爹。”“爹?”許柔兒看著半路搶來的帥氣漢子,見色起意,一把薅來。“他就是你們的爹了!”帥男疑惑:“這可不興喜當爹。”“我都喜當娘了,你怕什麼喜當爹!”
47.3萬字8 29692 -
完結377 章

女主,你狐貍尾巴露了
養狐貍之前,裴鳴風每日擔憂皇兄何時害我,皇兄何處害我,皇兄如何害我?養了狐貍之后,裴鳴風每日心煩狐貍是不是被人欺負了,狐貍是不是受傷了,狐貍是不是要離開自己了。冀國中人人知宮中有個“狐貍精”,皇上甚為寵之,去哪帶哪從不離手。后來新帝登基,狐貍精失蹤了,新帝裴鳴風帶了個蕙質蘭心的皇后娘娘回來。
66.9萬字8 11395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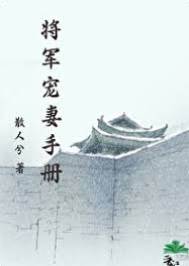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