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老師要請家長》 38、38
“我幫你洗。”
祁言這話時沒想那麽多,隻單純顧忌到上有傷口,獨自洗澡不方便,萬一沾了水極易染,好不容易擺了蛇毒影,不能再出什麽事。可話音剛落,屋子裏頓時安靜,陸知喬接到手裏的袋子沒拿穩,“啪嗒”掉在地上,而後抬起頭,驚惶地看著。
耳尖蔓延開點點櫻。
祁言怔愣,後知後覺到話裏曖昧意味明顯,薄了:“我——”
“祁老師幫媽媽洗澡啊?那不是要看了?”陸葳好奇地長脖子過來,打斷了祁言的話,生生令氛圍愈發引人遐想。
陸知喬擰起眉,臉頰唰地紅了大片,不自聯想起那個瘋狂的夜晚,心髒撲通撲通跳得飛快,佯裝若無其事,彎腰撿起袋子,聲:“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這會兒反應過來,祁言也許是好心,沒想那麽多,怕顧忌傷口洗澡不便,反倒是,沒來由地往歪想。自己腦子裏裝著什麽,看到聽到的便是什麽,賴不得別人。
“我不是那個意思,你別誤會……”
祁言有口難辨,看向罪魁禍首妞妞朋友,急中生智:“大家都是生,你有的我也有,沒什麽好害的。”
這妮子,言語險些汙清白。
誰料,陸葳用力點頭附和道:“就是啊,媽媽,你的不能水,自己洗澡肯定不方便啊,讓祁老師幫你一下,就別害啦。”
“……”
屋裏一陣詭異的沉默。
祁言心一,以為孩子發現了什麽,故作淡定地抬眼去,卻見姑娘抱著手機繼續玩遊戲,渾不在意的樣子,稀鬆平常。
這孩子是直的,是直的,是直的。祁言心安自己。
以見人無數的經驗來看,越是直,越對同之間的親行為不以為意,時候親親抱抱的同學都是如此,人不自知,引姬佬瞎想。若是想偽裝,便順著這一特融合進去,任何時候,友都能拿來做擋箭牌。
Advertisement
可是,哪裏能甘心於所謂的友呢?還想要更多,迫不及待地想,但同樣的,須得尊重陸知喬的意願,隻要對方一不接,們就隻能繼續維持“友”。
“真的不用了。”陸知喬低垂著眼皮,聲音訥訥。“我拿浴巾把包起來,不會到水的。”
“萬一呢?”眼見掉以輕心,祁言有些著急,聲音不由自主變大。“染可不是開玩笑的,你才從醫院出來,又想進去嗎?”
在醫院等待的那幾分鍾,漫長如幾個世紀,當時覺得都要塌了,現在想來仍背後冒冷汗,那種滋味,九歲時嚐過一次,今又嚐一次,不想再嚐第三次。
許是被這突然嚴厲的聲嚇到,陸知喬終於抬起眼皮,看著,那雙瀲灩的琥珀眸裏憂思萬千,寫滿了後怕,含著怒意,卻又十分克製,心翼翼,生怕被看見更深的在意。
看見了。
心用力躍了一下,突突地跳到嗓子眼。
的世界一片荒蕪,幹涸太久。有人在意,張,便猶如久待的甘霖,淅淅瀝瀝滲裂的心田,蠢蠢,本能地,一下子繳械投降。
“……好吧,我去給浴缸放水。”
“我去。”祁言攔住,把袋子提到廚房,掉外麵的防曬,轉進浴室,用洗手反複洗了兩遍手,又衝洗了下浴缸,才開始放水。
兒窩在沙發上打遊戲,似乎進到激烈階段,打得正開心,全然沒注意這邊的況,陸知喬也顧不得那麽多,上髒太難,便一鼓作氣掉了短袖和熱|,紅著臉進去。
熱水很快放滿了,裏麵煙霧氤氳。
祁言一轉,就見陸知喬在門邊,牆壁站著,隻穿了|y和|ku,麵紅耳熱手足無措的樣子,嚨忍不住了一下,迅速收回視線,低聲:“該看的都看過了,你也看過我,咱們扯平,不用不好意思。”
“”
不還好,一,陸知喬反倒往那方麵想,臉燙得燒手,恨不能立刻逃出去。然而祁言已經拿著浴巾過來:“把傷口包上。”
極力控製自己不看,眼睛卻不聽使喚。
陸知喬平常看上去纖瘦,弱弱的,實則該胖的胖,該瘦的瘦,(和諧)骨架子輕細,給人鳥依人的覺,(和諧)但應該不大健,線條略鬆,棉花糖一樣。
有熱意,沿著脊椎線燒上來,連忙退開些,假意去試水溫。
見規矩,陸知喬也鬆一口氣,利落除|去剩下的,用浴巾包住傷口,打了個結,走到浴缸邊下水。
“慢點。”祁言怕重心不穩摔著,扶著細瘦的胳膊,讓大半的重量都倚著自己。視線不由自主往偏移,堪堪掠過茂盛的叢林,眸忽而晦暗。
兩人挨得極近,聞見彼此發間的香味,而水汽本就悶熱,燥意湧上來則更加,陸知喬敏|極了,心髒在嗓子眼裏激烈地跳著,既不自在,又有些難言的興。微微偏頭,薄不經意到祁言的耳朵,可以明顯到這人僵了一下。
但,誰也不敢玩火。
陸知喬一隻腳水,另一隻腳半截搭在浴缸沿上,坐下來,瞟了祁言一眼。
祁言始終目不斜視,規矩自持,視線不挪半分,隻盯著包住傷口的浴巾,還十分善解人意地:“你自己洗,我不看,要挪或者要拿東西跟我。”
“……”
誰讓你看了。陸知喬腹誹,抿了,沒理。
蒸騰的水汽愈來愈盛,推拉玻璃門霧蒙蒙的,祁言凝神著浴巾,像個木偶似的一不,表麵越是平靜,心就越是翻江倒海——聽著耳邊潺潺淅瀝的水聲,不自浮想聯翩,實在是折磨人。
偏偏出來玩,同住一屋,沒帶玩。
於是不得不轉移注意力,想中午的事,想著雨林,蛇,鮮,還有死亡的恐懼,漸漸走神,也就好些。
洗完澡,祁言去收拾食材做飯,陸知喬站在臺上吹風。
太已經落下地平線,幕暗沉沉的,晝夜替之際,月亮爬了上來。沙灘上遊人依然很多,有的搭帳篷,有的烤串、喝啤酒,好不熱鬧。
微信收到許多新年祝福,陸知喬挨個回複,左右都是些客套話,溫子龍給發了紅包,收下,轉手發一個更大的過去,而後心來,給祁言也發了一個。
那人在做飯,應該看不到手機。
暖風吹散了些臉頰熱意,陸知喬轉進屋,手機擱到一邊,輕手輕腳走到廚房門口,看到祁言在裏麵忙碌的聲音,不自覺上前:“我來幫忙吧。”
鍋裏燉著湯,祁言正切土豆,聞聲側頭,眉眼展開溫的笑:“不用,你快去休息,等吃飯就好了。”
陸知喬沒,手去翻食材袋子,裏問:“都買了什麽?”
“不知道你吃什麽,我看見隻要有的,就各買了些。”祁言斂眸,不好意思地笑笑,一時悲從心起。
不是第一次給陸知喬做飯,每次,做什麽,陸知喬就吃什麽,無論早餐的粥、點心,還是午餐的炒菜,夜宵的麵條,這人幾乎都不挑。前兩特地用有限的食材和出,做了幾個口味不同的菜,飯桌上想觀察陸知喬吃哪樣菜最頻繁,可這人每樣菜都吃得很平均,不多一口,亦不一口,好像完全不挑食。
沒有偏好口味的人,是最難琢磨的,本無從下手。
陸知喬手一頓,心口有電流激,細長的指節抖著蜷了蜷,聲:“你可以問我。”
“那我現在問你。”
“好。”
“你喜歡吃什麽蔬菜?”祁言停下手裏的刀。
“土豆,金針菇,冬瓜,空心菜,豆。”
“葷菜呢?”
“牛,。”
“海鮮?”
“魷魚,基圍蝦,生蠔。”
“水果?”
“草莓,荔枝。”
“零食?”
“不吃零食。”
祁言問了很多,陸知喬都一一回答了,最後比了個k個手勢,表示知道,繼續忙手裏的活兒。
看著切菜,刀工練的樣子,順的長發披散在背後,宛如瀑布,陸知喬忍不住輕輕收攏頭發,把玩著,狀似自言自語:“其實,除了生薑大蒜和洋蔥,我基本不挑。”
發質真好,著溜溜的,很舒服。
“謝謝誇獎。”
“什麽?”
祁言稍稍傾斜子,任由玩自己頭發,抬眸一笑:“你的意思不就是誇我做什麽都好吃,做什麽你都喜歡吃麽?”
“……”
這人當真自,本不知臉皮是何。陸知喬暗暗惱,手上微微加重力道,揪頭發。
“哎喲——”
“專心切菜。”
吃過晚飯,祁言帶著陸葳去外麵散了會兒步,消消食,因心念著陸知喬一人在酒店,便沒太久,十幾分鍾就回了房間。為打發無聊時間,三人坐在臺上打撲克牌,祁言故意放水輸了好幾回,腦袋上被滿了白條,逗得母倆開懷大笑。
白發生的事讓每個人都繃著,耗費太多神,這會兒在心口的大石頭放下來,神經一鬆懈,生出許多疲憊,不到十點便困意連。
想著陸知喬上有傷,祁言讓單獨睡一張床,自己跟妞妞睡,孩子當然沒有異議,三人早早躺下,各自睡去。
遊人漸漸退去,夜幕下的沙灘一片安寧。
陸知喬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陌生的樹林,被一條黑的大蟒蛇追著跑,那蟒蛇張著盆大口,兩顆尖利的毒牙滴著腥臭惡心的唾,發出詭異恐怖的聲。跑到一懸崖邊,退無可退,絕之際縱跳了下去,然後驚醒過來。
睜開眼,靜謐的黑暗裏手不見五指。
原來是夢。
上汗涔涔的,枕頭和床單濡了一片,乎乎的,張深呼吸著,緩了會兒,睡意盡無,索爬起來,去了臺。
夜裏涼風吹拂,夾雜著鹹的氣息,一彎孤寂淒清的殘月高高掛在上,沙灘邊約傳來海浪拍打泥的聲音,四周黑魆魆的,隻有星點燈。
陸知喬手肘支著欄桿,肩背稍含,凝著沙灘上若若現的帳篷廓,神思飄忽飛遠。
假期才過一半,卻覺有半輩子那麽長,短短幾,好像經曆了無數事,心緒七八糟,複雜不出滋味,恍然有種在做夢的覺。
海島是與世隔絕的堂,在這裏,忘記了原本的自己,摘下了厚重的麵,裏麵最真實最不堪的東西出來,無法直視,甚至險些與死神麵對麵。開始思考自己是誰,究竟要做什麽,這輩子有何意義。
一切都因那個人而起。
從前哪裏會想這些,哪裏會有如此多不切實際的憂思,哪裏會自尋煩惱。的人生已經被一道做罪惡的鴻分割開,前二十一年,是自己,後麵這十一年,是麻木的死掉的機。
可是今活了過來,真切到被張,被在意的覺,那種滋味足以擊潰冰冷的機械外殼,深深鑿中裏麵的心。
忽然間意識到,原來自己如此。
像沙漠中尋找綠洲的旅人。
祁言,會是海市蜃樓嗎?
對好的人,很多很多,關心的人,也很多很多,不會因為別人的些許恩惠,就自我奉獻一切。但是祁言不一樣,或許早早就被那個人吸引,隻是不自知,所以這些任何人都能做的事,換祁言來做,便惹得悸不已。
然,像祁言那樣的人,注定與不屬於一個世界。
怎麽會喜歡祁言呢?
不會的。
陸知喬走著神,沒留意後的玻璃門被悄悄拉開,突然腰|間纏上一條胳膊,猝不及防被從後麵抱住,尖生生被溫|熱的掌心捂回了嚨裏。
“祁——”
“噓。”
鼻子裏鑽進清淡幽然的洗發水香味,很是悉,耳側撲來微熱的呼吸:“睡不著?”
猜你喜歡
-
連載757 章

婚期365天(慕淺霍靳西)
(此書已斷更,請觀看本站另一本同名書籍)——————————————————————————————————————————————————————————————————————————————————————————————————————————————————————————————————慕淺十歲那年被帶到了霍家,她是孤苦無依的霍家養女,所以隻能小心翼翼的藏著自己的心思。從她愛上霍靳西的那一刻起,她的情緒,她的心跳,就再也沒有為任何一個男人跳動過。
133.4萬字8 22440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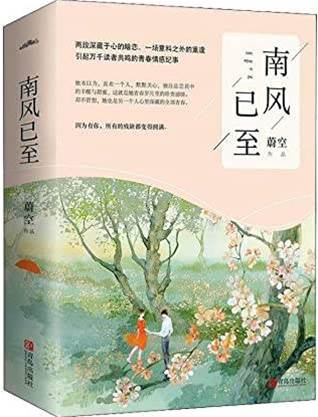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78 章

為情所婚
故事的開始,她闖入他的生活,從此天翻地覆。 故事的最后,他給了她準許,攜手共度一生。 一句話簡介:那個本不會遇見的人,卻在相遇之后愛之如生命。
20.9萬字8 19102 -
完結1547 章

墨少難惹:嬌妻帶球跑
他是商業帝王,清冷孤傲,擁有人神共憤妖孽臉,卻不近女色! 她是綠世界女王,冰冷高貴,卻…… “喬小姐,聽聞你有三禁?” 喬薇氣場全開,“禁孕,禁婚,禁墨少!” 轉瞬,她被丟在床上…… 某少居高臨下俯視著她,“禁婚?禁墨少?” 喬薇秒慫,想起昨夜翻雲覆雨,“墨少,你不近女色的~” “乖,叫老公!”某女白眼,拔腿就跑~ 某少憤怒反撲,“惹了我,還想帶球跑?”
272.3萬字8 60252 -
完結850 章

閃婚當晚,禁欲老公露出了真面目
【重生打臉+馬甲+懷孕+神秘老公+忠犬男主粘人寵妻+1v1雙潔+萌寶】懷孕被害死,重生后她誓要把寶寶平安生下來,沒想到卻意外救了個“神秘男人”。“救我,我給你一
87.7萬字8.18 36674 -
完結201 章

我欲將心養明月
高中暑假,秦既明抱着籃球,一眼看到國槐樹下的林月盈。 那時對方不過一小不點,哭成小花貓,扒開糖衣,低頭含化了一半的糖,瞧着呆傻得可憐。 爺爺說,這是以前屬下的孫女,以後就放在身邊養着。 秦既明不感興趣地應一聲。 十幾年後。 窗簾微掩,半明半寐。 秦既明半闔着眼,沉聲斥責她胡鬧。 林月盈說:“你少拿上位者姿態來教訓我,我最討厭你事事都高高在上。” “你說得很好,”秦既明半躺在沙發上,擡眼,同用力拽他領帶的林月盈對視,冷靜,“現在你能不能先從高高在上的人腿上下去?”
31.6萬字8 25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