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斷幽閣》 第130章 懵懂少年
鐵面閻羅苗賀坐在凳子上,漆黑的鬼臉上一雙充滿戾氣的雙眼,散發著嗜的寒,宛如鬼魅一般令人不寒而栗。冷冷地看著跪在自己面前的曼羅,宛如在看一條落水狗。
“師父,都是曼羅無能,他們夜間突襲三清山,我們實在不曾料到。”曼羅神惶恐。
“那你當時又在何?”苗賀語聲森冷。
“曼羅在山上巡視。”
“是嘛,你在巡視?怎就未發現有人夜襲?“
“是曼羅無能,的確不曾發現有人,等我回到道觀時我們的人已經跟他們打起來了,他們有三四千人之多,均穿黑,沒有任何旗幟和標識,本無法確認是何人所為,從襲到戰,看上去訓練有素,曼羅懷疑是湘國的軍隊。”
“湘國的軍隊攻打三清山?莫非又是肖寒干的?那你怎麼沒死?”鐵面閻羅語聲森然。
曼羅道:“混戰中曼羅傷,又被一人重重擊了一掌便暈過去了,他們或許以為我已經死了。等我醒來的時候山上已無賊人蹤影。”
一陣可怕的靜寂后,苗賀開了口:“可發現賊人線索?”
“賊人撤退后,曼羅四搜尋蹤跡,可是他們卻連一把劍,一柄匕首都沒有落下,山上除了我們自己人,不曾看到與敵人有關的任何線索,曼羅不敢撒謊。”
“你傷了?傷勢如何?”悶在面后的聲音冷如冰般散發出寒氣,令人骨悚然。
曼羅咬了咬牙,解開袖束口,將袖口緩緩推上去,出一大片纏繞的紗布,將紗布拆開,手臂上半尺長的刀傷剛剛開始結痂。
“傷的不輕嘛,難怪拿不穩日月雙鉤,打不過別人。”
話音剛落,隨著一道寒乍現,手臂上正在愈合的半尺長的傷口被苗賀手中突然出現的一柄匕首生生劃開,鮮如泉水般涌了出來……
Advertisement
曼羅“嗯”一聲悶哼,臉煞白,子晃了晃,險些栽倒在地。手捂住傷口,鮮還是從指間不斷漫溢出來。
苗賀幽幽道:“你的運氣還不錯嘛?伏龍山上山豹死了,我兩三百名奴死的死傷的傷,獨獨讓你毫發無損地逃了,此次死了千人又獨活了你一個。”
“師、師父,是曼羅命大了。”
“是嗎?嗯,上回聽說茹鸮‘照顧’得你很不錯啊,要不要我再喚他來教教你該怎麼為師父做事呀?”
聽得此言,曼羅眸中頓時閃出驚懼之,故作驚恐萬狀地拼命搖著頭,跪行兩步,哭求道:
“師父,不要啊,曼羅知錯了,是我沒有查探仔細,沒有及時發現敵人,可是真的只是曼羅命大沒有被他們殺死而已啊師父,曼羅無父無母,十二歲就跟著師父了,在我眼中師父您就是我的親生父親一般,師父說什麼曼羅無有不從,這麼多年來,我不敢對師父有半分地不敬,如今留著曼羅一條命,愿為師父肝腦涂地,不敢有毫懈怠,求師父饒了我吧……師父……”
上如此說,心中卻咬牙暗想:留下我一條命,我還要助爺報殺父之仇呢。
面后一聲悶悶地冷哼,“若不是山豹死了,湘國各據點又被肖寒那小子給盯上了,如今正缺人手,否則,就看你這兩次失手,老夫早就送你上西天了。”
曼羅哭著磕頭道:“多謝師父不殺之恩。”
苗賀嗡聲道:“不用急著謝我,老規矩,死罪可免,活罪難逃!”
一聽此言,曼羅頓時腦袋嗡嗡作響,不知道這次又會面臨怎樣的懲戒。
苗賀沉聲道:“來人。”
門外立時進來兩名甲武士。
“把給我掛樹上去,照老規矩辦。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當真命大,若得不死,我便再饒你一回。”
“是。”
苗賀起走人,不再多看曼羅一眼。
兩名甲武士取了繩索來,將曼羅的雙腳腳踝捆在一起,倒拖著來到門外一株大樹旁,將繩子拋上去,手用力一拉,曼羅便被倒掛了上去……
曼羅清楚地知道,苗賀口中的“老規矩”指的便是對屬下行失敗后的懲罰,其中之一即是將人如此倒吊七天七夜,任它風吹日曬雨淋,不給食和水,七日后是死是活便全看自己的命數了。
……
這時的曼羅已經完全不作他想了,命大不大,此刻全給了老天爺,事已至此,不過是聽天由命罷了。
自從被苗賀帶走,的苦難歲月才剛剛開了頭,多年來為奴司賣命,無數次刀劈斧砍鞭撻,好在還算聽話,與三位師兄所到的責罰相比,的責罰算是最的。
而如今自己這般被倒掛著,倒讓瞬間想起十九年前剛到奴司的景。
那時的還方夕悅,那個戴著鬼臉面的人將帶進一個很大的院子,便看見一個男孩如此這般被倒掛在院中的樹上。鬼面人將安置到一個臥房中,告訴,從今日開始你的名字就“曼羅”,隨即便離開了。
推開窗戶,院場景一覽無余。院中都是磚石地面,只有那株壯的百年老樹下有一圈泥土。那個倒吊在樹上的男孩早已氣息奄奄,時值酷暑,烈日暴曬,所幸老樹枝葉茂盛為他弱小的子帶來一清涼。一雙纖細的手臂無力地垂掛下來,一陣微風吹過,瘦小的子隨著長墜的繩索微微晃,旋轉,而男孩卻始終一不毫無生機,便如一只待宰的羔羊。
就在那株大樹的背后,一個中年男子遍鱗傷依靠著樹干,上十多傷口都在流,沒有人為他療傷,他自己仿佛也在聽之任之,未打算對傷口采取任何措施,一任鮮不停地流淌,猩紅的流大樹下的泥土中,為了這株百年大樹的養分。
院中來往的人不多,長相各異,形形,但唯一相同的卻都是面冷,無聲無語,仿佛一無聲行走的尸,了無生氣,他們從院中懸掛的男孩前走過,從流不止的男子側穿行,均宛若未見,神麻木。
這般如同人間煉獄的場景將十二歲的曼羅嚇的目瞪口呆,完全不知道這里是什麼地方,鬼面人將自己帶來此又是想做什麼,嚇壞了,一個人在墻角驚慌失措,臉上淚水橫流。
夜了,從窗前看去,院中燈籠閃爍著飄渺的,樹下已不見了那個渾跡的男子,只有那個孩子還倒掛在樹上。
一個跟一般大的孩來給送飯,問孩,那個樹下的男子去了何,孩淡淡地回道:
“盡而亡,拖走了。”
神依舊麻木,可是眸中卻有一抹地苦一閃而逝。
又問,那個男孩為何被如此吊掛著。
孩說:“犯錯了,已經掛了三日。”
問:“何時能放下來?”
孩說:“還有四日。”
問:“他這般掛著,可如何吃飯?”
孩道:“不準吃,聽天由命。”隨后便離開了。
……
夜深人靜,院中沒有一聲響,各房都熄了燈,終于忍不住了,了鞋赤著腳,吹熄燭火,端起一碗水,躡手躡腳地打開門向院中那株老樹走去。
男孩倒掛的頭部剛好面對的臉,他雙目閉,干裂,死了一般地安靜。
將手指放在他鼻下到一微弱的呼吸,心中一喜,忙將水碗湊近他的邊。男孩緩緩睜開了眼,紅的眼球暴突,長長的睫輕,當看清了眼前顛倒著的子的臉,他赤紅的眸子驟然多了一淡淡地澤。
用水碗輕輕他的,示意他喝些水,可是他張了張口卻又閉上,意識到男孩倒吊著本沒法喝水,水喝急了若是嗆鼻孔定然引起咳嗽反而會被人發現,將碗放在地上,躡手躡腳回房找了個勺子來,順便將晚上在自己的晚飯里留下的一點飯菜也取了來,一口口地喂給他喝,再喂給他吃,男孩極了,可是他倒著,吃喝極為困難,給他口中塞一口飯菜,男孩猛然翻而起,雙手牢牢抓住捆著腳踝的繩子,稍作息咽下飯菜后,再頭沖下翻下來再吃一口飯,如此這般三四次。
男孩低頭向看去,眼中閃出激之,口中艱難地吐出兩個字“快走”,聲音干沙啞。
……
如此連續三日,時常會于夜間看見那男孩會翻向上抓住那繩子像個蠶蛹一般,隨后再頭朝下倒掛下來。而曼羅每晚都會留下一半自己的晚飯,夜時端著水和飯讓他吃些,到第四日,也就是男孩懲罰的第七日,一醒來便奔向窗前向院中的大樹去,可是樹上已沒有了男孩的影,心中惴惴不安。
直到那個孩來送給送早飯時,問:
“樹上掛著的那個男孩去哪里了?”
孩漠然道:“懲罰時日到了,放下來了。”
心跳如鼓,急問:“死了嗎?”
孩道:“半條命。”
又問:“那他人呢?”
孩的下朝隔壁抬了抬,道:“回房了。”
聽得此言終于長長松了口氣。
幾日后便了鐵面閻羅的弟子,而這個男孩便是的四師兄——茹鸮,與曼羅一樣,“茹鸮”的名字都是師父給的,誰也不知茹鸮的本名。
也是到那時才知道,奴司對不聽話的,不能完任務的所有人都會有所懲罰,而懲罰的方式更是多如牛,可謂花樣繁多,手段殘忍,而且大多會在大庭廣眾下懲罰,以儆效尤,令人之不寒而栗,誰還敢心生半分忤逆之心?!
在謹慎小心如履薄冰地度過了十九年后的今天,終于還是到倒掛在樹下了。樹不是那棵樹,人也不是那個人,但痛苦如出一轍,心境絕無二致。
此時,眼睜睜看著手臂上的滴落在地上,著天地顛倒的暈眩,不知自己究竟會盡人亡還是等不到生生死就已經管裂翹辮子了。
陡然想起了那個“蠶蛹”,當時并不知十四歲的茹鸮為何會做出這般作,可今日,終于明白了,因為那時的小茹鸮尚無高深的武功,并無渾厚的力控制倒流的,他若不能時常讓自己頭朝上歇息一會兒,恐怕不出兩日就管裂而亡了。
想到此,曼羅閉上了眼睛,凝神運氣……
猜你喜歡
-
完結367 章

前妻,敢嫁別人試試
三年前,她在眾人艷羨的目光里,成為他的太太。婚后三年,她是他身邊不受待見的下堂妻,人前光鮮亮麗,人后百般折磨。三年后,他出軌的消息,將她推上風口浪尖。盛婉婉從一開始就知道,路晟不會給她愛,可是當她打算離去的時候,他卻又一次抱住她,“別走,給…
95.4萬字8 74666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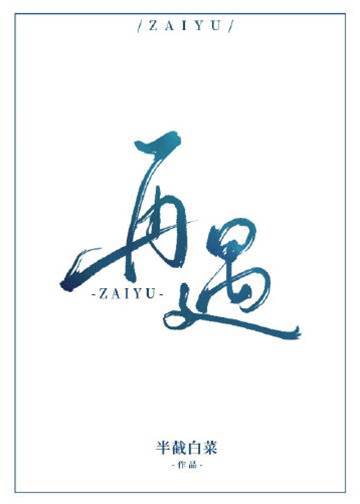
再遇
孟淺淺決定復讀,究竟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應浩。她也不知道。但是她成功考上了應浩所在的大學。一入學便得知,金融系應浩正跟金融系的系花談戀愛。-周喬曾說應浩不是良人,他花心,不會給她承諾以及未來。孟淺淺其實明白的,只是不愿意承認,如今親眼所見,所…
38.8萬字8 18890 -
完結641 章
重返七零之空間小辣妻
末世大佬唐霜穿到年代成了被壓榨的小可憐,看著自己帶過來的空間,她不由勾唇笑了,這極品家人不要也罷; 幫助母親與出軌父親離婚,帶著母親和妹妹離開吸血的極品一家人,自此開啟美好新生活。 母親刺繡,妹妹讀書,至于她……自然是將事業做的風生水起, 不過這高嶺之花的美少年怎麼總是圍著她轉, 還有那麼多優秀男人想要給她當爹,更有家世顯赫的老爺子找上門來,成了她的親外公; 且看唐霜在年代從無到有的精彩人生。
121.5萬字8 68733 -
完結2314 章

第一名媛:奈何嬌妻太會撩(盛莞莞凌霄)
“我愛的人一直都是白雪。”一句話,一場逃婚,讓海城第一名媛盛莞莞淪為笑話,六年的付出最終只換來一句“對不起”。盛莞莞淺笑,“我知道他一定會回來的,但是這一次,我不想再等了。”父親車禍昏迷不醒,奸人為上位種種逼迫,為保住父親辛苦創立的公司,盛莞莞將自己嫁給了海城人人“談虎色變”的男人。世人都說他六親不認、冷血無情,誰料這猛虎不但粘人,還是個護犢子,鑒婊能力一流。“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是什麼?”“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說你不好,那個人依然把你當成心頭寶。”
426.6萬字8 397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