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前任他叔沖喜》 第184章
第184章
溫暖的散落在西廠庭院中, 一棵枯柳下擺著一張籐椅,陳河一襲青衫,靠坐在籐椅裡, 合著雙目, 修長乾淨的手指輕輕過膝上的雪團。他平時並非懶散人, 即使放鬆下來,亦沒有多慵懶之態, 清冷疏離於世。
待姬無鏡走得近了,陳河才睜開眼,道了一聲:「師兄。」
「起來, 跟我造反去。」
趴在陳河上的雪團被吵醒了,它了個懶腰,用頭蹭了蹭陳河的手掌。
陳河垂眼瞧它, 手掌捧起它的臉,雪團習慣地歪著頭,更用力地去蹭陳河的手。陳河的目落在雪團上,溫笑著,說:「師兄還是找旁人。你知道,我最怕麻煩。」
姬無鏡下心裡的不耐煩, 怪氣地開口:「你喜歡貓曬太怎麼不去海邊?還能聽浪看,多快活哈。留在西廠裡也不嫌麻煩。」
「師兄此言差矣,西廠雖事多,可若師弟平時管理妥當,各項事由自有負責的人, 而我,只需偶爾檢查罷了。頂天誰與誰有了衝突矛盾,再出面判個一二三四。師兄不諳管理之道,若是興趣,師弟倒是可以傳授些經驗。」
雪團沿著陳河無一褶皺的青衫慢吞吞地往上爬,它將小爪子搭在陳河的肩上,用頭去蹭陳河的下。
姬無鏡看在眼中,無語道:「陳河,已經死了,雪妃已經死了,死得乾乾淨淨,和這隻貓沒有半點關係。」
陳河輕雪團的手指微僵了一瞬,又繼續緩緩輕雪團的髮。他「嗯」了一聲,說:「我知道。」
可它是與這人世間最後的一點牽連了。
陳河垂眼凝視著雪團。他的臉上始終掛著溫的笑,早已不見悲戚。
Advertisement
十五歲時,他陪著從遙遠的北川背井離鄉不遠萬里和親而來,陪了宮。兩年後,香消玉殞,獨留他一人在這異鄉,眨眼已十年。
送來的柳苗已長,三月風絮,夏時避。即使是寒冬枯落時,亦可伴他。
他答應過,會好好地活,認真地活,亦會幫庇護族裡。
姬無鏡往前走了一步,在陳河側懶散蹲下,與他平視,難得拿出幾分認真的語氣來,說道:「師兄知道你不在意誰當皇帝,你就想安安分分當你的西廠督主,在這院子裡,在這棵柳樹下和你的貓膩歪。但是你想想,我兒子當了皇帝,你這日子豈不是更安穩?」
陳河看向姬無鏡。
「你不僅能當西廠督主,還能把東廠也一併收了。」姬無鏡再,「錢啊,兵啊,都送去雪族,護雪族百年昌盛?」
陳河看了姬無鏡半晌,終於開口:「師兄究竟想讓我做什麼?我不覺得有什麼事是西廠能辦到而你自己搞不定的。」
姬無鏡輕扯了下角,笑:「其實有你沒你也沒什麼區別,但是有你的話,更完些。」
陳河平靜的墨眸中終於浮現了一無語。
他說:「事先說好,有命之憂的事我不做。」
「行行行,天塌了師兄在前面給你頂著。」
姬無鏡和陳河到了宴席時,正是顧見驪從屏風後緩步走出來的那一刻。
「顧見驪?」姬平蓮的臉變了又變。本來一直興今日事父親了大功臣,來日風無限……
心裡一直是暖的,直到顧見驪出現,像是一頭涼水澆下來,讓稍微清醒了些。
顧見驪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不是應該被圖爾強佔了去?與料想不同,這讓姬平蓮心中不悅。面上大度,實在小心眼得很,上次壽宴上顧見驪當眾落了的面子,一直記恨著。
不管姬巖如何質問,不管姬巖抬出來多個人證,也不管朝臣暗藏鋒芒的話語,姬嵐一直都是從容的。可是他看著顧見驪出現時,一下子握了手中的酒樽。他微微瞇起眼,凝視著顧見驪一步步走近,直到走到臺下近,與溫靜姍並肩時,姬嵐才悠悠開口:「盛儀郡主也要摻和一場?」
「陛下篡改詔書是事實。」顧見驪抬頭,直視姬嵐。
姬嵐死死盯著顧見驪的眼睛,半晌,忽然輕笑了一聲。
沒想到,今日竟是在這樣的況下與相見,也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他慢悠悠地轉著酒樽,似有些出神。
姬巖看了看溫靜姍,又看了看顧見驪,心中的懵怔又添了一重。顧見驪怎地也到了?
事實上,他苦於沒有姬嵐篡改詔書的證據,做了假證。反正前面有那麼多真證據在,渾水魚一遭也無妨。是,姬無鏡曾派長聆告訴他國宴之日陳河將會來作證。但是姬巖並不放心姬無鏡的行事,將什麼都不知道的小太監抓來,想要小太監做偽證。果真陳河並沒有出現,他正想把那個小太監帶上來,怎麼陳河沒來反倒是顧見驪來了?
溫靜姍也好,顧見驪也好,們的出現明明是幫了姬巖,姬巖應當高興才對,可是他心裡竟然生出一種奇怪的不安來。
「今日景,盛儀郡主萬不可妄言。」臨泗王道。
顧見驪對他輕輕頷首,聲輕緩卻堅定:「先帝駕崩之夜,我本在宮中。最後見到先帝的人亦是我。當日大火熊熊,陛下與五皇子很快趕來,得知先帝崩逝,兩位皇子迅速趕去拿到詔書,詔書之上所寫之人的的確確是二殿下。五殿下派人去請已離京的二殿下,卻被陛下親手殺。」
席間譁然一片,竊竊私語逐漸聲大,議論不休,嘈雜一片。
「我媳婦兒真好看誒。」姬無鏡立在角落時,懶洋洋裡帶著驕傲。
陳河側首,問:「師兄讓我過來是看嫂夫人的?」
姬無鏡沒搭理陳河,遙遙著顧見驪。
姬嵐著顧見驪張了張,想說什麼,卻又終是儒雅溫潤地笑了。
在過去的一年裡,他曾多次想過殺掉顧見驪。將先帝駕崩那一日所有知人盡數斬殺,不該留著知他把柄的顧見驪才對。他每每勸著自己顧敬元還有利用價值,顧敬元寵,若是殺了顧見驪,定然會遭到顧敬元的反攻。
可真的完全是因為顧敬元嗎?
也不全是。
後悔嗎?
姬嵐欠,將手中的酒樽慢慢放在了案桌上。
不,他不後悔。
他這一生,從來不悔。
本就一無所有,爬至今日,即使再失去一切,亦不賠。
隨著姬嵐的沉默,席間的氛圍變了。只因姬嵐這個時候的沉默太像默認。
「陛下,二殿下與盛儀郡主所說可都是實?」
「陛下設計陷害先太子,借二殿下之手殺之,嫁禍四殿下,又篡改詔書,殺五殿下,追殺二殿下?這一樁樁一件件究竟是不是真的?」
「陛下可還有別的話說?」
「老臣有幸,在諸位殿下時給你們啟蒙上課,看著你們兄弟幾人長大。殿下所作所為實在是讓老臣心寒。」
一時之間群臣討伐。
竇宏巖急了一頭汗,他急忙湊到姬嵐耳畔,低了聲音說道:「陛下,萬不可放棄。我們還有五萬林軍,還有東廠之眾,還有外涼可汗相助……」
姬嵐提袖,慢悠悠地給自己倒了一盞酒。他臉上掛著淺笑,一副從容釋然相。
有林軍有東廠有外涼又有何用?
今日形式,朝臣皆反,重兵在外,舊事暴再無人心。要人,沒人。要兵,沒兵。要人心,更無。
即使他今日利用這五萬林軍殊死博弈,就算贏得一時安穩,大勢終已去。
更何況,他自小學著忍,已無心再過逃亡日。
不知不覺中,席間喧囂竟停了,幾百人誰也沒有發出一丁點聲音來,一雙雙眼睛向高臺之上的姬嵐。
姬嵐神態自若地飲了一口佳釀,甜酒,他品了酒香,目落在下方的顧見驪上。他著顧見驪,緩緩說道:「郡主可想念你的姨母?」
顧見驪在一瞬間變了臉。
姬嵐平靜地目掃過滿朝文武,道:「二哥賢能,朕願意禪位。實不相瞞,禪位詔書早已寫好。」
姬巖怔了怔,覺得不可思議,半信半疑地盯著姬嵐的臉,想在他的臉上看出些端倪來。
姬嵐起,隨著他細小的作,所有的視線亦跟隨著他。
「盛儀郡主可願意陪朕去取禪位詔書?」
姬嵐的這個提議又是讓所有人驚了驚,這莫不是什麼謀詭計?
姬嵐儒雅地笑了,「詔書、玉璽都被朕放在一,旁人就算將這皇宮掘地三尺亦不得尋。盛儀郡主可願同往,替新帝拿這詔書與玉璽?」
顧見驪整顆心懸了起來,滿心都是姨母!
姨母難道被姬嵐抓了起來?——這個想法讓顧見驪遍生寒。不能,不能讓姨母再半點折磨痛苦啊!
「好,我與陛下同往。」顧見驪聽見自己的聲音這般說。
不管姬嵐打了什麼主意,必然要去這一遭。即使喪了命,也要走這一遭。
陳河還沒來得及作,便覺側一道風掠過,連帶著他腰間的佩劍亦不見了蹤影。
姬無鏡面無表從角落裡藏的高臺飛掠而下,快如風。不過是瞬息之間,他的影飛過整片宴席桌案,掠上高臺,手腕翻轉間,佩劍刺姬嵐膛。鮮湧出,染紅劍。
即使是護著姬嵐的竇宏巖都沒反應過來。
姬無鏡挑起眼睛,瞧著面前的姬嵐,流嫌惡之。哪那麼多廢話,哪那麼麻煩,殺了再說。
讓我的小驪驪和你同往?呵。
顧見驪呆呆著這一幕,連反應都忘了。
猜你喜歡
-
完結3579 章

韓先生情謀已久
“收留我,讓我做什麼都行!”前世她被繼妹和渣男陷害入獄,出獄後留給她的隻剩親生母親的墓碑。看著渣男賤女和親爹後媽一家團圓,她一把大火與渣男和繼妹同歸於盡。再醒來,重新回到被陷害的那天,她果斷跳窗爬到隔壁,抱緊隔壁男人的大長腿。卻沒想到,大長腿的主人竟是上一世那讓她遙不可及的絕色男神。這一次,她一定擦亮眼睛,讓 韓先生情謀已久,恍若晨曦,
354.7萬字8 57206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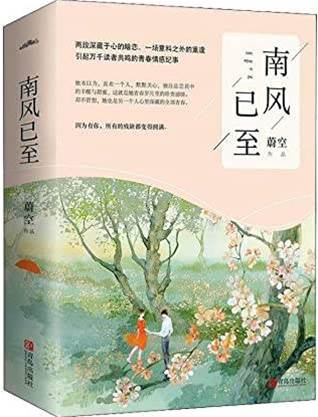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491 章

裴教授,你行不行啊
絕世小甜文,年齡差,先婚后愛,1v1雙潔,斯文敗類教授X古靈精怪富家女。劇情一:葉允澄可憐巴巴的看著裴修言:“老公,我作業沒寫完,你跟我們導員熟,你跟她說一聲讓她別檢查作業了好不好。”裴修言抿唇不說話。結果第二天,導員只檢查了葉允澄一個人的作業...下班回家的裴修言發現家空了一大半,葉允澄不見了...
97萬字8 44785 -
完結183 章

乖吝
【甜寵&雙暗戀&校園到婚紗&雙潔&救贖】(低調清冷富家大小姐&痞壞不羈深情男)高三那年,轉學至魔都的溫歲晚喜歡上了同桌校霸沈熾。所有人都說沈熾是個混不吝,打架斗毆混跡市井,只有溫歲晚知道,那個渾身是刺的少年骨子里有多溫柔。他們約好上同一所大學,在高考那天她卻食言了。再次相見,他是帝都美術學院的天才畫手,是接她入學的大二學長。所有人都說學生會副會長沈熾為人冷漠,高不可攀。卻在某天看到那個矜貴如神袛的天才少年將一個精致瓷娃娃抵在墻角,紅著眼眶輕哄:“晚晚乖,跟哥哥在一起,命都給你~”【你往前走,我在身后...
32.4萬字8 9635 -
完結872 章

誘捕玫瑰
五年前,溫棉被人戳着脊樑骨,背上爬養兄牀的罵名。 所有人都說她是個白眼狼,不懂得感激裴家賜她新生,反而恩將仇報。 只有她自己知道,這所謂的恩賜,只是一場深不見底的人間煉獄。 五年的磋磨,溫棉險些死在國外。 重新回來時,她煥然一新,發誓要讓裴家的所有人付出代價。 本以爲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死局。 卻沒想到,這個將她送到國外的養兄,卻跟個甩不掉的牛皮糖一樣跟在身後。 她殺人,他遞刀,她報仇,他滅口。 終於,溫棉忍不住了—— “你到底要幹什麼?” 而那隱忍多年的男人終於露出了尾巴:“看不出來嗎?我都是爲了你。”
84.4萬字8 21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