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嬌太子的外室美人》 第16章 哄
江音晚背倚在裴策的膛前,到寬厚的溫熱。素約細腰,被一雙堅實臂膀松松環著。聞到淡淡龍涎香氣,清冽微苦。
神志,終于一點點從那場過于真實的噩夢中離。側過頭,杏眸抬起,視線里是后男人棱角分明的下頜,近在咫尺。
這樣近的距離,隨著長睫的輕,剔的淚珠,沒裴策玄織錦蟒紋的襟,洇開一點更深的墨。
江音晚察覺到腰際手臂將攏得更了些,似乎眨眼睫,便會劃過男人頸部的皮。不由將上微微后仰,拉開一些距離,問:“殿下,是音晚擾了您安歇嗎?”
嗓音如枝頭輕的一瓣梨花,一場蒙蒙煙雨便能將其摧折。清甜的氣息,拂在男人的脖頸,輕輕的,勾起意。
江音晚看到近在眼前的結輕輕滾,隨后一只大掌從腰際上移到了背部,輕輕將向懷里。拉開的那點距離,很快消盡。
江音晚下意識地閉上了眼,脊背難以控制地繃。環過腰背的臂膀卻收得更。
黑暗里,鼻端龍涎香氣,就像這香的主人,明明冷淡疏離,亦并不,卻以強勢的從容,將籠罩。
男人的下輕輕抵在的頭頂。聽到低沉的嗓音響起,帶著懸心后終于松了口氣一般的清倦:“無礙。”
過于的懷抱里,江音晚能察覺說話時他膛的輕。因張僵了許久,終于再次開口,聲音同思緒一樣飄忽似煙絮:“我好像做了一個噩夢。”
Advertisement
裴策一臂環著的纖腰,另一手掌在單薄的脊背上輕輕拍著,低低道:“孤知道。只是個夢。”
可懷里的人,并沒有到安。他聽到幽微的啜泣,仿佛抑著不敢出聲,前襟暈開涼涼的意。
緩緩拍的手掌,了節律。
江音晚努力下哽咽,道:“不一樣的。”
“什麼不一樣?”裴策嗓音沉緩,耐心問。
江音晚無法作答。那夢里的驚痛,不敢再回憶分毫。
那個夢,只是一些零散支離的畫面,短暫,朦朧。卻過于真實。
依舊是置于歸瀾院,卻有細微的不同。看到菱花檻窗外,檐下多了一只鸚鵡,翅膀和長尾是漂亮滴的青翠,部有一點藍。
它立在鳥架棲桿上,足上拴著帶金鈴的細鏈,每每扇那雙鮮亮的翅膀,金鈴就一晃一晃地響。
很快如投石水,這一幅畫面散作破碎水波,影瀲滟間,那細細的金鏈,竟似到了自己的腳踝上。
纖白的踝,輕搖的鈴,叮鈴叮鈴,響在耳邊。
那金,漸漸晃得迷,化作模糊一團。
下一個畫面,看到了自己,抱著膝蓋坐在拔步床上。重重越羅帷幔如紫輕霧,聽見自己在哭。
而秋嬤嬤站在夢里那個自己的邊,俯勸:“人死不能復生,還請姑娘節哀……”
什麼人死?什麼節哀?
江音晚的心瞬時揪,一種雷霆將落的預,如巨石上心頭,讓不過氣。
站在迷離影里,怔怔看著秋嬤嬤開闔,一字一字,如綿長尖利的針,刺進的口——
“流放崖州氣候惡劣,路途艱苦,江夫子弱難,染疾故。奴婢亦十分悲慟,姑娘想哭便哭出來吧。只是哭過之后,活著的人還是要向前看,保重自己才要……”
江音晚腦中嗡的一聲,一時仿佛每個字都聽不懂。待遲鈍拼湊出話里的意思,已如置冰窖,通生寒。
父親江景行獲罪之前在國子監教書講經,長安人亦隨學生尊稱一聲“江夫子”。
染疾故……
驚雷萬鈞,冰凍千尺,不過如是。
背上拍的手停下,江音晚聽到裴策詢問地喚一聲:“音晚?”
江音晚朦朧回神,才發覺臉頰著冰涼,原來自己的淚已染裴策襟一片。
“太過真實了。”喃喃答,那麼輕緲,的,如掌心一塊將要化盡的碎冰。
裴策手掌挪到的肩頭,又輕拍了兩下:“是你魘著了。”
“真的只是夢嗎?”江音晚的自語,含糊在斷斷續續的啜泣里。
“只是夢。你已經醒了,已經沒事了。”裴策繼續的背,難得有這樣的溫和。
江音晚沒有說話,亦沒有再發出啜泣聲。然而裴策知到前襟的涼意,默默擴大著,手掌下的單薄肩背不住小幅地。
他的聲音是一貫的沉緩,只有自己知道其中掩去了幾分慌:“許是你今日去了牢獄,有所沖撞。明日,孤去保國寺一趟,求一道平安符。”
江音晚依然沒有說話。連那句慣常掛在邊的“音晚多謝殿下”都沒有說。
裴策失了素來的游刃有余,面向外間,眉眼冷峻如淬了冰:“太醫怎還未至?”
李穆守在外間,此時恨不能做個形人,卻不得不答太子的問話。
那扇紫檀木邊座漆心染牙屏風已被撤去,月門落地罩前,垂下一幕珠簾,顆顆潤澤飽滿、大小一致的珍珠,間以晶瑩剔的紅瑪瑙,長垂至地。
李穆弓著腰背進來,小心抬手拂開,避免它發出聲響。這會兒,自然是謹慎再謹慎,一點差錯都可能被遷怒。
然而那珠簾細,一旦互相,便不可避免地出聲,如珩佩流響。
本是輕靈悅耳的聲響,江音晚的脊背卻微微一瑟。
拔步床型龐大,前有回廊。太子坐在床頭,最外頭那層薄薄羅幔垂下,其形影影綽綽。
李穆低著頭不敢抬起,只覺太子落在自己上的視線,驟然凌厲如劍。
縱是太子邊的老人,亦不由生出冷汗,趕忙回話道:“已派人去請,想來已在趕來的路上。”
李穆在心中苦,太醫總需有在途中的時辰。然而太子一言不發,顯然是不滿。
幸而就在李穆即將汗脊背之時,外頭通傳太醫至。李穆長舒一口氣,急忙將人引進來。
江音晚聽到太醫進來行禮:“微臣叩見太子。”
掙了掙,覺得總不能就這樣讓太醫診脈。然而裴策一臂桎梏在的腰際,并不放開,另一手輕輕著的細腕,似就這樣遞到床圍之外。
有些著急,用了力將上后仰,噙了淚的杏眸對上裴策的眼,哀求地低低喚一聲:“殿下。”
裴策垂眸看,那幽邃的眼,仍如清寒的冷泉,一息后,終是松開了錮著纖腰的手。
猜你喜歡
-
完結940 章

農門長嫂富甲天下
倒霉了一輩子,最終慘死的沈見晚一朝重生回到沈家一貧如洗的時候,眼看要斷頓,清河村的好事者都等著看沈家一窩老弱病殘過不了冬呢。 她一點都不慌,手握靈醫空間,和超級牛逼的兌換系統。 開荒,改良種子,種高產糧食,買田地,種藥材,做美食,發明她們大和朝見所未見的新東西……原打算歲月靜好的她一不小心就富甲天下了。 這還不算,空間里的兌換系統竟還能兌換上至修仙界的靈丹,下到未來時空的科技…… 沈見晚表示這樣子下去自己能上天。 這不好事者們等著等著,全村最窮,最破的沈家它竟突然就富了起來,而且還越來越顯赫。這事不對呀! ———— 沈見晚表示這輩子她一定彌補前世所有的遺憾,改變那些對她好的人的悲劇,至于那些算計她的讓他們悔不當初! 還有,那個他,那個把她撿回來養大最后又為她丟了性命的那個他,她今生必定不再錯過…… 但誰能告訴她,重生回來的前一天她才剛拒絕了他的親事怎么辦?要不干脆就不要臉了吧。 沈見晚故意停下等著后面的人撞上來:啊!沈戰哥哥,你又撞我心上了! 沈戰:嗯。 ———— 世間萬千,窮盡所有,他愿護阿晚一生平平安安,喜樂無憂。
181.6萬字8.33 135289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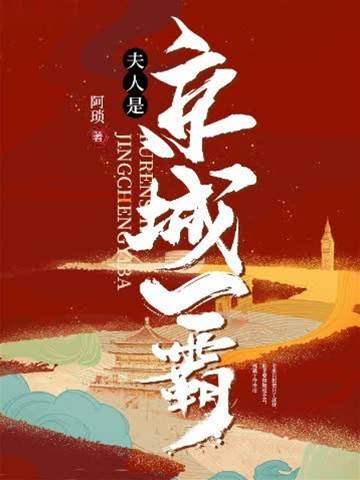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109 章

偏執太子的掌心嬌
宣威將軍嫡女慕時漪玉骨冰肌,傾城絕色,被譽為大燕國最嬌豔的牡丹花。 當年及笄禮上,驚鴻一瞥,令無數少年郎君為之折腰。 後下嫁輔國公世子,方晏儒為妻。 成婚三年,方晏儒從未踏進她房中半步。 卻從府外領回一女人,對外宣稱同窗遺孤,代為照拂。 慕時漪冷眼瞧著,漫不經心掏出婚前就準備好的和離書,丟給他。 「要嘛和離,要嘛你死。」「自己選。」方晏儒只覺荒謬:「離了我,你覺得如今還有世家郎君願聘你為正妻?」多年後,上元宮宴。 已經成為輔國公的方晏儒,跪在階前,看著坐在金殿最上方,頭戴皇后鳳冠,美艷不可方物的前妻。 她被萬人敬仰的天子捧在心尖,視若珍寶。
33.7萬字8.18 14518 -
完結942 章

重生我嫁給了未婚夫的死對頭
86.7萬字8 280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