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寡嬌妻不甜不要錢》 第1997章:【番外】春生江上幾人還(1)
酒吧里的搖滾樂震天響,男男在舞池里瘋狂舞,五六的燈打過去,群魔舞的景象頗有幾分驚悚。
“我都對他那麼好了,他為什麼還是要劈?!”哭的滿臉是淚的孩子趴在桌子上一杯一杯的給自己灌酒,“為什麼啊……”
朋友勸:“又不是非他不可,不行就分,下一個更好。”
孩子卻說:“就是非他不可!”
淚眼朦朧的看著朋友,哽咽的問;“你心里有沒有那樣一個人?你清楚的知道,除了他,你不會再上任何一個人。”
林雨門隔著幢幢人影看見了那個孩的眼睛,怔了一下,而后垂眸一笑。
心里也有這樣一個人。
林雨門并不經常想起那個人,甚至很多時候都以為自己忘記了那段跟在他邊的日子。
但只要想起,就總會覺得心臟缺了一塊,無論用什麼都填補不滿。
Advertisement
林雨門起,打了個響指,出幾張鈔票在杯子下面,對酒保道:“那個妹妹的酒我請了,你看著點,別被人撿尸了。”
酒保笑的答應了,又問:“是你妹妹嗎?”
林雨門想了想說:“只是對那句話很有同罷了。”
走出熱鬧的酒吧,外面的街道明顯冷清許多,距離上次軍訓時見到阮落榆,已經過去兩周了。
回想起那時候阮落榆的態度,覺得自己當年做的可能是有點太狠了,畢竟阮落榆一直對很縱容,有嚴厲的時候,但上次見面,他的厭惡之幾乎流于表面。
林雨門仰頭看著天空嘆了口氣,手指無意識的在自己心口比劃了兩下,知道阮落榆心口那里就有這樣一條長長的疤痕,曾經親手剖開了人的皮。
“喲。”忽然一道口哨聲響起:“小妹妹,一個人啊?”
林雨門轉頭,就見幾個流里流氣的小混混雙手著兜圍了上來。
這種事在混的酒吧附近常有,喝醉了的直接拖走,沒喝醉的就采取暴力脅迫的方式。
林雨門今晚喝了一點酒,但還遠沒有到醉的程度,抬起眼看了看這幾個不長眼的小混混,犯到手里算是倒霉。
正要挽起袖子,忽然瞥見什麼,立刻弱弱的后退兩步:“你們、你們想干什麼?!”
為首的混混怪笑道:“別怕啊小妹妹,我們只是想要跟你玩兒個游戲而已,你乖乖配合的話我們就溫點兒,要是不聽話的話……”
路過的人停住腳步,往這邊看了一眼。
他穿一件黑的薄外套,戴著鴨舌帽和口罩,好像很怕見,但優越的高和型在人群中還是非常顯眼。
“看什麼看!”有混混拿著棒球指了指男人,兇惡道:“別多管閑事,趕滾!”
男人看看小混混,又看看林雨門,而后退后兩步,禮貌頷首:“你們繼續,我沒有打擾的意思。”
林雨門:“……”
這到底是個什麼品種的狗才能干出這種事啊!
猜你喜歡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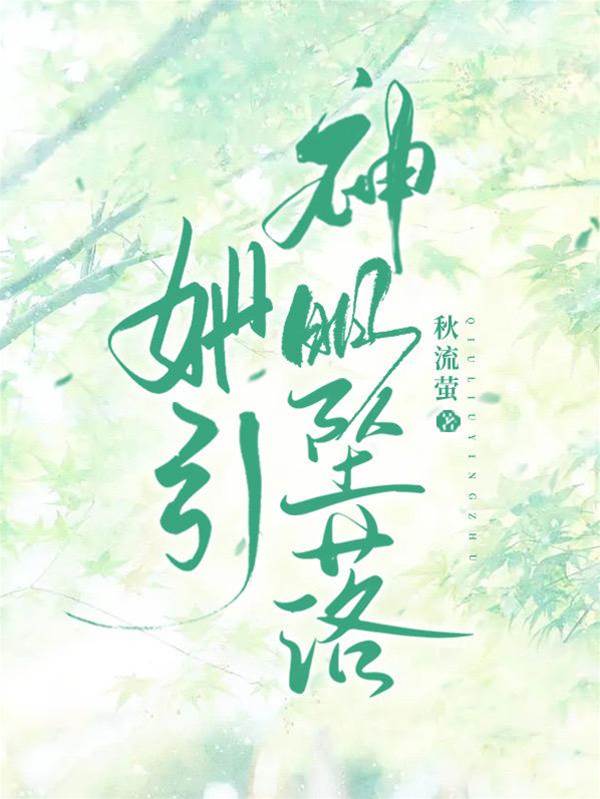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69 章

溫先生的心尖月
(蓄謀已久 細水流長 甜寵 雙潔 無虐 年齡差五歲左右)(女主醫生,非女強)*【溫婉清麗江南風美人 & 內斂沉著商圈大佬】容煙出身書香門第,自小跟隨外公生活。聽聞外公給她尋了門親事,她原以為聯姻對象是同為醫生的溫二公子,殊不知卻是接管溫家的溫景初。煙雨灰蒙,寺廟裏,容煙瞥見與她擦身而過的男人。上一次見他還是四年前,可他從不信神佛,為何會出現在這裏?朋友生日聚會結束,溫景初送她歸家。車內,容煙壓住心中疑惑,終究沒問出口。*容煙本是溫吞的性子,喜靜,信佛。她自認為婚後的兩人是相敬如賓,搭夥過日子。而他卻步步誘她淪陷。某日,容煙在收拾書房時看到了寺廟的祈福袋,裏麵白色宣紙上寫著她的名字,似乎珍藏了許久。而此時溫景初正接受電視臺采訪,清肅矜貴,沉穩自持,淡定從容與人交談。主持人問,“溫先生,聽聞您並不信神佛,但為何每年都到靈山寺祈願?”容煙手中拿著祈福袋,略帶緊張的等待著他的回答。男人黑眸如墨,思忖片刻,緩緩啟唇,“因為溫太太信佛。”簡單一句話卻擾亂她的心。
33.1萬字8.09 265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