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荒不慌,三歲福寶寵全家》 第131章 慘痛的代價
“大人,草民盧新知,求您為草民一家做主啊!”
跪在堂下的是一名三四十歲的中年男人,穿儒衫,頭戴方巾,上來就狠狠磕了三個響頭。
程小棠眸微閃,這人來的時機很微妙,一看就不是善茬,還姓盧。
“爹!你怎麼才來救我!”盧士翰大哭著撲向盧新知,坐實了他的份。
來人正是盧夫人在源縣頤氣指使的底氣,盧縣令的堂兄。
“孽障!居然蠢到被刁奴蒙蔽!”盧新知狠狠給了兒子一耳,痛罵道,“還不快跪下認錯!”
“再敢胡言語,為父就把你逐出家門!”
盧士翰徹底傻了,頂著對稱的兩個掌印癱在地上,瑟瑟發抖。
“盧新知,你有何冤屈,想要狀告何人?”盧縣令公事公辦的問話,心中已經猜到這位堂兄姍姍來遲的緣由。
果不其然,盧新知唱作俱佳地控訴了一番刁奴蒙蔽良主的冤。
他將所有事,都推到欺上瞞下的月桃上,而盧夫人和盧士翰,所犯最大的錯誤就是愚蠢和輕信。
盧新知長相端正,氣質儒雅,雙目含淚的模樣活就是一個痛心不已的無助慈父,很快就贏得了大部分圍觀百姓的同。
擔驚怕多時的盧夫人有了主心骨,也登上戲臺,邊咳邊為兒子求饒。
Advertisement
“大人,若是翰兒有罪,民婦愿代子過。”
“子不教父之過,要罰也該是我這個做父親的。”盧新知扶住妻子,聲音哀切。
盧縣令從善如流,淡淡道:“盧士翰年,的確不宜杖刑。”
“二位愿代子過,本甚是。來人,帶他們下去,一人杖刑五十。”
“至于流放之刑,一家三口共同分擔的話,就往北走一千里吧。”
剛被盧新知夫妻虛偽的戲碼惡心到的程小棠,聽到盧縣令這般諒民意,差點沒笑出聲。
這算水平,不愧是民如子的好。
剛帶人趕回來的程翠兒,恰好看到這一幕,手攔住躍躍試的一名男子,“不急,再等等。”
衙役們手腳麻利,很快就抬來了兩條行刑用的長凳。
“等,等下!”盧夫人鬢發凌,慌忙找借口,“我心口疼,不了。”
盧新知暗暗拳頭,往外面遞了個眼神。
人群中立即傳來一聲蒼老的怒罵,“月桃!你還不認罪,是想全家抬不起頭做人嗎?”
月桃渾一抖,就看到怒目圓睜的祖父,也是盧府的管家。
是盧府的家生子,全家的賣契都在盧新知手里。流放三千里或許還有活路,要是違抗盧新知,祖父絕對會活活打死。
“大人,奴婢認罪。”月桃絕地閉上雙眼。
張德和李康二人,順著聲音,看到老管家領著他們的家人到了大堂前,當即俯首認罪。
這麼一來,盧夫人無罪,盧士翰也從主犯變人蒙蔽的從犯。
最終主犯月桃維持原判,杖刑一百,流放三千里。
張德和李康誣告程天福當街傷人,杖刑四十,拘役一年。
念在從犯盧士翰年,流三千里可依照“折杖法”折為脊杖二十,杖一百。
盧新知趁機提出以錢贖罪,減輕罰。
在付出五百石大米和三百石小麥的巨額代價后,落到盧士翰上的最終罰是杖三十,他人不得替代。
鑒于盧家為賑災做出的貢獻,盧縣令法外開恩,允許盧士翰分三次刑。
就是手的衙役太老實,打得盧士翰哭爹喊娘,皮開綻。
聽著兒子的慘聲,盧新知的臉難看至極,卻不得不咬牙出愧之。
對于這個結果,程小棠可以說滿意極了。
心里有數,盧士翰才十一歲,哪怕是包青天再世來斷案,也不會真讓他流放三千里。
更何況指控他人盜,本就是可大可小的事,說是眼花看錯都行。
若不是盧夫人太過囂張跋扈,自恃是盧縣令的堂嫂,非要鬧上公堂,本不至于付出這麼慘痛的代價。
北方連年大旱,一斗米已經漲到一百二十文,一石就是一兩二錢銀子。
程小棠隨便一算,都替盧新知到疼,難怪再怎麼裝模作樣,臉看起來都像是吃了大便一樣難看。
反觀盧縣令,氣明顯見好。
蒼白的臉上浮現出淺淺的紅暈,眼神出掩飾不住的喜悅,就差寫著“得償所愿”四個大字。
看來他們老程家遭這一回罪,是替盧縣令劫富濟貧了。
不過浪費這麼多時間,程小棠也不想空手而歸,湊到程天福耳邊小聲道:“大哥,我要去罵壞人。”
程天福心疼妹妹了大委屈,自然無所不應,抱著往盧氏夫妻邊上走了幾步。
“盧老爺,盧夫人,你們以后不要再被刁奴騙了,那樣會破財的。”程小棠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寫滿了“幸災樂禍”,語氣卻很真誠。
盧新知撐著謙遜的表,啞聲道:“今日我兒多有得罪,還見諒。”
“你——”盧夫人眼前一黑,又嘔出一口。
【宿主行為寵盧新知一次,獲得一千八百積分。】
【宿主行為寵夏書萱一次,獲得兩千五百積分。】
城里人氣可真大。
程小棠慨著,轉向被打得屁開花的盧士翰,卻發現他已經疼暈過去了,只得作罷。
四千三百積分能兌換不好東西了,不比盧縣令收獲。
“這就開心了?”謝玲花好笑地兒的臉,止不住后怕道,“你呀,也不知隨了誰,膽子這麼大。”
程大牛驕傲道:“當然是隨我。”
一家人低調地站在角落等看熱鬧的百姓散去,互相安著,臉上都出了劫后余生的笑容。
這次是不幸中的萬幸,遇上了好。
“翠兒姐姐,抱。”程小棠對著程翠兒手,悄悄將牌令放回懷里,咬耳朵道,“我沒讓人看到哦。”
乖巧中帶著得意的小模樣,看得程翠兒心都要化了,“棠寶真棒。”
原本站在邊的男子,聽到程翠兒哄孩子的嗲音,打了個冷戰,默默地混人群中離開。
“幾位稍等,縣令大人有請。”宋差攔住了程家人的去路。
猜你喜歡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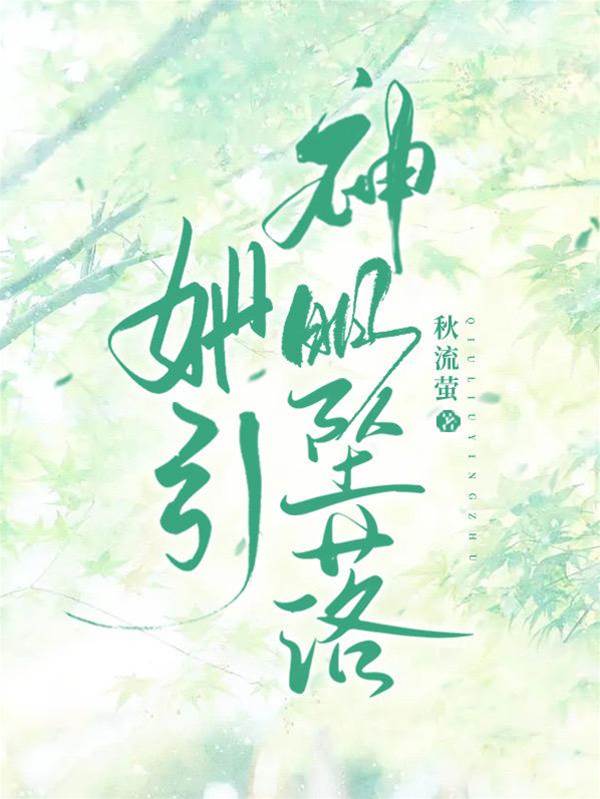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69 章

溫先生的心尖月
(蓄謀已久 細水流長 甜寵 雙潔 無虐 年齡差五歲左右)(女主醫生,非女強)*【溫婉清麗江南風美人 & 內斂沉著商圈大佬】容煙出身書香門第,自小跟隨外公生活。聽聞外公給她尋了門親事,她原以為聯姻對象是同為醫生的溫二公子,殊不知卻是接管溫家的溫景初。煙雨灰蒙,寺廟裏,容煙瞥見與她擦身而過的男人。上一次見他還是四年前,可他從不信神佛,為何會出現在這裏?朋友生日聚會結束,溫景初送她歸家。車內,容煙壓住心中疑惑,終究沒問出口。*容煙本是溫吞的性子,喜靜,信佛。她自認為婚後的兩人是相敬如賓,搭夥過日子。而他卻步步誘她淪陷。某日,容煙在收拾書房時看到了寺廟的祈福袋,裏麵白色宣紙上寫著她的名字,似乎珍藏了許久。而此時溫景初正接受電視臺采訪,清肅矜貴,沉穩自持,淡定從容與人交談。主持人問,“溫先生,聽聞您並不信神佛,但為何每年都到靈山寺祈願?”容煙手中拿著祈福袋,略帶緊張的等待著他的回答。男人黑眸如墨,思忖片刻,緩緩啟唇,“因為溫太太信佛。”簡單一句話卻擾亂她的心。
33.1萬字8.09 265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