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聞中的家主大人》 第100章 第一百章
看來這一帶都歸奔雷手負責搜查,位居道通衢所在的青水鎮就是他的落腳點。
阿虎想湊上去,起先被府兵攔下,隨后奔雷手命府兵放開,招招手讓阿虎到他邊。
“快走。”
幾乎是同一時間,姜九懷拉起,快步向鏢局走去。
后傳來奔雷手的大聲疾令:“你們都給我聽著,賊人就在這座鎮子里,給我一家一家搜!所有面生的男子,一個都不要放過!報訊舉發者,重重有賞!”
姜家府兵轟然應聲,他們鎧甲森然,勢不可擋,整條街上頓時兵荒馬,飛狗跳。
元墨和姜九懷快步把這一片混甩在上。
元墨一面走,一面看向姜九懷。
他的臉在冪籬中,看不真切。
想,可能錯了。
的聲音有點發,“阿九,怎、怎麼辦?”
他一定有辦法吧?
他明明那麼肯定地說了“犯險也無妨”,一定是有應對之策。
“快。”姜九懷道,“只有快。趕在奔雷手追查到鏢局之前,離開青水鎮。”
這不是辦法,這是賭命!
元墨心里像是狠狠被貓爪撓了一下,終于明白,姜家的奪位之爭是真刀真槍海尸山里堆出來的,本容不下半點一念之仁。
難過得快要哭過來:“阿九,我……”
“放過他的人不是你,是我,你無需道歉。”姜九懷腳下不停,“若我昨晚滅了口,你定會難過。若你難過,我便會后悔。所以,你現在不用疚也不用難過,因為犯險是我自己的選擇。”
后一片喧囂,他的腳步很快,語速也很快。
元墨卻覺得一切好像都慢了下來。
把他的每一個字掰開爛了聽,真正明白了他的意思。
Advertisement
滅口是上上之策,一舉鏟除,永無后患。
但,他不想難過,所以,寧愿以犯險。
元墨的眼睛迅速泛紅,還好有冪籬擋住,看不見。
深吸一口氣,用力回握姜九懷的手,加快腳步將他帶往鏢局。
放心吧阿九,就算拼了這條命,我也一定會讓你回到揚州。
府兵們一時還沒搜到東邊,鏢局附近尚算安靜,車夫們靠著車轅聊天,見到元墨和姜九懷往這邊來,便有人上來問要不要用車,去哪里。
姜九懷道:“清江。”
這答案出乎元墨的意料之外,不是應該去揚州嗎?
“哎呀,清江可不近吶,這會兒總得酉時才能到,我還得住上一天才能回來……住一宿,外加三餐,還要馬兒要吃料,兩位小娘子,這趟至得十兩銀子。”
這分明是敲竹杠,若換了平時元墨一定同他理論,但這會兒哪怕他說一百兩,也不會說半個不字,點點頭就上了車。
阿彌托佛,菩薩保佑,不管是揚州也好清江也好,馬上離開這個青水鎮!
可就在馬車掉頭的時候,后面忽然傳來一聲暴喝:“所有馬車,全給我停下!”
元墨本就是渾繃,這一下險些跳了起來。
姜九懷按住的手:“鎮定。”
他的手照舊微涼,聲音卻很溫和,元墨深吸一口氣,不錯,越慌張,越容易出馬腳。
車夫停了下來,府兵呼喝著讓車夫和客人全都下車。
一下車,元墨就看到了奔雷手,忍不住再次僵了僵。
別的府兵也許好糊弄,但奔雷手可是見過和姜九懷的。
府兵把鏢局的人全都了出來,烏泱泱地在門前站了一大片人。
府兵喝問:“有沒有去揚州的馬車?出來!”
元墨這才明白姜九懷報給馬夫的目的地為什麼是清江。
奔雷手自然會循著揚州這條線去找,因為無論如何,姜九懷的目的地都是揚州。
去揚州的客人和馬車立刻被被拉了出來,有人稍加反抗,便換來一頓拳打腳踢,鏢局的鏢師看不過去,想要手,他的人按住他,低聲道:“莫惹事!那可是姜家!”
一個七八歲的小孩被嚇得哭起來,母親摟在懷里,又急又怕:“別哭,別哭。”父親急壞了,手去捂小孩的。
小孩哭得越發厲害。
元墨陶出一只胭脂盒子,遞給小孩:“送給你,要不要?”
但凡是孩子,沒有不喜歡這些的,何況這胭脂盒子上面描著艷的牡丹花,十分好看。
小孩子一下子忘記了哭,呆呆地著胭脂盒。
元墨把胭脂盒往前遞了遞,小孩正要接,一只手卻比快一步,接過了那盒胭脂。
那只手比常人的要大上一圈,小扇也似,元墨毫不懷疑,被這樣的手拍上一下,一定能人五摧傷而死。
“喲,這位爺這是做什麼呀?”元墨聲道,“這是奴送給這小妹妹的,可嚇壞了。”
奔雷手擰開胭脂盒,里面確然是胭脂,并無異樣。
他沉聲:“去哪里的?”
“回大爺,去清江。”
“去清江做什麼?”
“找人。”
“找什麼人?”奔雷手問,“你們又是哪里人?”
元墨頓住了。
“有什麼不能說的麼?”奔雷手聲音猛然抬下,“摘下冪籬!”
姜九懷微微抬起左手。奔雷手定知他有金麟,能不能一擊得手,姜九懷也沒有多大的把握。但此時此刻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元墨猛地回,撲到上,看起來像是害怕得不得了,實則剛好按住了姜九懷的手,尖聲哭道:“姐姐怎麼辦?看來是坊主報了,他們是來抓我們的!”
奔雷手皺眉道:“怎麼回事?我們不是抓伎的。”
“當真?回大爺,我們是揚州月心庭的伎,老坊主死了,新坊主又把花魁賣了,眼看接下來就要打發我們,我們也不知會被賣到哪里,實在是怕得不得了,只好趁夜逃出來,想往清江去找衛公子。”
元墨說著摘下冪籬,出一張面孔,努力哭了這一陣,淚水沖化了妝容,哭得五扭曲,大概紅姑過來都認不出。
甚至很有誠意,連阿九頭上的冪籬都摘了下來。
見如此自覺,奔雷手疑心去了大半,略瞧了“另外一名伎”一眼,只見“”發垂在兩頰,臉上濃妝艷抹,倒也有幾分人心,確實配得上月心庭的名頭。
他問:“哪個衛公子?”
“就是衛家的衛子越公子,聽說他在蘇州府的清江縣當兒。當初他最喜歡我們姐妹倆了,他為人又好,出手又大方,一定會為我們姐妹贖的!”
衛家獨苗衛子越出手大方是全揚州都知道的事,月心庭也是剛剛換了主人,這一切都對得上。
元墨瞧出奔雷手神已經放松,再加上一劑猛藥,撲上去抱住奔雷手的,“大人您就行行好放過我們吧!我們也不圖大富大貴,只要能長伴衛公子左右,這輩子就心滿意足了……只要您放了我們,我們都可以為你做……”
這一蹭,一來蹭糊了自己的妝,二來把脂及鼻涕眼淚都蹭到奔雷手的擺上,奔雷手一把年紀了,還穿著一白,顯然十分潔,頓時一腳踹開了元墨:“滾!”
元墨如奉綸音:“謝大爺開恩!大爺一定長命百歲!”
一面說,一面拉著姜九懷麻溜地滾了。
姜九懷過面紗,深深地看了奔雷手一眼。
奔雷手沒有注意這一下回眸,他正用手帕擺上的污痕。
待所有人被搜問完畢,已經是大半個時辰后。
奔雷手帶著人前往下一。
馬車重新上路。
元墨長長地松了一口氣,十分慨:“哇,會哭真好。”
發現那干枯了十多年的淚水好像在那水岸邊被激活,只要再想到姜九懷當時躺在岸邊無知無覺的樣子,它們就能嘩嘩往下掉。
十分好用。
姜九懷沒有說話,手去的擺。
元墨下了一大跳,車廂狹窄,躲也躲不過,擺被到膝蓋,出小。
小潔修長,只是多了一塊微微發紅的痕跡,要不了多久,這微微紅便會轉為瘀青。
正是方才被奔雷手踹著的位置。
姜九懷的手指,輕輕過那一塊位置。
元墨強忍著他的手帶給的一片戰栗,趕將子放下去。
“我要殺了他。”姜九懷低低地道。
這點元墨相當贊同:“對,連他的主子一起!”
馬車線黯淡,姜九懷看著,眸子里面有什麼東西浮浮沉沉,終于凝結一種非常非常深沉的溫。
之前那一幕又一次涌進腦海,他的眼中閃過一凌厲的痛楚。
明知是演戲,明知那只是的手段,他心中還是恨極。
他是父親唯一的兒子,生來就知道自己將來會是姜家的家主,那個位置對他來說天經地義,沒有驚喜,也沒有期待,即使是這次回揚州,也是復仇多過于奪權。
但此時此刻,他想要那個位置。
只有將姜家牢牢地抓在手中,他才能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才能撐出一方天地,讓元墨不用向任何人低頭,免一切風雨。
不一時到了中午,歇腳的時候,車夫門路地跟元墨兩人套近乎:“原來兩位姑娘是去找衛大人吶!你們可真是找對人了,咱們有緣吶!衛大人我著呢,每個月都要打從他府衙后門過……”
元墨問姜九懷:“咱們真要去清江?”一直以為姜九懷說去清江只不過一個幌子。
姜九懷點頭:“找衛子越。”
“找衛子越干嘛?”
“盡其用。”
元墨:啥?用什麼?怎麼用?
猜你喜歡
-
完結1099 章
鳳女重生:侯爺夫人要複婚!
前世,許瑾瑜將豺狼虎豹當成了良人,闔府被斬首,自己也落得個葬身火海的下場。最後她才知,那個冷心冷情的人將自己愛到了何等地步。重活一世,許瑾瑜想要馬上上了花轎,跟那人和和美美的過完這一生。可是還冇走兩步,就看到了那人,一本正經的說道。“雖家父與叔父早已有言在先,可婚姻大事並非兒戲,既大姑娘不願,我亦是願意就此解除婚約。”許瑾瑜握緊了自己的小拳頭,眼裡起了一層薄霧,直接噠噠噠的走了過去。“侯爺戰功顯赫,為世人敬仰,理應知道流言不可儘信,現如今又怎可因為流言就要解除婚約呢?”孟敬亭冷心冷情,從未對任何人動過心,可是卻被這眼前的小姑娘給軟了心腸。
131.7萬字8 50226 -
完結77 章

奪金枝(重生)
虞莞原本是人人稱羨的皇長子妃,身披鳳命,寵愛加身。 一次小產后,她卻眼睜睜看著夫君薛元清停妻再娶,將他那個惦記了六年的白月光抬進了門。 重活一次,本想安穩到老。卻在父母安排的皇子擇婦的宴會上,不期然撞進一雙清寒眼眸。 虞莞一愣。面前此人龍章鳳姿,通身氣度。卻是上輩子與薛元清奪嫡時的死敵——模樣清冷、脾氣孤拐的的薛晏清。 迎上他的雙目,她打了個哆嗦,卻意外聽到他的一句:“虞小姐……可是不愿嫁我?” - 陰差陽錯,她被指給了薛晏清,成了上輩子夫君弟弟的新娘。 虞莞跪于殿下,平靜接了賜婚的旨意。 云鬢鴉發,細腰窈窕。 而在她不知道的上輩子光景里—— 她是自己的長嫂,薛晏清只能在家宴時遠遠地看她一眼。 再走上前,壓抑住眼中情動,輕輕喚一句:“嫂嫂。” 【又冷又甜薄荷糖系女主x內心戲起飛寡言悶騷男主】 1V1,男女主SC 一些閱讀提示:前期節奏有些慢熱/女主上輩子非C,介意慎入 一句話簡介:假高冷他暗戀成真。 立意: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20.2萬字8 39694 -
完結139 章
我以為我拿的救贖劇本
一朝穿越,虞闕成了修真文為女主換靈根的容器。好消息是現在靈根還在自己身上,壞消息是她正和女主爭一個大門派的入門資格,她的渣爹陰沉沉地看著她。虞闕為了活命,當機立斷茍進了一個不知名的小門派。入門后她才發現,她以為的小宗門,連師姐養的狗都比她強…
62.6萬字8.33 16859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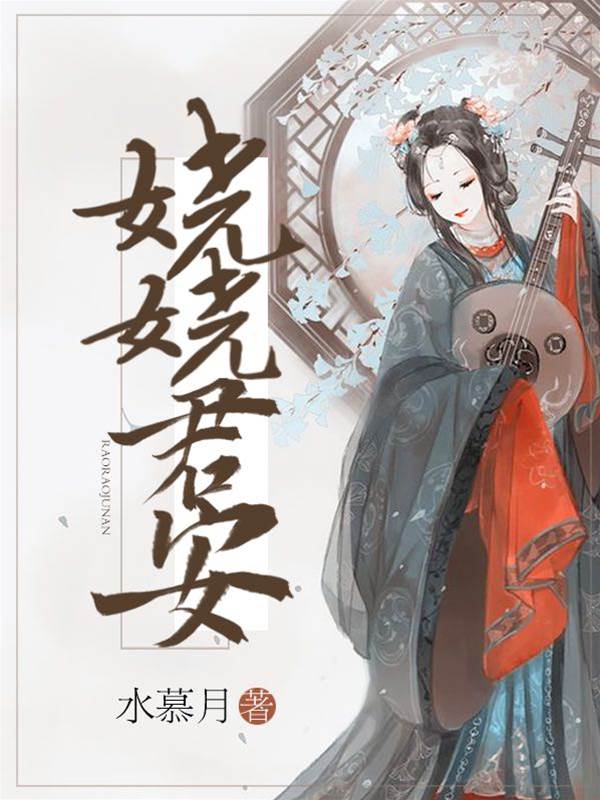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