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誘餌》 第85章 不敢見我
陳淵送張理回醫院,又直奔公司,途經一家咖啡廳,一個男人招手。
他泊住,降下車窗,“胡醫生。”
對方很謹慎,蒙得嚴嚴實實,“我助理已經調包了。”
“確認無誤嗎。”
男人說,“我親自帶的學生,沒問題。”
陳淵點頭,“林鶴公然違規,東窗事發后,他的下場是停職,由你取代他一鑒的位置。”
男人興不已,“我信得過陳總,只要我擔任一鑒,任何鑒定項目,我甘愿為陳總效勞。”
陳淵沒回應,駕車離去,男人也迅速上車。
櫥窗旁的灌木叢后,相繼走出兩名男子,后面的冷笑,“胡崇早就覬覦我的位子,果然按捺不住了。”
他看向前面的男子,“您要我怎麼做。”
“正常鑒定,不再手腳。”
林鶴問,“胡崇又換了樣本,換了誰的?”
男子不慌不忙豎起大的領,“自然是我父親。”
“那...萬一結果。”林鶴沒說下去。
男子笑著,“陳淵請君甕,一定沒想到甕捉他自己。”
***
當晚,沈楨下班,駛過小區花壇被一輛車停。
瞟了一眼捷豹,在灰蒙蒙的路燈盡頭,男人半張臉若若現。
米白的高領,銀藍的羊絨外套,是沈楨最他的模樣。
近乎冬季的冷冽,天際晦暗沉,屬于這座城市最復古憂傷的8點鐘。
這一切太潦倒,太落寞。
陳崇州就在廢墟一般荒蕪的世界里,演繹他的華麗。
他發梢淋淋,烏黑而潤,額間淌著一滴水。
喬麗說,男人長相溜水,都花里胡哨,不安分。
可驗是真棒。
他們會,會演,會吻。
之后再談的男人,總索然無味。
Advertisement
至沈楨沒見過,比陳崇州更會把控人心的男人。
比劃手勢,示意他挪車。
他沒,揭過虛無混沌的,著。
公子哥全有一病,甩人行,被甩,咽不下這口氣。
沈楨目不斜視,拐彎倒三米,強行超車。
尖刺的聲在耳畔炸開,發力失控,險些側翻,驚慌失措踩剎車。
捷豹當即一橫,頂向車頭,堪堪穩住。
陳崇州也熄了火,胳膊搭在窗框,慵懶得很,“知道RF俱樂部麼。”
二代子弟最燒錢的銷金窟,超一流家才玩得起,千萬級的豪車,名下起碼三輛,方有資格會。
破產了,水了,一律踢出局。
易名就那圈子玩的,漂移,越野,專業賽車手都打不贏他。
陳崇州漫不經心叩擊方向盤,“我是會長。”
沈楨面發青,深吸氣。
“連任三屆。”
丟人丟大發了。
竟然搭錯筋朝他炫車技。
沈楨解安全帶,下車。
陳崇州也下來,攔住,“你服在我那。”
昨夜突然鬧掰,胡打包了行李,沒仔細翻柜,是留下幾條子。
貴的,牌子貨。
不值錢的服,沒往他那拿。
畢竟階級懸殊,再穿得太寒酸,也沒底氣了。
“我空回去。”
陳崇州點煙,空氣太,火苗一冒頭,無聲熄滅。
他騰出一只手捂住打火機,用力嘬,腮骨繃,下頜線抻得筆直,更清俊幾分。
“故意落下,借機回頭。”他帶點戲謔氣。
沈楨沒解釋,調頭走。
“你沒錯?”陳崇州扼住手腕,“去陳淵那住幾次了,關系合適麼。”
“你和倪影暗度陳倉,騙我幾次了?”沈楨忍無可忍,“又給你戴綠帽了,你刺激了?”
“除了你,誰還給我戴?”他銜著煙,噴出一團霧,一秒融化。
“服我不要了,麻煩你扔了。”
掙扎,要離。
陳崇州皺了下眉,煙霧散得快,架不住他吸得猛,一口接一口,縷縷纏繞。
面容淪陷在霧里,極為深沉,英朗。
“不分,行不行。”
沈楨一不。
他碾了煙,“我不見,喬藤管。”
“你心里惦記。”
陳崇州悶燥,“你挖開看了?”
偏頭,“我害怕打雷,怕黑,你在病房陪倪影,你想過我嗎?”
細的雪刮過,沈楨頭頂白了一片。
“你給治病,照顧,你是醫生,我索相信你,你坦白報備一下很難嗎?醫院沒有護工,家人也死絕了,是嗎?非要前男友陪護,整整兩晚。”
他沉默片刻,“不分,行麼。”
“你大方坦,我不會無理取鬧,你藏著掖著,我對你沒信任了。”
出自己手,進樓道。
“沈楨。”陳崇州在后喊,“我只低這一回。”
樓梯上的人腳步沒停,消失在黑暗里。
他倚著車門,撥通訊錄。
廖坤休假,睡得迷迷糊糊的,電話掛斷又打,那頭比他戾氣,“想轍。”
“吹了?”他翻個,“我提醒過你,前友是炸彈,尤其倪影,天底下的現任都忌諱,那攻擊太大了,你執意瞞著,我沒轍。”
沒說完,廖坤開始笑,“一降一啊,這些年多人為你要死要活,栽跟頭了吧。”
陳崇州抬起頭,看那扇亮燈的窗戶。
人拉窗紗,影一閃而過。
似乎,躲在簾后。
窺他。
***
次日,沈楨進公司,們正圍在一起議論,姜彤一擰大,“小的比大的帥,我喜歡白凈斯文的。”
對面的同事反駁,“深有男人味兒,普遍大,力強。上周五,我去總經辦報賬,大陳總腰腹那線條,襯都包不住。”
“想啊?年會灌醉他,有膽子直接睡,大陳總還告你不?”們起哄大笑。
沈楨整理文件夾,姜彤拍桌子,“大小那兩款,你吃哪款?”
“什麼大小?”
姜彤瞪眼,“大陳總,小陳總啊。”
面不改,“和咱們無關,陳總訂婚了,陳渣...”一噎,及時收住,“陳經理也不到你。”
“那眼饞總行吧,誰不喜歡好看的男人呢。”姜彤晃悠著椅子,“王兆他們說,你認識小陳總,郊區那塊工程,你和他膩乎了半個月?”
“胡扯。”沈楨坐下,寫材料,“他那樣份,你以為人想膩就膩?”
姜彤一琢磨,“也對,你離異的,他瞧不上。”
沒多久,前方發一陣,沈楨沒太當回事,倒是姜彤,激拉,“小陳總!”
作一頓,“在哪?”
“財務室查賬呢,富誠集團五百萬以下的項目,從晟和走賬。”
沈楨站起來,“我去飲水間泡咖啡,你捎一杯嗎?”
姜彤驚奇,“你不看帥哥啊?巨帥。”
話音未落,聲至門口。
正中央的男人系著領帶,涂了發蠟,短發固定住,利落有型。
他穿正式的西裝,比醫生那副裝扮顯得更為,有氣場。
那種,煥然一新的制服。
仍舊從他骨骼里滲出的,卻不是單調的清冷,而是濃,烈,厚,也艷。
艷是形容一個男人最高層次的氣質。
獨特,復雜,各異的風。
像兩截然不同的韻味,在靈魂里撞擊,激,慢慢浮于皮囊。
剎那勾住人的味道。
陳崇州環顧一圈,不知在搜尋誰,招待他的公關經理主說,“陳總傍晚有飯局,白天休息。”
沈楨沿著墻角,趁逃離。
“去哪。”
他停下,對準背影。
男助理和司機候在原地,陳崇州靠近,音量剛夠彼此聽清,“不敢見我?”
渣之神。
分都分了,不讓痛快。
沈楨轉回,“陳經理,中午好。”
他意味深長打量,“這麼客氣,不是掐我的時候了。”
“你胡謅啊。”警告。
陳崇州笑了一聲,“嗯,這狗脾氣最像你。”
沈楨看著他,毫無征兆鞠躬,額頭重重嗑在他膛,這下,砰地一震,震得眼花,也震得陳崇州肋骨劇疼。
他抿。
是狠。
最初就是被這又純又又野的勁兒吸引了。
不過,嗑得比他嚴重,眉骨上半寸,淤青一塊。
“傷敵八百,自損一千。”陳崇州傾,挨側臉,“傻?”
沈楨著,沒理他。
他不發笑,腔微微起伏。
確實狗脾氣,說咬就咬。
姜彤忽然沖上去尖,“小陳總,我們是舊相識!”
陳崇州略退一步,疏離。
“我爺爺姜大牙!前-列腺癌晚期,是你主刀的,多活了半年呢。”
他沒印象,淡笑,“是麼。”
“簽個名吧。”姜彤十分虔誠,雙手捧著紙,“清明節燒給我爺爺,他生前最激你了。”
沈楨撇開臉,要走。
“站住。”
陳崇州越過姜彤,在一旁盯著。
沈楨被盯得發,“這是公司,咱倆的私事別在大庭廣眾聲張。”
“還自。”他不咸不淡移開視線,“我來取合同。”
“那你抓著我不放——”
陳崇州彎下腰,撿起一枚耳環,遞到面前。
耳環是他七夕節送的,藏在漱口杯里,沈楨早晨洗漱才發現,他從背后抱住,問喜歡嗎。
他去外市出差,見李妍那次,買了項鏈,還買了這對耳環,連廖坤也不知道。
當時,其實于冷戰期。
陳崇州這人,生來涼薄,心腸也,但渣歸渣,他對人的品不毒。
五毒俱全的至尊渣,既占人的便宜,又野花,最終還PUA,倒打一耙。
他不是那款。
陳崇州肯在人上出,不算計金錢,一天沒分,就盡一天的義務。
這點,不多見。
沈楨手接住的同時,他方向一偏,也撲了個空。
“沈小姐,以后不要自作多,曲解男人的意思。”陳崇州邊噙一笑,松開,冰涼的耳飾墜在掌心。
那別有深意的調侃,沈楨臊得臉漲紅,手向下,耳環又掉落,“我不稀罕了。”
他挑眉。
“渣男虛假意。”撣了撣手,“不要也罷。”
扭頭撤。
陳崇州也惱了,拽住,“哪個渣男花六位數玩虛的?”
“原來陳總如此了解渣男的行。”沈楨笑容明,“像腳踏兩只船的渣男,人該怎麼對他?”
陳崇州瞇起眼。
許久,“你綠沒綠我。”
“沒綠。”
“我沒踩兩只船。”
沈楨甩開他手。
喜歡他的長念舊,他對倪影長,對后來的友,也同樣。
可不喜歡他斬斷不了,將舊廝混進新中,為另一個人撒謊擔憂,夜不歸宿。
“和神,我都無法接不純粹。”
陳崇州眼底涌著寒意,“不接我,接陳淵和周海喬,對麼?”
這年紀,誰心中沒藏個人,沒藏一段。
接不了他,倒能忍他們。
這時,安橋匆匆趕來,“陳經理,還有一份隸屬晟和的報表,您過目。”
他接過,隨意翻看,“在什麼部門。”
安橋掀眼皮一掃,“沈小姐市場部,主管調研和談判。”
陳崇州審閱完,在末頁簽字,“有酒局麼。”
“陳總特意打過招呼,沈小姐不必陪客戶應酬。”
他睥睨安橋,沒說話,揚長而去。
從晟和出來,陳崇州去了一趟總醫院。
在何佩瑜的病房,上陳智云帶著倪影過來探視。
氣恢復不錯,耐人尋味同他對視,“智云,你不介紹嗎。”
陳智云了一眼,“老二,你認得,倪影。”
不滿意,再次提示,“我是你什麼人?”
何佩瑜坐在床上,表不太好,陳政對于倪影的出現,神也微妙,“智云,你一把歲數了,也學年輕人胡鬧嗎?”
陳智云說,“大哥,我們婚前公證了。”
陳崇州和倪影肩之際,小拇指不著痕跡他手背,似有若無的一句挑逗,“刺激嗎。”
他停住,看地面。
“征服你二叔的人呢?”
。
倪影在暗示,清楚何佩瑜那點不堪揭的底細。
陳崇州波瀾不驚往里走,“父親,母親,二叔。”又轉向陳淵,“大哥。”
陳淵含笑,“老二,有一件神奇的事,昨天在華司鑒定機構的辦公室,我遇到一個與你七八分相似的男人。”
陳政的目從那邊挪向陳淵,蹙眉。
【作者有話說】
謝Marmalade打賞虎虎生威,旺財打賞催更符,打賞3朵鮮花
謝林深時見鹿、書友85052、以馬利、ioumylovery、好聽的id、??漫畫小說的四姐姐、值得、小逗貓、好吧那你報警吧??、念想、星球限定打賞金幣
謝大家投票支持~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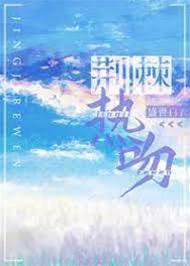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2033 章
盛世婚寵:帝少難自控
她的孩子還未出世便夭折在肚子裏!隻因她愛上的是惹下無數血債的神秘男人!傳聞,這個男人身份成謎,卻擁有滔天權勢,極其危險。傳聞,這個男人嗜他的小妻如命,已是妻奴晚期,無藥可治。他說:夏木希,這輩子你都別想從我身邊逃開!你永遠都是我的!她說:既然你不同意離婚,卻還想要個孩子,那就隨便到外麵找個女人生吧!我不會怪你。五年後她回來,發現那個男人真的那麼做了。麵對他已經五歲的孩子時,她冷冷地笑著:秋黎末,原來這就是你放棄我的原因?那時她不知道,這個男人已丟掉了一隻眼睛……而這個五歲的孩子,竟也滿身是謎!——那是夏與秋的間隔,夏的末端,是秋的開始。秋,撿到了失意孤寂地夏的尾巴。夏,許諾終生為伴,永不分離。經曆了離別與失去,到那時,秋,還能否依舊抓住夏的氣息?
566.6萬字8 14283 -
連載1657 章

雙寶媽咪是大佬顧挽情
五年前,顧挽情慘遭未婚夫和繼妹算計,與陌生男子共度一夜,母親因此自殺,父親嫌她丟人,將她驅逐出家門。五年后,顧挽情帶著龍鳳胎回歸,一手超凡醫術,引得上流社會無數人追捧。某德高望重董事長,“我孫兒年輕有為,帥氣儒雅,和你很相配,希望顧神醫可以帶著一雙兒女下嫁!”追求者1:“顧神醫,我早就仰慕你,傾心你,希望可以給我個機會,給你一雙兒女當后爸,我定視為己出。”
166萬字8 338525 -
完結442 章

把她送進監獄後,慕少追悔莫及
慕南舟的一顆糖,虜獲了薑惜之的愛,後來她才知道,原來一顆糖誰都可以。一場意外,她成了傷害他白月光的兇手,從京都最耀眼的大小姐,成了令人唾棄的勞改犯。五年牢獄,她隻想好好活著,卻背著“勞改犯”的標簽在各色各樣的人中謀得生存。再遇慕南舟,她不敢愛他,除了逃,還是想逃!慕南舟以為他最討厭的人是薑惜之。從小在他屁股後麵跑,喊著“南舟哥哥”,粘著吵著鬧著非他不嫁,有一天見到他會怕成那樣。他見她低微到塵埃,在底層掙紮吃苦,本該恨,卻想要把她藏起來。她幾乎條件反射,麵色驚恐:“放過我,我不會再愛慕南舟了!”慕南舟把她禁錮在懷中,溫柔纏綿的親她:“乖,之之,別怕,叫南舟哥哥,南舟哥哥知道錯了。”
85.7萬字8 63357 -
完結561 章
離婚后孕吐,總裁前夫追瘋了
隱婚三年,他甩來離婚協議書,理由是他的初戀回來了,要給她個交待。許之漾忍痛簽字。他與白月光領證當天,她遭遇車禍,腹中的雙胞胎沒了心跳。從此她換掉一切聯系方式,徹底離開他的世界。后來聽說,霍庭深拋下新婚妻子,滿世界尋找一個叫許之漾的女人。重逢那天,他把她堵到車里,跪著背男德,“漾漾,求你給我一次機會。”
117.1萬字8 257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