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小撩精》 第25章 第25撩(一更)
就在鹿笙還杵在門后深有所思的時候,一樓的門開了,簡士抱著英寶寶站在門口:“怎麼這麼早就回來啦?”這才十二點多啊!
鹿笙笑了笑,尷尬又不知所措地在想要找個什麼樣的理由。
簡士已經走到邊:“吃飯了嗎?”
點頭:“吃過了,在食堂吃的。”
這時候,樓上傳來門開鎖的聲音,簡士回頭看了眼,視線收回來的時候,小聲問:“和懷璟一塊回來的呀?”
“嗯。”
既然是在食堂吃的,兩人又是一塊,那估計是家南教授特意送回來的!
不然這小子不可能大中午的回來!簡士在心里樂。
沙發里,南懷璟安靜地坐著。
是表面看似很平靜,但心里卻波濤洶涌的那種。
他覺得自己大概是瘋了。
竟然拉一個人作擋箭牌,還在那麼多人面前。
簡士說他不紳士。
對,簡士說的很對,他的確不紳士,他所有的紳士都是假象,他不喜歡那些人的靠近,特別是在他拒絕后仍不死心,還將自己的心袒于他的靠近。
他以前沒拒絕人,可從來都是禮貌有涵養的,可是今天,他當著那麼多人的面給了周曼那麼大的一個難堪。
可是除了讓周曼沒有臺階下,他還讓鹿笙陷流言。
不過一個午飯的時間,他就讓兩個人為‘眾矢之的’。
還禮貌嗎?
還紳士嗎?
還是別人眼里的翩翩君子嗎?
正常的社禮儀而已,可那些人為什麼要給他安這麼多的帽子?
他從沒有那樣自詡過自己。
如今自己這麼做,再想想自己在那些人眼里的形象。
那畫面就像在眾目睽睽之下給自己銬上手銬。
南懷璟這一坐就坐到了點,虛掩著的門傳來低低哀哀的一聲“喵嗚”。
Advertisement
南懷璟從沙發里起,門開,英寶寶支著兩只前爪,擱在地上的那條茸茸的尾,在輕輕地搖,看見門開,英寶寶抬頭看他。
和那雙圓圓的、澄藍的眼睛對視兩秒后,南懷璟突然失笑了聲。
他在門里側蹲下來,出右手,并攏四指朝它招了招手。
英寶的尾不搖了,歪著渾圓的腦袋看他。
別說,這怔怔懵懵的表,和中午還真是有幾分像。
他眉心悄悄的、不自察地往一起攏。
不知中午有沒有看出來他坐到對面的用意。
點半的時候,南懷璟接到院長電話。
聽見樓關門的聲音,鹿笙從客廳出來,看著他從樓道里出來,看著他腳下步子邁的很大地徑直走向門口,鹿笙不自覺地輕咬下。
五分鐘后,鹿笙也下了樓。
以前鹿笙去咖啡店總坐里面的位置,這次,選擇了窗邊。
不知是不是因為工作日的原因,咖啡店里人不多。不過,剛剛點單的時候,看見吧臺里有不打包好的訂單。
耳邊一如既往的放著舒緩的,讓人聽著會覺放松的音樂。
鹿笙看著窗外,在失神。
他剛剛腳步那麼匆忙,是去哪了呢?
“在看什麼?”許洲遠把點的熱巧放到面前。
鹿笙回過神來,抬頭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說沒什麼。
可的表,一看就是有心事。
許洲遠猜,可能、大概是與南懷璟有關。
他在對面坐下來:“你有段時間沒更博了。”
鹿笙還是笑笑,岔開話題:“最近生意怎麼樣?”
許洲遠看了眼店里:“來店的客人沒有以前那麼多了,但外賣單比之前多了不。”
很明顯,這個話題不是所在意和關心的,所以有些敷衍的,但也不失禮貌地點頭:“那也好。”
興許是店里不忙,又或者說他有點想八卦他那個不沾人間塵的朋友,所以,許洲遠把話題一轉:“簡阿姨人怎麼樣?”
“很熱。”
許洲遠笑著點頭:“會不會覺得熱過了頭?”他帶了點玩笑。
鹿笙角的弧度彎的比之前深了點:“還好。”
那就是被他說中了。
他這才把話題繞到南懷璟上:“和南教授的一冷一熱,對比很強烈吧?”
鹿笙看他:“你平時也喊他南教授嗎?”
許洲遠聳了下肩:“打趣的時候。”
所以他在打趣南懷璟的冷漠咯?
咖啡店里開了暖氣,不冷。鹿笙端起馬克杯,包裹在手心里,問的好像很隨口:“他對異是不是都這樣?”
“哪樣?”許洲遠饒有興趣地明知故問。
鹿笙抿了抿,斟酌了一個詞:“拒之千里。”
許洲遠低笑了聲。
鹿笙眼眸轉了幾下,面有點不自然:“笑什麼?”
角的笑不下去,許洲遠笑著問:“他拒絕你了?”
小心臟一提,鹿笙避開他耐人尋味的眼神,看向窗外,“我又沒跟他表白,他有什麼好拒絕我的”聲音低了幾分,但語速有很急。說完,將手里的馬克杯到邊,小小地喝了一口。
哪里知道,許洲遠大學主修的是心理學。
不過許洲遠雖然好奇,但他不是一個輕易聊人‘八卦’的人,更何況那人還是他的好友,不過好朋友的人生大事,他還是很想上一腳的。
所以,他好心地送上一句:“他很慢熱。”
就在鹿笙在心里回味這兩個字的時候,許洲遠起回了吧臺。
掌心包裹著的杯漸漸涼了溫度,鹿笙擱下馬克杯,起。
在吧臺結了賬,剛要轉,許洲遠喊住了,他把兩塊黑巧放在吧臺上:“另一塊幫我給他。”
墨影鋪地,道路兩旁的綠朦朧。灰白的路面上,不斷有車子從后面超上來。
從莫大到知南街,十五分鐘的路程,南懷璟今天用了二十六分鐘,到停車場是六點四十。
把車倒進停車位,車熄火后,他便在車里安靜地坐著。
他沒想到,院長會因為食堂的那件事把他去辦公室,他更沒想到,那個周曼還是院長的侄。
可那又怎樣,因為是院長的侄,他就會接嗎?
他只會比以前更排斥而已。
車窗下來,冷風刮著他的臉,也灌進車里。
今天周五,知南街上人不,算不上人如織,但也熙熙攘攘,南懷璟下車的時候剛七點。到了巷口,他看了眼咖啡店,見門口有人排隊,他便沒進去,轉拐進了巷子。
進了院子,他抬頭看了眼樓,目順便掃了一眼四樓的窗戶。
還沒走,南懷璟低頭看了眼時間,才七點零五分。
等他到了樓門口,手剛口袋去拿鑰匙,他目頓住。
銀門柄上掛著一個紙袋,白的,上面什麼圖案也沒有,他將袋子取下來,往里看了眼,里面是和上次裝桂花糖一樣的銀鐵盒,不過這次的盒子只有掌大。
盒子打開,里面裝著兩塊黑褐錫紙包裝的巧克力,是許洲遠那兒才有的。他怔怔地看著那兩塊黑巧出神,驀地,他合上蓋子裝回袋子里,將袋子重新掛回門柄上后,他轉往走廊那頭去。
鹿笙從咖啡店回來后,除了去了一趟樓,其他時間就一直在房間里待著,外面傳來敲門聲,鹿笙手里的筆一頓,潛意識里,猜到了是誰。
南懷璟站在門口,敲了兩下門后,他就低著頭,在看地上的絨地墊。
里面傳來清脆的聲音:“等一下。”
也沒等多久,門就開了,門簾被拂開半扇。
今天沒穿那件枯玫瑰的睡袍,穿的是一件黃的戴帽子的絨睡,睡不厚,前還垂著兩個球球,看著茸茸、乎乎的。
視線匆匆從臉上掃過一眼,他說了聲:“謝謝。”
說完他就走了。
鹿笙把腦袋從門簾里出來,往走廊那頭看。
他走的很快,很快就消失在走廊轉角,等看不到人了,鹿笙才把腦袋回去。門關上后,抿笑著跑回了房間,繼續畫的心上人。
沙發正對著的電視沒有開,黑的屏幕能倒映出對面的人影。
客廳里很靜,能清楚聽見掛鐘里傳出的“嗒嗒嗒嗒”聲。
南懷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盯著它看,隨著秒針有頻率地轉,分針緩緩往前移,已經七點五十二了,樓下還沒有傳來聲音。
八點整,“砰”的一聲門響。
沙發里的人,眼皮一震。
很快,又傳來門落鎖的聲音。
視線終于從掛鐘盤里收回來,里的苦融化完,一抹淡淡的薄荷甜在舌尖悄然留存。
翌日是周六,多云。
南懷璟昨晚凌晨兩點才睡著,他鮮失眠的。
十點二十,簡士上來敲門,敲了兩下,里面沒人應,在門口又等了一會兒,門還沒開。
家南教授就算睡懶覺也不會睡到這個點。
簡士又敲了兩下門,敲門聲比剛剛急了。
“懷璟?”
“懷璟?”
南懷璟的臥室和客廳隔了兩堵墻,但是臥室窗戶朝南,所以平時外面有什麼聲響都是從窗戶那兒傳來。
手從被子上抬起來,放在了額頭,因為被吵醒,他眉心攏著。
“懷璟吶?”
他長呼一口氣,撐著床墊坐起來,沒下床,閉著眼,倚著床背。
這麼老半天都聽不見回應,簡士是真急了,小跑著穿過走廊去樓下拿備用鑰匙。
五十多歲的人了,跑上跑下,拿著鑰匙再回到樓,氣吁吁。
結果鑰匙剛進鎖眼,門就從里面打開了。
簡士心口還在劇烈起伏著,不知是慌的還是累的。
“你這臭小子,”簡士這是第二次喊他臭小子,第一次是當著老公南知禮的面:“我剛剛又是敲門又是喊你的,你聽不見?”
他沒說話,神怏怏,眼底也有遮不住的濃濃倦意。
簡士還第一次見他這副無打采的樣子,不由得湊近他的臉:“不舒服嗎?”手就要去他的額頭。
南懷璟把頭往旁邊偏了一下,簡士的手落了空。
“我沒事,就是昨晚睡晚了。”
簡士撇:“比工作重要,知不知道?”
他嗯了聲。
簡士心里頭心疼:“樓下給你留了飯,要不要給你端上來?”
“不用,”他聲音又低又啞的:“我不。”
今天是周六,南孝宇在家,十一點的時候,他上了樓,踩上樓平階,腳剛轉了個方向,就看見他哥端著杯水,站在臺上。
別看今天有太,可氣溫很低,他哥就穿了一件薄薄的絨衫。
南孝宇輕腳走過去:“哥。”
南懷璟也沒扭頭看他,低低地嗯了聲。
南孝宇見他微微低著頭,在看樓下的什麼,他順著他哥的視線,往院子里看。
鹿笙背坐在石凳上,低頭不知在做什麼。
南孝宇站著的位置,只能看見他哥的側臉,他有點不確定:“你看什麼呢?”
“花。”
花?
南孝宇在院子里找了兩圈。
這麼冷的天,月季沒開,櫻花也沒開。
哪來的花?
該不會是在看石桌前的那朵人花吧!
南孝宇瞧出了點端倪。
本來他上來是想問他哥討點零花錢,現在看來,這個星期的零花錢可以先從他家簡士那兒下手了,畢竟他哥出手比他家簡士要闊綽,可以先留著以備大的花銷。
南孝宇默默溜下了樓,到了一樓樓檐下,南孝宇又看了眼鹿笙的背影。
說真的,這個的真漂亮的,后腦勺也漂亮的那種。
要不是他心里有人了,他肯定多看兩眼。
他轉進了客廳。
簡士正在廚房里做飯,南孝宇敲了下門,然后擰開門柄:“媽。”
油煙機開著,噪聲大。
簡士小幅度地側頭看了眼:“有事?”
也不知他家簡士在炒什麼,嗆人,他捂咳了聲,走進去,把門關上。
猜你喜歡
-
完結397 章

深情入骨:裴少撩妻套路深
要問蘇筱柔此生最大的幸運是什麼,她會說是結緣裴子靖。那個身份尊貴的青年才俊,把她寵得上天入地,就差豎把梯子讓她上天摘星星。可他偏偏就是不對蘇筱柔說“我愛你”三個字,起先,蘇筱柔以為他是內斂含蓄。直到無意間窺破裴子靖內心的秘密,她才知曉,那不…
112.5萬字8 16872 -
完結623 章

豪門危婚
臨近結婚,一場被算計的緋色交易,她惹上了商業巨子顧成勳,為夫家換來巨額注資。 三年無性婚姻,她耗盡最後的感情,離婚之際,再遭設計入了顧成勳的房,莫名成為出軌的女人。 一夜風情,他說:“離婚吧,跟我。” 她被寵上天,以為他就是她的良人。 她不知道,他的寵愛背後,是她無法忍受的真相。 不幸流產,鮮血刺目,她站在血泊裏微笑著看他:“分手吧,顧成勳。” 他赤紅著雙眼,抱住她,嘶吼:“你做夢!” 顧成勳的心再銅牆鐵壁,裏麵也隻住著一個許如歌,奈何她不知......
103.9萬字8 117371 -
完結1609 章

一胎三寶,爸比好厲害!
因失戀去酒吧的阮沐希睡了酒吧模特,隔日落荒而逃。兩年後,她回國,才發現酒吧模特搖身一變成為帝城隻手遮天、生殺予奪的權勢之王,更是她姑姑的繼子。她卻在國外生下這位大人物的三胞胎,如此大逆不道。傳聞帝城的權勢之王冷血冷情,對誰都不愛。直到某天打開辦公室的門
149.4萬字8 55852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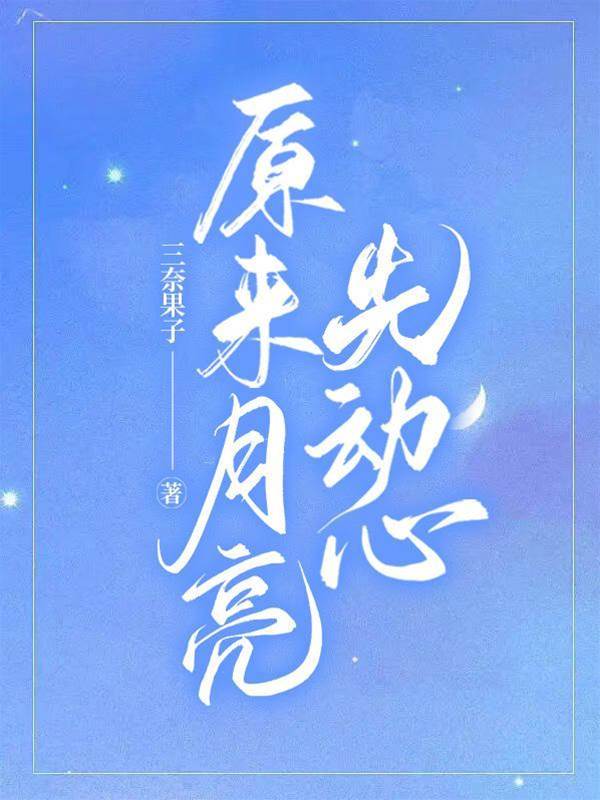
原來月亮先動心
【已簽約出版】原名:《喝醉後,我錯撩了閨蜜的小叔》【蘇撩 甜寵 教授 七歲年齡差 校園 救贖】【蘇撩腹黑小叔X古靈精怪少女】江落是十足的手控,為了一張手照,搭訕了一位帥哥,不料事後發現,對方居然是她閨蜜的小叔!江落腰板挺直,站姿乖巧:“小、小叔好。”……多年後,南大突然傳出生物學係的高嶺之花傅教授已經結婚的謠言。同事:“傅教授,這些謠言都是空穴來風,你別信……”“澄清一下,這不是謠言,”傅紀行冷靜補充,“我確實結婚了。”!!!江落跟傅紀行扯證時,她正讀大四。扯完證回去的路上,男人手裏拿著小本子,溫聲提醒:“喊了我這麼多年的小叔,是不是該換一下稱呼了?”“什、什麼稱呼?”“比如……”男人的吻落在她唇上——“老公。”
21.2萬字8 82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