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少的替嫁甜妻》 第1496章 緊急撤離
程澄聽著窗外的雨聲,一直沒辦法眠。
睡覺之前給張瑤和保鏢們都提醒過,讓他們提高警惕,不要睡死,免得出現什麽意外來不及逃出來。
這雨太大了,嘩啦啦的聲音讓人聽了就覺得害怕。
程澄翻來覆去睡不著,最後還是忍不住坐了起來,將服穿戴整齊。
剛做好這一切,突然聽見門口傳來陳薰的喊聲:“程澄,快起來,我們得離開這裏了。”
程澄趕忙將門打開,看見陳薰披著雨站在院子裏,神焦急。
“陳導,怎麽回事,為什麽突然要撤離?”
“剛剛村民給我傳了消息,雨太大了,附近的河水決堤了。我們這邊地勢低窪,很容易被水淹。你快把你重要的東西帶著,我去傅玉清。”
陳薰說著,裏嘀咕:“傅玉清該不會是睡死了吧,我剛剛喊這麽大聲,程澄都聽見了,他一點靜都沒有。”
Advertisement
程澄趕忙回房間帶上自己重要的行李,尤其是將顧雨辰送的手機帶上。
等背著包出來的時候,張瑤和四個保鏢也收拾好了,在門口等著。
張瑤一見出來,連忙衝到邊,抓住的手:“程澄,你待會一定要抓我,別離我太遠。”
張瑤隻覺得他們太慘了,拍個戲還遇到了幾十年難遇的大暴雨,偏偏這個地方偏僻,連信號都時有時不有。
要是真出了什麽事,那可是天天不應,地地不靈。
程澄點點頭,朝出安的笑容:“不用擔心,我們不會有事的。”
話雖這麽說,程澄抓住張瑤的手卻又了些。
想了想,對其中兩個保鏢道:“你們跟著瑤瑤,保護好的安全。”
那兩個保鏢有些為難,他們的職責是保護程澄。
不過對上程澄威嚴的目,那兩個保鏢還是點了點頭,站在了張瑤後。
張瑤心中一陣,程澄太善良了,要關頭還想著。
發誓以後一定要對程澄好一點更好一點。
他們幾個都準備好了,但是陳薰還在敲傅玉清的門。
程澄冒雨跑過去,著急詢問:“怎麽了?傅玉清怎麽不開門?”
“我也不知道,敲了好久的門,但是一直沒人開。”陳薰有些著急,看了看手表,再不開門,就來不及跟著村民撤離了。
程澄眉眼一蹙,扭頭來了自己的四個保鏢:“給我把門踹開。”
那四個保鏢對程澄唯命是從,當即直接抬腳將房門給踹開了,因為用力,門板轟然倒塌。
程澄走進屋裏,準備將傅玉清揪起來,結果一進去卻發現裏麵空無一人。
“傅玉清不在房間!”程澄語氣嚴肅。
這大雨天的,這人不好好在房間裏待著,跑去哪了?
張瑤猜測道:“陳導,你說傅是不是已經出去和劇組其他人員集合了?”
“不可能,我剛得到消息就跑來你們了,傅玉清不可能比我先得到消息。”陳薰麵容凝重。
傅玉清不見了,人不知道去哪了,萬一出了什麽事,那就糟糕了。
他不僅僅是他們劇組的投資人,還是傅家小爺,份貴重,陳薰不能讓他在劇組出事。
“陳導,我們先出去吧,時間已經來不及了。等出去後,我們再沿路尋找,讓劇組的人都幫忙找找,人多力量大。”
陳薰聽了程澄的話,覺得有道理:“行,我們先撤離。”
說完,率先一步離開院子,程澄幾人追其後。
不過程澄快離開房間的時候,突然看到窗邊的書桌上有一張紙條。
隨意掃了一眼,意外注意到紙條上有的名字。
程澄一下子停住了腳步,連忙衝到窗前,將紙條拿了起來。
“程澄,怎麽了?”張瑤一扭頭見又回到房間裏,有些納悶。
程澄將紙條遞給,神冰冷:“有人冒充我給傅玉清寫了紙條……”
說完,突然想起自己窗外的那張紙條,神更加凝重了:“這樣的紙條我也收到了,隻不過我的被雨打了,所以我沒當一回事。”
張瑤看到上麵程澄的字跡,氣的咬牙切齒:“誰這麽不要臉,你和傅玉清關係這麽差,怎麽可能大半夜約他單獨見麵。”
說完,突然意識到什麽,和程澄四目相對:“程澄,傅玉清該不會真的去了吧?!”
猜你喜歡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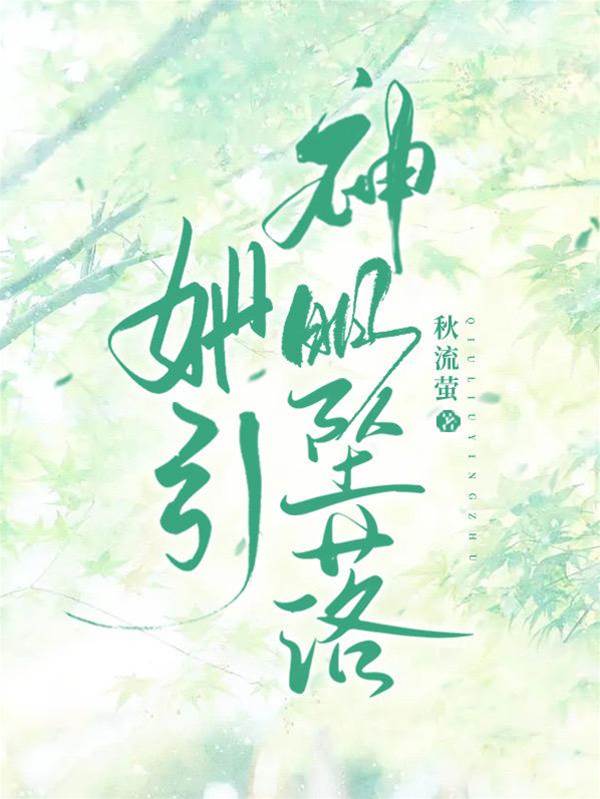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69 章

溫先生的心尖月
(蓄謀已久 細水流長 甜寵 雙潔 無虐 年齡差五歲左右)(女主醫生,非女強)*【溫婉清麗江南風美人 & 內斂沉著商圈大佬】容煙出身書香門第,自小跟隨外公生活。聽聞外公給她尋了門親事,她原以為聯姻對象是同為醫生的溫二公子,殊不知卻是接管溫家的溫景初。煙雨灰蒙,寺廟裏,容煙瞥見與她擦身而過的男人。上一次見他還是四年前,可他從不信神佛,為何會出現在這裏?朋友生日聚會結束,溫景初送她歸家。車內,容煙壓住心中疑惑,終究沒問出口。*容煙本是溫吞的性子,喜靜,信佛。她自認為婚後的兩人是相敬如賓,搭夥過日子。而他卻步步誘她淪陷。某日,容煙在收拾書房時看到了寺廟的祈福袋,裏麵白色宣紙上寫著她的名字,似乎珍藏了許久。而此時溫景初正接受電視臺采訪,清肅矜貴,沉穩自持,淡定從容與人交談。主持人問,“溫先生,聽聞您並不信神佛,但為何每年都到靈山寺祈願?”容煙手中拿著祈福袋,略帶緊張的等待著他的回答。男人黑眸如墨,思忖片刻,緩緩啟唇,“因為溫太太信佛。”簡單一句話卻擾亂她的心。
33.1萬字8.09 265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