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病嬌綁定之后》 第98章 淚落心上
夏蒹微微怔住。
“那孩子,說是一切皆要照能做到的最好的規格去辦,”嫻昌面上的笑容顯得有些譏諷,磨得尖細的指頭一下一下捋著發,“三禮六聘,冠霞帔,十里紅妝,全都要樣樣不你,這勢頭,怕是之前南云氏李姓貴嫁承安侯世子都沒要這麼大場面罷。”
人微瞇起眼直起,紅玉過來,細細幫將腰間的系帶綁好。
夏蒹端坐著,指尖攥,又松開,重復多次,依舊緩不過指尖輕微發麻。
裴觀燭與嫻昌商討想和婚。
而這個當事人竟對此毫不知。
今日嫻昌找,怕其實也是不滿一介曾被棄的孤如今能有這樣大的造化。嫻昌不喜歡,雖然,夏蒹覺得可能裴觀燭娶誰,嫻昌都不會喜歡對方,但這個人是夏蒹的話,嫻昌只會更為厭惡。
因為夏蒹與嫻昌注定不站在一條線上。
夏蒹起眼,與嫻昌對上視線。
大抵是因為沒有裴觀燭在場。
人今日鋒芒畢,面上笑容始終帶著一抹譏諷,四目相對時,嫻昌微微昂起下,從上往下,輕翹起角,彎眼俯視著。
夏蒹微微吸進一口氣。
這是第一次,夏蒹發覺到,其實嫻昌和裴觀燭一丁點都不像。
一丁點都不。
“你伴本宮出去外頭走走吧。”
紅玉后退,人穿著層層疊疊的宮裝,出好潔白的脯。
“是,貴妃娘娘。”
夏蒹跟在嫻昌后。
一路無話,直到兩人上了一座白玉橋,嫻昌自紅玉手中接過魚食,小步端莊,傍晚,夜逐漸取代了橘的黃昏,宮人掛起宮燈,海棠樹的花瓣片片自天上飛舞而下,落在白玉石橋上,被人毫不留的踩在腳下,明亮的宮燈線映在上,將上穿著的宮裝布料映亮,乍一看,好似月宮仙子下凡,艷至極。
Advertisement
“天轉涼了呢,”嫻昌道,指尖捻過魚食,一點一點撒進湖中,金紅的錦鯉噗通蹦上來,爭相搶食。
“就連日頭也逐漸短暫,這樣快天便黑下來了。”
“是,貴妃娘娘。”
“你這丫頭,”嫻昌彎起眼看向,“上回不是還十分伶牙俐齒麼?怎麼?鏡奴不在,便覺沒主心骨,都不敢同本宮作對了麼?”
眼里散著些微的得意。
夏蒹與對上視線,面無表的臉上彎起一個沒什麼緒的笑臉。
“貴妃娘娘是這樣認為的嗎?”夏蒹聲音坦坦,“原來在貴妃娘娘眼中,民上次一番話,竟是故意與娘娘作對麼?”
嫻昌微微瞇起眼。
“并沒有這個必要,只是民這人天生好奇心比常人要強,尤其是關系到晚明的,哪怕是一團麻,民也想要一點一點捋順,捋通了,若上次民言行有得罪到娘娘之,還請娘娘多多見諒,畢竟民確實如您所見,并不似晚明那般有這樣好的教養。”
說著卑微的話,染著棕的瞳子澄澄探過來,著難得一見的無畏與坦。
嫻昌看著,微微皺起眉,復又松開。
——不過一介沒教養的孤,只怕是無知者無畏罷了。
“你確實缺人教導,”嫻昌看著,無名指慢條斯理將被風吹的碎發捋到耳后,淺淺笑起來,“真算是上輩子修來的福氣。”
又來了。
但夏蒹看著嫻昌,卻莫名沒了第一次聽到這種話時的氣憤,和第一次頂撞的時候覺到的激與恐懼。
全都煙消云散了。
據夏蒹所知,眼前的人,曾是宋府地位最為低下的庶,若比起上輩子修來的福氣,那麼這位如今被當今圣上放在心尖上的寵妃,大抵更配得上這句話,畢竟才是了真正的榮華富貴,萬千寵于一。
但夏蒹本不好奇的人生旅程,事實上,這和也并沒有什麼關系。
“娘娘真是從心底護晚明,”夏蒹起眼,“若是民不知道,大抵還會以為貴妃娘娘才是晚明的親生母親呢。”
……
從貴妃殿門出去。
夏蒹呼出一口氣,秋日泛寒,上衫單薄,走在小道上,都覺得有些寒冷。
海棠樹的花瓣一路飄到小道上,踩在這些花瓣上會讓人覺得不忍,夏蒹一路小心避開,走到如今,花瓣漸,走路的趣味也淡了很多。
上次走這條小道,還是和裴觀燭一起,當時還沒有這樣多的花瓣掉下來。
今日的心一直在浮躁,因為與裴觀燭短暫的分別而到浮躁。
但這一趟,并非毫無意義。
起碼,夏蒹更確定了心中想法。
嫻昌絕對不會是裴觀燭的親生母親。
其實,夏蒹從一開始就沒有懷疑過裴觀燭大抵并非是宋夫人的親生孩子這一可能。
裴觀燭只可能是宋夫人的親生之子。
不為其他。
只為,據夏蒹了解,裴玉極干凈的東西,這一點現在,就連裴觀燭的名,也是用鏡來取名。
鏡,能映照出人心丑惡,最干凈,最容不得骯臟的鏡,不是水,不是玉,而是鏡,只有鏡才能映照,且永遠不會被玷污。
而裴玉對‘干凈’有所執念,這一點嫻昌貴妃也心知肚明。
而且裴觀燭曾親口說過,裴玉覺得,癡傻,才是‘干凈’的。
這一點,夏蒹也知道,例如說看到過的一些書,曾提到過的阿姐鼓,有些人他們對‘干凈’極為有執念,雖然裴玉的質不同,但大抵夏蒹猜測他也有慕癡傻的質在,因為覺得癡傻才是最干凈的。
這樣的人,夏蒹不會認為他會在從一開始,就做出和慕之人的親妹妹茍且這種事,他一定做不出來。
更別提。
夏蒹皺起眉,回想起方才嫻昌那令人不悅的笑臉。
“真的?你真的這樣覺得?”人的高興著莫名的病態,像是藏都藏不住。
想要做裴觀燭的母親嗎?
到底是為什麼?
終于踏出了貴妃殿。
夏蒹起眼,卻沒見小轎。
一輛只掛家紋令牌的馬車停在燈火瑩亮。
守在馬車前的宮人見了,忙小跑上來,“夏姑娘,您可算是過來了,裴大公子在這兒等您許久了。”
“啊?”夏蒹遲疑著,眼睛看向閉的馬車小簾,心中莫名添上一抹張。
“您快些上去吧,可別讓裴大公子久等了。”宮人面為難,就差推著夏蒹上馬車了。
夏蒹看著宮人的模樣,有些不解,呼吸兩下,才在宮人催促的視線下,拉開了馬車簾。
裴觀燭正坐在馬車。
年穿著他最近最常穿的雪青圓領長衫,墨發用紅發帶半束起來,發尾卻都一縷縷掉了下來,遮住整張面龐,掀開簾子,也沒換的裴觀燭回一下頭。
夏蒹莫名張,提著一口氣般,視線匆匆一瞥,不敢多看,便覺后宮人拍了拍,忙坐上來,坐到裴觀燭側。
馬車往前行。
夏蒹渾張,正要問裴觀燭有沒有得到留的口信,便忽然聽見了一聲輕輕的吸氣音。
夏蒹一震,轉頭看過去。
年手放在膝蓋上,雙手著雪白的帕子,他端端坐著垂著頭,但眼淚一顆一顆,在雪青布料上落下一個又一個深的圓點。
“你……”夏蒹手忙腳湊過去,“你哭什麼啊?”
裴觀燭始終低著頭,夏蒹只能坐在他畔,“我給你留了口信的,下人都沒跟你說麼?”
“就一句道歉也沒有嗎?”
裴觀燭轉過頭,眸像是被水洗了一遍,眼眶都是紅的,死死盯著,“一句道歉,就是連一句道歉都沒有!一句道歉都沒有!”
“我!”夏蒹無法理解,“我道什麼歉?我又沒錯,馬車上呢你嚷嚷什麼!”
“有夠過分的!你有夠過分的!你說為何要道歉!你說我為何要大喊大!你說為何!你說究竟是為何!賤人!你是賤人!”
淚水劃下下,裴觀燭盯著,“說好了的!都說好了的!不準離開,明明都說好了的!好過分!有夠過分的!”他焦躁的不停咬著手指頭,夏蒹一看,才發現他大拇指已經滲出了,忙去抓他手腕,卻被他的手打開,一下掐住脖子。
茶桌上的茶摔下來,茶水從桌上流下來。
“唔!”夏蒹脖子往上,拼命地掙扎,“你瘋了!你瘋了是吧裴觀燭!松開我!快點松開我!”
“有夠過分的!賤人!賤人!嗚……嗚……!你要我怎麼辦,我究竟要怎麼辦?說好了的都要毀約嗎!明明說好了的!你都要毀約!你都要這樣!我算什麼!嗚……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淚水砸上的臉。
夏蒹眼睛瞪得很大,裴觀燭崩潰不安的緒像是滲進了的心臟里,夏蒹對上他蒙著淚水的眼睛,明明是這樣的眼神,但掐著脖子的手始終都沒有收力。
夏蒹看著他,漸漸停了掙扎,抬起胳膊抱住了裴觀燭的腰。
猜你喜歡
-
完結205 章

香妻如玉
凝香從冇想過自己會嫁給一個老男人。可她偏偏嫁了。嫁就嫁了吧,又偏偏遇上個俏郎君,凝香受不住俏郎君的引誘,於是甩了家裡的老男人,跟著俏郎君跑了。不料卻被老男人給抓了個現行!“你殺了我們吧!”凝香撲倒郎君身上,勇敢的望著老男人。老男人冇殺她,給了她一張和離書。然後,然後就悲劇了....俏郎君負心薄倖,主母欺辱,姨娘使壞,兜兜轉轉的一圈,凝香才發現,還是原來那個老男人好。突然有一天,凝香睜開眼睛,竟然回到了和老男人剛成親的時候。可這一切,還能重來嗎?--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42.4萬字8 11515 -
完結591 章

帶著千億物資穿成大奸臣的炮灰前妻
穿成大反派的作死前妻,應該刻薄親生兒女,孩子養成小反派,遭到大小反派的瘋狂報復,死后尸體都被扔去喂狼。 看到這劇情走向,俞妙云撂挑子不干了,她要自己獨美,和離! 手握千億物資空間,努力發家致富,只是看著這日益見大的肚子,俞妙云懵了,什麼時候懷上的? 不僅如此,大反派體貼化身寵妻狂魔,小反派乖巧懂事上進…… 這劇情人設怎麼不一樣?
103.7萬字8 99967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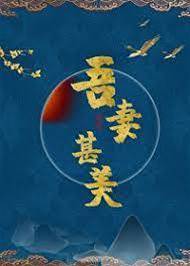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