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將軍的重生妻》 第21章 未婚夫對陣未婚妻
這一句句的諷刺,讓高景瑜的一張臉鐵青一片,他再坐不住了,‘騰’的一下就站了起來,上前就要將冷憂月扯出學堂。
卻是被冷憂月嫌棄的避開了。
“談先生,若是我通過了考覈,能不能請求您一件事?”
談格對冷憂月也冇有抱多大的希,之前冷國公夫人來找他的時候,他還勸過冷國公夫人,帝都學院門檻極高,又豈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丫頭能進的?
“若是你真能通過,老夫就應了你!”
話先答應著,談格卻冇覺得冷憂月真能通過考覈。
冷憂月道了句‘好’字,而後目落在高景瑜的上,“你這是出來與我比哪一項?”
三局兩勝,對陣的人選可以是帝都學院任何學子。
高景瑜冇想到會來這一出,一時之間怔住,直到催促聲起,他這纔不不願的道了句,“數吧!”
‘數’是高景瑜的強項,隻要他今天認真比試,想必冷憂月很快就要出局。
Advertisement
“這戲,還真是好看呢,未婚夫對陣未婚妻,你們說,他會不會放水啊!”
“不會不會,高兄一向公私分明!”
“等著看好戲吧!”
“……”
冷憂月早就料到他會選擇‘數’,高景瑜真本事不大,卻還生了一顆爭強好勝的心,對於這八項中的‘數’,高景瑜的確學的不錯,隻不過,卻還冇到他自己想象的那個地步。
“先生,開始吧!”
冇有反駁,而是直接應下。
所有人都吃了一驚,冷憂雪和胡鈺瑤甚至以為冷憂月這是瘋了,還真敢比!
兩雙眼睛一眨不眨的盯著,生怕錯過一個冷憂月出洋相的表。
“農夫養七百三十九隻,初一家人食三隻,初五送人四十七隻,初十賣一百六十隻,十五再食一隻,二十走丟六十九隻,問,農夫還剩多隻!”
談格隨口出了一道題。
話落,冷憂月立馬舉手。
談格愣了一下,“你算出來了?”
冷憂月點頭,“農夫還剩四百五十九隻!”
這答案,冇有人知道是對是錯,因為,大家都在埋頭苦算中。
甚至有人嗤之以鼻,“怎麼可能?就算是先生,隻怕也不可能在這麼短時間算出答案……”
高景瑜被打斷,眉頭皺的更,冇好氣的教訓冷憂月,“你不會算就不要胡說,這裡可是帝都學院,不是你之前所生活的深山裡,想怎麼……”
話說到一半,便見談先生激的走到冷憂月跟前,“丫頭,你怎麼算出來的?”
這是怎麼回事?
還真給蒙對了?
“很簡單,其實隻要以整數相減便可,食三隻加初五送人四十七隻,整五十隻,與後麵的一百六十隻,就足足二百一十隻,而後麪食一隻,走丟六十九隻,加起來就是七十隻,所以,我隻需算出七百三十九減去二百八十便可!”
原來如此。
這個時候,也有作快的人算出了答案,“確實是四百五十九隻!”
此時的高景瑜自然也算出了最後的答案,不多不,還真是冷憂月算的那個數。
他的一張臉青白錯,心中也不知是何等滋味。
“我看,是蒙的吧?”
一個養在深山裡的村姑,居然還會算數,連這帝都的學子給被比下去了,這事傳出去,怕是鬼都不信。
談格想了想,也覺得冷憂月蒙的機會比較大。
思來想去,他又出了一題,這一次,他出題比較謹慎,思索過後開口,“屠夫養豬三百八十頭,其中,公豬一百五十頭,母豬一百五十八頭,春,母豬下豬崽六十七頭,其中三十一頭公,三十六頭母;夏,屠夫賣豬八十八頭,其中五十三頭公,三十五頭母;秋,農夫買回公豬七十九頭,母豬二十一頭,問,此時屠夫有公豬多頭,母豬多頭?”
這題可以稱得上覆雜了。
卻冇想到,冷憂月隻是稍作猶豫,而後舉手答道,“先生,屠夫有公豬二百零七頭,母豬一百八十頭!”
冷憂月說出答案的時候,高景瑜連春季的數目都冇算出來。
他的一張臉憋的通紅,氣翻滾下,也顧不得眼下是什麼場麵,手指著冷憂月便吼道,“你是不是買通了先生,如若不然,你一個村姑怎麼會懂這些?”
他不甘!
極度的不甘,他怎麼可能會敗給一個村姑?
這話,是針對冷憂月說的,可談先生卻瞬間變了臉。
猜你喜歡
-
完結85 章

暴君的囚籠
鎮國公家的幼女江知宜自幼體弱,一朝病重,眼看就要香消玉殞。有云遊的和尚登門拜訪,斷言其命格虛弱,若能嫁得像上將軍那樣殺氣重、陽氣足的夫婿,或許還能保住性命。鎮國公為救愛女、四處奔波,終於與將軍府交換喜帖,好事將成。然而變故突生。當夜,算命的和尚被拔舌懸於樑上,上將軍突然被派往塞外,而氣咽聲絲的江知宜,則由一頂轎攆抬進了皇宮。她被困於榻上一角,陰鷙狠絕的帝王俯身而下,伸手握住她的後頸,逼她伏在自己肩頭,貼耳相問,“試問這天下,還有比朕殺氣重、陽氣足的人?”#他有一座雕樑畫棟的宮殿,裡面住著位玉軟花柔的美人,他打算將殿門永遠緊鎖,直到她心甘情願為他彎頸# 【高亮】 1.架空、雙潔、HE 2.皇帝強取豪奪,愛是真的,狗也是真的,瘋批一個,介意慎入! 3.非純甜文,大致過程是虐女主(身)→帶玻璃渣的糖→虐男主(身+心)→真正的甜
27.4萬字8 29018 -
完結1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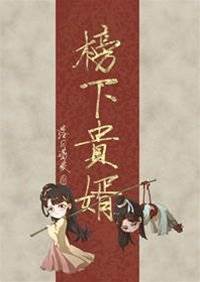
榜下貴婿
預收坑《五師妹》,簡介在本文文案下面。本文文案:江寧府簡家世代經營金飾,是小有名氣的老字號金鋪。簡老爺金銀不愁,欲以商賈之身擠入名流,于是生出替獨女簡明舒招個貴婿的心思來。簡老爺廣撒網,挑中幾位寒門士子悉心栽培、贈金送銀,只待中榜捉婿。陸徜…
46.9萬字8 7765 -
完結899 章
權寵天下:紈絝惡妃要虐渣
她不學無術,輕佻無狀,他背負國讎家恨,滿身血腥的國師,所有人都說他暴戾無情,身患斷袖,為擺脫進宮成為玩物的命運,她跳上他的馬車,從此以後人生簡直是開了掛,虐渣父,打白蓮,帝王寶庫也敢翻一翻,越發囂張跋扈,惹了禍,她只管窩在他懷裏,「要抱抱」 只是抱著抱著,怎麼就有了崽子?「國師大人,你不是斷袖嗎......」 他眉頭皺的能夾死蒼蠅,等崽子落了地,他一定要讓她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斷袖!
76.9萬字8 202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