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軟嬌妻馭惡夫》 第七百五十二章 他們怎麼可能錯
柳萍萍他們走了之后柳婆子是越想越堵心,又加上村里人說什麼都有,自己撒出這口氣,便來家罵的這一場。
本來是三百兩銀子的,最后都手只有五十兩,還斷了以后再能拿到銀子的可能,造這一切錯的都是家。
是罵的痛快了走了,等魏氏再進里屋去看丈夫,發現丈夫不僅吐了還人事不省。
魏氏嚇得不行,高聲喊著兒子。
毅的傷早就養好了,也不疼了,但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幾個月都不下床不出門走的原因,現在他走路的時候左腳好似要短些。
他自己沒有察覺,別人不注意看也看不出來。
他躲著連爹娘都不愿意見,所以魏氏和嚴錚都沒有發現這一點。
剛才柳婆子來罵的時候他就拿布條子堵了耳朵,為的是聽不到也不煩。
是以,柳婆子走了他并不知道,現在魏氏連著喊了他兩聲他是聽到了的,也沒有應,他以為是魏氏喊他出去,他怎麼可能去面對外頭的那個潑婦?
Advertisement
還是魏氏到他屋里來找,這才跟著出來去看他爹的況。
人都昏了自然是要趕送醫館的,魏氏還記得上回大夫可是叮囑過了的,就怕緒激。
魏氏也是怕他再中風,好好的一個人躺在床不得,只一對眼珠子的樣子也怕了。
叮囑了毅在家給他爹還一干凈的服,去村里請了趕牛車的人來幫忙往鎮上醫館送。
雖說是不樂意跟家打道,但現在是關乎到人命的事,即便是再不樂意還是來了。
幫著把人背上板車送到醫館,還等著看要不要一道再回來。
結果大夫看了嚴錚的況,說他這是中風,比上次還嚴重。
不止是中風,還有心臟和肺上的疾病。
嚴錚這幾年都在咳,肺上有問題是他們心里都有數的,但這幾個月都沒有再咳,他們以為是好了。
現在一氣之下是哪兒的不好了,大夫還不敢說能救得了。
這回用的藥也貴,畢竟是救命的藥。
家存下的銀子都用上了,嚴錚也只是堪堪醒了而已,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大夫叮囑了回去一定要按時吃藥,魏氏除了一樣一樣記著也沒有別的辦法。
半夜里,魏氏本就睡不著,懷里抱著家里裝銀子的匣子,里面只剩下些散碎的銅板,連三天后的藥錢都不夠。
可是,大夫說了,這個藥得長期吃著。
丈夫每月得的銀子只是供他吃藥都不夠,哪還說什麼吃喝?
到了這種時候,魏氏能想到的只有跟他們斷了親的兒,要說這是還不是惹出不來的。
于是,魏氏就到宋家村來找卿,來晚了。
“彪子他們昨兒就上京去了,你們家不是都斷了親了嗎?你還來干什麼?”
“他們家哪有好人?專門找來還能有好事?怕不是銀子不夠使了,這又專門是來要銀子的吧!
不然,能抬貴腳踏咱們這地兒?”
“哼!若是要銀子,沒有!
找人,人也不在。
再一個,咱們宋家村就不歡迎你們姓的一家,趕走吧,以后也都別再出現在咱們宋家村。”
猜你喜歡
-
完結810 章
鳳謀天下:王爺為我造反了
「我雲傾挽發誓,有朝一日,定讓那些負我的,欺我的,辱我的,踐踏我的,淩虐我的人付出血的代價!」前世,她一身醫術生死人肉白骨,懸壺濟世安天下,可那些曾得她恩惠的,最後皆選擇了欺辱她,背叛她,淩虐她,殺害她!睜眼重回十七歲,前世神醫化身鐵血修羅,心狠手辣名滿天下。為報仇雪恨,她孤身潛回死亡之地,步步為謀扶植反派大boss。誰料,卻被反派強寵措手不及!雲傾挽:「我隻是隨手滅蟲殺害,王爺不必記在心上。」司徒霆:「那怎麼能行,本王乃性情中人,姑娘大恩無以為報,本王隻能以身相許!」
150.5萬字8 82602 -
完結1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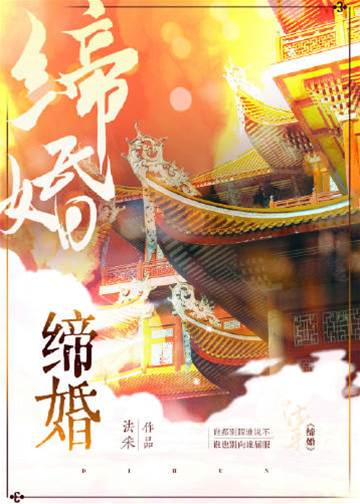
締婚
家敗落之後,項家老爹成了人人喊打的奸佞,項宜帶著幼年的弟妹無依無靠、度日艱難。 她尋來舊日與世家大族譚氏的宗子、譚廷的婚約,親自登了譚家的門。 此事一出,無人不嘲諷項家女為了算計、攀附譚家,連臉面都不要了。 連弟弟妹妹都勸她算了,就算嫁進了譚家,...
45萬字8.33 82137 -
完結136 章

重生之窈窈再愛我一次
謝令窈與江時祁十年結發夫妻,從相敬如賓到相看兩厭只用了三年,剩下七年只剩下無盡的冷漠與無視。在經歷了丈夫的背叛、兒子的疏離、婆母的苛待、忠仆的死亡后,她心如死灰,任由一汪池水帶走了自己的性命。 不想再次醒來卻發現自己回到了十七歲還未來得及嫁給江時祁的那年,既然上天重新給了她一次機會,她定要選擇一條不一樣的路,不去與江時祁做兩世的怨偶! 可重來一次,她發現有好些事與她記憶中的仿佛不一樣,她以為厭她怨她的男人似乎愛她入骨。 PS:前世不長嘴的兩人,今生渾身都是嘴。
27.1萬字8 266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