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你家小撩精野性難馴》 第80章 權衡抉擇
此時,遠在千里之外的京城。梅蘭正跟自己的老友,說起自己的小徒弟:「我那個小徒弟啊,至至至善至。小叭叭叭的不饒人,可是心腸比誰都。十二歲那年,跟著我去義診,遇上一個攔路搶劫的年。那丫頭二話不說,上去就是一頓揍,把那個年揍的鬼哭狼嚎。可是當聽說,那個年是被人綁架了,費勁九牛二虎之力才逃了出來,因為缺吃穿,這才突發奇想,想要搶點吃的。看到我們一個老一個弱,就想對我們開刀。結果,上了,這個茬。」說到這裏,梅蘭自己都沒忍住笑:「然後我那個小徒弟就心了,把自己的食和水都送給了他,還幫他檢查了上的傷口,就地采了一堆草藥,給他敷了傷口。一邊給他治療一邊叨叨叨的教育他,把那個年數落的,頭都要耷拉到口了。後來,我們離開的時候,那個小丫頭還給他特意烤了一隻野兔,把上所有的零花錢都給了他。」「確實是個有趣的丫頭。」友人附和說道。「也幸虧是個小辣椒的脾氣,不然也撐不起這個家。」梅蘭慨的說道。正說著話,電話響了起來。梅蘭一看,說道:「真是說曹,曹就到。我小徒弟來電話了。我先接個電話。喂……」「老師。」寧半夏的聲音充滿了猶豫糾結掙扎不安。「怎麼了?」梅蘭站了起來,來到一邊接電話:「出什麼事兒了?」「老師,我知道我不該再做去這種糊塗事。可是今天,江景爵過來找我了,他說,只要啊我繼續扮演下去,就給我出了忍冬全部的治療費,而且提前隊,拿到針劑。蔣家也找到我,希我繼續扮演下去,理由是他的祖母胃癌晚期,想要見見素未謀面的孫。老師,我該怎麼辦?」梅蘭深深嘆息一聲:「你的心裏已經有答案了,不是嗎?」「可是,我答應過老師,不再做這種事。」寧半夏聲音低落的說道。「老師沒有責怪你的意思。半夏,你是個聰明的孩子,也是個能擔起大事兒的孩子。想做什麼就去做吧。」梅蘭溫的說道。「老師……嗚嗚嗚嗚……」寧半夏再也忍不住,對著電話哭了起來。上的力,真的太大太多了。才二十三歲啊!別的孩子,二十三歲,剛剛畢業,正是無憂無慮著父母人疼的時間,而卻早早的背負起了生活的重。「有什麼需要老師的地方,儘管開口。」梅蘭說道:「在我的眼裏,你不僅僅是我的小徒弟,還是我的孩子。」「謝謝老師。我知道怎麼做了。」寧半夏吸吸鼻子:「我完老人的願,我就徹底離江蔣兩家,再也不要跟他們有任何牽扯了!到時候,忍冬好起來,我就帶著忍冬離開T市,天涯海角任我行!」掛了電話,梅蘭苦笑一聲,轉看著自己的好友:「老夥計,我跟你討個人。」「哎呦,你可別這麼說。能讓國寶級的梅醫生開口,是我的榮幸。」友人趕回答。「過些日子,你幫忙給兩個孩子安排個落腳的地方。」梅蘭說道:「到時候,再聯繫你就是了。」「好好好。」友人一口應了下來:「包在我的上。」寧半夏掛了電話,看看剛剛裝修好的小飯館,親自鎖上門,掛上了歇業的牌子。「喲,這還要繼續歇業啊?」鄰居湊過來問道:「你這是又要出遠門啊?」寧半夏苦笑一聲:「是啊,這不是錢不湊手,進貨的錢都沒有了嗎?出個遠門,賺點原始資金,再回來進貨開店。」鄰居同的看著:「你爸爸又賭錢了?」「是啊。」寧半夏臉皮賊厚的回答:「家裏又沒錢啦!」寧半夏微笑,老寧你繼續背黑鍋吧!寧半夏給江景爵打電話:「方便說話嗎?」江景爵馬上抬起手指,暫時中止正在開的會議,對著電話小聲說道:「方便,你說吧。」「你讓我回來繼續扮演蔣依依,期限是多久?」寧半夏問道。
Advertisement
猜你喜歡
-
完結397 章

深情入骨:裴少撩妻套路深
要問蘇筱柔此生最大的幸運是什麼,她會說是結緣裴子靖。那個身份尊貴的青年才俊,把她寵得上天入地,就差豎把梯子讓她上天摘星星。可他偏偏就是不對蘇筱柔說“我愛你”三個字,起先,蘇筱柔以為他是內斂含蓄。直到無意間窺破裴子靖內心的秘密,她才知曉,那不…
112.5萬字8 16872 -
完結623 章

豪門危婚
臨近結婚,一場被算計的緋色交易,她惹上了商業巨子顧成勳,為夫家換來巨額注資。 三年無性婚姻,她耗盡最後的感情,離婚之際,再遭設計入了顧成勳的房,莫名成為出軌的女人。 一夜風情,他說:“離婚吧,跟我。” 她被寵上天,以為他就是她的良人。 她不知道,他的寵愛背後,是她無法忍受的真相。 不幸流產,鮮血刺目,她站在血泊裏微笑著看他:“分手吧,顧成勳。” 他赤紅著雙眼,抱住她,嘶吼:“你做夢!” 顧成勳的心再銅牆鐵壁,裏麵也隻住著一個許如歌,奈何她不知......
103.9萬字8 117371 -
完結1609 章

一胎三寶,爸比好厲害!
因失戀去酒吧的阮沐希睡了酒吧模特,隔日落荒而逃。兩年後,她回國,才發現酒吧模特搖身一變成為帝城隻手遮天、生殺予奪的權勢之王,更是她姑姑的繼子。她卻在國外生下這位大人物的三胞胎,如此大逆不道。傳聞帝城的權勢之王冷血冷情,對誰都不愛。直到某天打開辦公室的門
149.4萬字8 55852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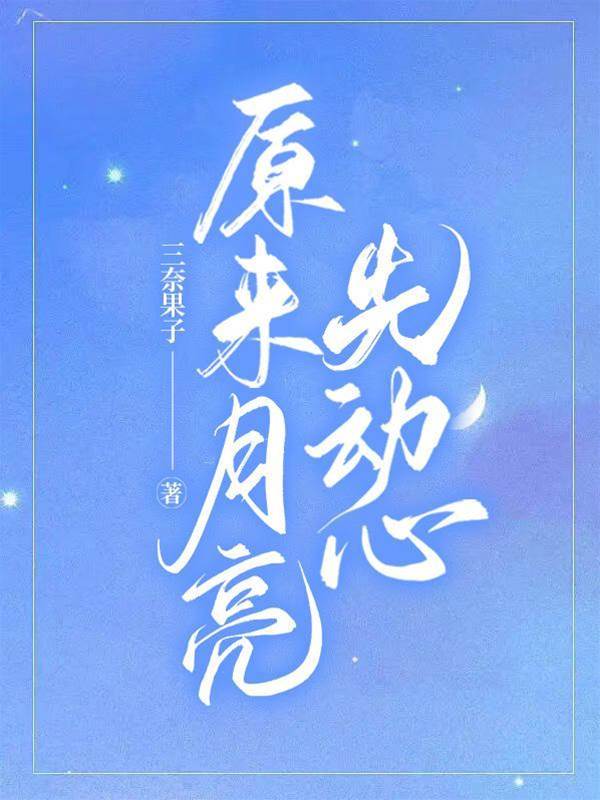
原來月亮先動心
【已簽約出版】原名:《喝醉後,我錯撩了閨蜜的小叔》【蘇撩 甜寵 教授 七歲年齡差 校園 救贖】【蘇撩腹黑小叔X古靈精怪少女】江落是十足的手控,為了一張手照,搭訕了一位帥哥,不料事後發現,對方居然是她閨蜜的小叔!江落腰板挺直,站姿乖巧:“小、小叔好。”……多年後,南大突然傳出生物學係的高嶺之花傅教授已經結婚的謠言。同事:“傅教授,這些謠言都是空穴來風,你別信……”“澄清一下,這不是謠言,”傅紀行冷靜補充,“我確實結婚了。”!!!江落跟傅紀行扯證時,她正讀大四。扯完證回去的路上,男人手裏拿著小本子,溫聲提醒:“喊了我這麼多年的小叔,是不是該換一下稱呼了?”“什、什麼稱呼?”“比如……”男人的吻落在她唇上——“老公。”
21.2萬字8 82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