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時已到》 170 這是可以直接問的嗎?
隨后便有一道溫潤的聲音響起:“蕭節使請起。”
聽著這道悉而久違的說話聲,蕭牧的視線又垂低幾分,開口時聲音平穩地道:“多謝陛下,多謝太子殿下。”
殿眾人見太子將人親自扶起來,心中各有計較。
“上一次朕見到蕭卿,還是四年前……”皇帝看向殿服紫袍的年輕人,稱贊道:“今日再見,更顯威武之余,亦是愈發沉穩不凡了。”
蕭牧垂眸:“陛下盛贊,微臣惶恐。”
“不,蕭卿當得起此贊。”皇帝病弱的面孔上滿是不掩飾的贊賞之。
“蕭卿于去歲之際,將北境五城先后收復,最后千秋城之戰更是兵不刃,未費一兵一卒,此等顯赫戰功,已然傳遍四海之,遐邇著聞。而朕此番召卿京,亦正是為了封賞之事——不知蕭卿,可有什麼想要的賞賜沒有?但凡是朕能辦得到的,無不應允。”
無不應允。
帝王的無不應允——
有員悄悄看向立在殿中的年輕人。
須知上一個當真信了這話,恃功而驕,看不清自己份的,早已了奈何橋邊的冤魂了。
“北境近年之戰縱有所,卻也皆是因陛下福佑四海,澤被大盛,而非微臣之功,而無功自不敢邀賞。”
年輕人的聲音清晰有力,語調聽不出半分諂虛偽之,仿佛事實果真如此,的確打從心底如此認為。
有幾位平日里最是舌燦蓮花的員,暗暗換了一記“后生可畏”的眼神——拍馬屁的最高境界,莫過于此了。
能兵不刃從契丹人手中收回千秋城的人,果然不是個莽的。
皇帝笑了兩聲,搖了搖頭:“不,有功便該賞,蕭卿既不愿開口提,那朕便也只能看著給了……”
Advertisement
說著,似思忖了一瞬,神關切地道:“說來,蕭卿這些年來常年忙于戰事,且每每親自領兵,諸事總要親力親為……此前與大大小小的捷報一同送京中的,亦有蕭卿又添傷病的消息,朕次次聽之,皆覺憂心不已。”
蕭牧聞言只做出恭謹之,并未急著接話。
果然,皇帝接著便說道:“如今北境戰事稍歇,蕭卿有無想過,于京師歇養數年,好好養一養傷?朕已命人為蕭卿于京師重新修葺府邸,且蕭卿這些年來為國事而勞神,早已過了議親的年紀,恰也可趁此機會將自己耽誤已久的終大事提上日程了。”
殿霎時間更是寂靜可聞針落。
于京師歇養數年養傷……
——然后呢?
若單單只是上兵符做一位閑散侯爺,那已是所能想到最好的收場了……
此一番話中,值得揣之太多了。
一道道晦的目,無聲地聚集在了那道年輕的影上。
這位定北侯絕非愚笨之人,不會沒有猜測。
而武將又多了幾分,這般所謂“賞賜”,當真愿意接下嗎?
殿安靜了幾息。
直到那位大盛建朝以來最年輕的節度使大人抬手行禮,平靜道:“一切但憑陛下妥善安排,臣無異議。”
立于文臣之首的姜正輔微微轉頭看向那位年輕人。
只見對方目不斜視,面上看不出半分不滿,亦或是不安。
皇帝回過神來,面上多了分笑意:“朕是覺得蕭卿當真到了該家開枝散葉的年紀了,若能留在朕跟前,朕亦能幫著持幾分……說到此,朕忽然想起來,此前朕之命,攜京中閨秀畫像前往營洲替蕭卿說親的,是否有些辦事不力之嫌,怎半年之久尚未能替蕭卿促一段姻緣出來?”
蕭牧斂眸:“是微臣一直無暇顧及此事,怠慢了才是。”
“原來如此。”皇帝面慈和:“日后若是久居京中,機會便多得是了……”
蕭牧應了聲“是”,話至此,眼看當下已近要將久留京中之事敲定下來,從始至終卻仍未曾出半分異。
個別站在后面一些的員不目思索。
雖說是個人皆能裝上一裝,說幾句謙恭順從的話,但這位蕭節使此番奉召京非但沒有二話,還把家中老娘都給帶來了!
這怎麼看怎麼都不像是有反心的樣子……
因有著這般前提在,此時如此態度,便更讓人下意識地想要相信幾分了。
畢竟這是將自己和親娘的命都擺到桌案上來了,一個不慎那可就是……
若果真有不臣之心,豈敢又豈會做到如此地步?
姜正輔眼底晦暗不明了片刻,正要出列之際,只聽一道聲音在自己前面開了口——
“父皇。”
太子恭聲道:“兒臣以為,北境雖說得此一時平穩,是因有蕭節使先后收復五城之威懾在此,此時若是北境忽然易帥,只怕會讓那些異族聞風而,再起禍心——而北境近年來雖說打了不勝仗,卻也耗損頗多,正是需要休養生息之際,實在不宜再冒此險。”
皇帝聞言笑了笑:“朕也只是隨口同蕭卿一提……如此大事,定然還是要好生商議一番的。”
有員暗暗相覷。
那便是試探的意思了?
但聽這意思,也并不會因為試探出如此結果,便就此打消這個念頭……
太子躬道:“是,父皇一貫圣明。”
說著,笑著看向蕭牧:“北地尚未真正太平,尚需蕭節使坐鎮——只是吾如此不肯放蕭節使清閑,不知蕭節使可會怨怪?”
聽出他話中用意,蕭牧道:“太子殿下言重了,為武將,護佑疆土乃是職責所在。微臣不過一介武夫,只會打仗而已,于國之政事一竅不通,故一應之事應皆由陛下與太子殿下做主,微臣只當命行事,以己盡全力守大盛江山太平。”
一介武夫?
姜正輔于心底無聲冷笑。
自踏這大殿之開始,對方的一舉一,一言一行,可都不像是所謂“一介武夫”。
一旁的員悄悄看了眼姜正輔的神后,站了出來道:“臣亦認為,蕭節使如此年輕,正是建功立業之時,若就此久居京師,倒的確大材小用,白費這一武功謀略了……”
言畢,頓了頓,才笑著往下說道:“且臣聽聞,昨日蕭節使城之際,城中萬人空巷,百姓皆自發前去相迎,場面極為轟,可見蕭節使之威名非但響徹北地,于京師之亦是家喻戶曉。據聞城中百姓多有人言,蕭將軍乃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將才,上一個這般年輕便立下如此不世戰功的,還是……”
他說到此,忽地頓住噤聲,面上笑意盡除,取而代之的是‘不慎失言’的局促和不安。
這句話并未說完,但那所謂的‘上一個’是何人,是殿大多數人皆心知肚明的。
坐在龍椅上的那位,更是再清楚不過——
皇帝微下耷的眼皮了,心神驀地被牽之下,啞著聲音咳了起來。
“陛下……”一旁的監連忙替皇帝拍背。
那“說錯話”的員神忐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太子抿了抿角。
蕭牧微微抬眼,靜靜看向那巨咳不止的皇帝。
殿氣氛一時凝滯,有人噤若寒蟬頭也不敢抬,有人悄悄拿復雜中帶有一同的目看向蕭牧。
皇帝的咳聲漸漸停下,無力地靠在龍椅,像是渾的力氣都被這陣巨咳耗了一般,渾濁的眼中被巨咳出了一點淚,微的雙手扶上龍椅兩側的蟠龍紋浮雕。
一片雀無聲,有年的聲音打破了這份寂靜:“蕭將軍的威名我也久聞了,今日還是頭一回見著真人。說來昨日蕭將軍進城時,我在一家酒樓也遙遙看到了城中的盛況,想我京當日,都沒那般排場呢!”
蕭牧聞聲看向那年。
這番話,若換作別人來講,定是如方才那位“失言”的員一樣別有居心——
但換了這位的話……
那就是純粹的口無遮攔,跟風之言了。
蕭牧對此很是篤定,畢竟,對方也算是他看著長大的了。
這著親王朝服的年,是當今圣人第四子湘王,前年剛出京前往封地。
看來湘地的吃食不錯,昔日的小圓團子,如今已長了大團子。
蕭牧認出了對方之下,遂道:“湘王殿下抬舉臣了,臣甚踏足京師,昨日城時也未有太多靜,按說不該驚擾城中百姓至此,不知因何鬧出了昨日之況,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實在多有慚愧。”
太子聞言即道:“蕭節使太過謙虛了,如此盛況,蕭節使之功,遠當得起。只是……昨日之事,的確略有蹊蹺,蕭節使本是低調京,卻引來如此之大的靜……”
太子思索間,面向階的方向:“父皇,兒臣覺得此事或有些不尋常,不知是否要查一查?”
皇帝渾濁的眼中浮現一抹猶疑之,片刻后,緩一點頭:“當查……”
湘王愣了愣。
他就這麼隨口一跟,怎還要查上了呢?
察覺到似有人在拿一言難盡的目看著自己,湘王殿下尷尬之下,忙想著要岔開話題,于是一個好奇已久的問題就口而出:“對了蕭節使,本王聽說你手中握有一張藏寶圖在,不知是真是假?”
眾員:“……?!”
這是可以直接問的嗎?
猜你喜歡
-
完結913 章

步生蓮:六宮無妃
她是名滿京城的才女,他是當今炙手可熱的皇位繼承人。他曾許諾,六宮無妃,隻有她一個皇後。可是慢慢的,誓言一點一點的變了,難道真的是色衰而愛馳嗎?他殺了她滿門,滅了她家族,一步步將她推向了深淵。情是甜蜜的源泉,也是斷腸的毒藥。她恨,可是到頭來才發現,一切都是宿命罷了!
163.4萬字8 9116 -
完結990 章
大佬們的團寵又嬌氣了
重生前, 阮卿卿:顧寒霄嘴賤又毒舌,就算長得好看,身材又好,我也不會喜歡上他! 重生後,真香! 前世她遇人不淑,錯把小人當良配。 現在,阮卿卿發現顧寒霄和自家哥哥們都把自己寵上天。 渣男敢厚著臉上門? 是大佬的愛不夠深,還是哥哥們的寵不夠甜,統統踢出去! 白蓮花們看不慣? 有能耐讓你爸媽再生幾個哥哥寵你們啊!
91萬字8 14558 -
連載432 章

將軍懷里的小嬌嬌是玄學大佬
【1v1+高甜+團寵+追妻火葬場!】 謝家老太太從外面買了個小姑娘,說是要給謝將軍做夫人,得知此事的謝將軍:我就是這輩子都站不起來,也不會娶這樣心機深沈的女人! 小姑娘紅著眼眶點頭:我明白的,將軍。 謝將軍的親祖母:他看不上是他沒福氣,衍都青年才俊多得是,我回頭給阿拂好好物色物色,他腿都斷了,還配不上我們阿拂呢。 謝將軍的親弟弟:那只好我將來長大後娶阿拂姐姐為妻啦~ 謝將軍的親妹妹:原來哥哥竟是傷了腿,我還以為哥哥是傷了眼睛,怎麽如此沒眼光! - 後來,謝將軍瞧著姜拂對著旁人笑,覺得異常刺眼。 他將人按在門口,委委屈屈道,「阿拂,別怕我。」
38.8萬字8 19113 -
完結1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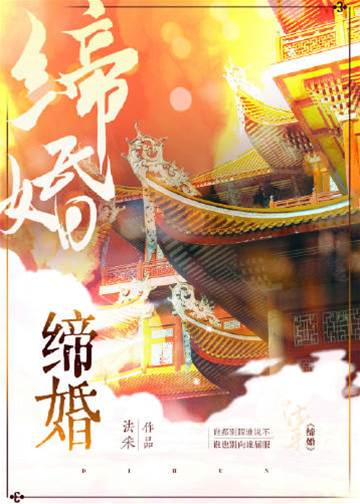
締婚
家敗落之後,項家老爹成了人人喊打的奸佞,項宜帶著幼年的弟妹無依無靠、度日艱難。 她尋來舊日與世家大族譚氏的宗子、譚廷的婚約,親自登了譚家的門。 此事一出,無人不嘲諷項家女為了算計、攀附譚家,連臉面都不要了。 連弟弟妹妹都勸她算了,就算嫁進了譚家,...
45萬字8.33 82137 -
完結170 章

娘娘嫵媚妖嬈,冷戾帝王不禁撩
一紙詔書,廣平侯之女顧婉盈被賜婚為攝政王妃。 圣旨降下的前夕,她得知所處世界,是在現代看過的小說。 書中男主是一位王爺,他與女主孟馨年少時便兩情相悅,孟馨卻被納入后宮成為寵妃,鳳鈺昭從此奔赴戰場,一路開疆拓土手握重兵權勢滔天。 皇帝暴斃而亡,鳳鈺昭幫助孟馨的兒子奪得帝位,孟馨成為太后,皇叔鳳鈺昭成為攝政王,輔佐小皇帝穩固朝堂。 而顧婉盈被當作平衡勢力的棋子,由太后孟馨賜給鳳鈺昭為攝政王妃。 成婚七載,顧婉盈對鳳鈺昭一直癡心不改,而鳳鈺昭從始至終心中唯有孟馨一人,最后反遭算計,顧婉盈也落了個凄然的下場。 現代而來的顧婉盈,定要改變命運,扭轉乾坤。 她的親夫不是癡戀太后嗎,那就讓他們反目成仇,相疑相殺。 太后不是將她當作棋子利用完再殺掉嗎,那就一步步將其取而代之。 如果鳳鈺昭命中注定要毀在女人手上,那麼也只能毀在她顧婉盈的手上。
32.1萬字8 10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