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千歲[重生]》 第1章 第 1 章
五更天,夜半褪,曦。
帝王寢宮之,燈火煌煌,監們在偌大宮殿里穿梭往來,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喜氣。今兒是陛下登基的大喜日子,廷四司八局十二監,為了這一日已經籌備了將近一月,眾人從三更天就開始忙碌起來,連素日寂靜冷清的宮殿也染上了幾分人間煙火氣。
殷承玉立于銅鏡前。
等高的銅鏡中映出一道著明黃中的瘦削影。青年寬肩窄腰,烏發雪,上揚的目里蘊著與生俱來的貴氣。
長久凝視著銅鏡里窄長的人影,殷承玉角勾起淺淺弧度,直到后傳來不輕不重的腳步聲,銅鏡里又映出另一道暗紅影,他才斂了笑。
一緋紅蟒袍的薛恕捧著皇帝冠冕行至他后,明黃中與緋紅蟒袍在銅鏡中疊糾纏,連聲音也變得曖昧起來:“臣為陛下更。”
殷承玉自銅鏡中瞥他一眼,之后便垂下眼睫,舒展手臂,任由他作。
袞、下裳、蔽膝……薛恕一樣樣為他穿戴妥帖,最后才拿起托盤里的白玉革帶,繞至殷承玉后,雙手自他腰側穿過,如同環抱一樣將他攏住,修長手指靈巧地將革帶上的玉扣扣上。
合上的玉扣發出“咔噠”一聲輕響,他卻并未退開,而是就著這個姿勢,攏住纖瘦的腰,將人帶懷中。
“恭喜陛下,終于得償所愿。”
他將下抵在殷承玉肩窩,帶著溫度的吐息盡數落在脆弱敏.的側頸,激起一連串細小的皮疙瘩:“這大喜的日子,不知陛下可能讓咱家也一償夙愿?”
宦特有的尖細嗓音被刻意低,暖燭里,疊的影仿佛也染上了幾許溫繾綣。
殷承玉抬起眼,過銅鏡與他對視:“廠臣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還有何心愿未了?”
Advertisement
耳側傳來一聲輕笑,腰上的手臂也隨之收,薛恕以鼻尖在他耳廓輕,如同.人耳語一般道:“陛下明知道臣想要什麼。”說完,直的鼻梁順著耳廓線條下,至側頸流連輾轉。
這是他們彼此都非常悉的作,再往下,后的人便要用上齒了。
殷承玉閉了閉眼,揮開腦海里不合時宜浮現的旖旎畫面,角抿直:“廠臣要的,朕恐怕給不起。”
“是給不起,還是不想給?”
后擁著他的人卻仿佛忽然被到了逆鱗,單手著他的下,強迫他轉過臉來和自己對視,眼底布滿暗:“還是說……陛下亦鄙夷咱家這等閹人,恥與為伍?”
每回他生氣時,便不稱“臣”,總怪氣地稱“咱家”。
殷承玉從不慣著他這一生氣就忤逆犯上的壞病。
下被掐得生疼,他氣急,掙扎著坐起來,罵了一聲“混賬”。
外頭守夜的小太監聽見靜,小心翼翼進來,隔著床帳輕聲詢問:“殿下可是醒了?眼下才四更天。”
殷承玉恍惚間回過神來,這才意識到只是在做夢,了眉心,疲憊道:“無事,退下吧。”
小太監聞言放輕了步伐,又輕悄悄地退了出去。
殷承玉卻再睡不著了。
他已經連著三晚夢見前世之事,夢見薛恕。
按照上一世的軌跡,再過三天,便是薛恕凈宮的日子。之后五六年里,他將從宮中最不起眼的小太監,一步步往上爬,最后坐上西廠督主之位。皇帝寵信,權勢遮天,連皇位亦能輕易左右,時人稱之為九千歲。
而再有三個月,皇帝與二皇子黨便會對他出手,先是外家虞氏牽扯進貪墨案中,滿門盡誅;再是母后驚早產,一尸兩命;他的太子之位亦會被廢,從尊貴無雙的一國儲君變棄子,自此幽皇陵,孤立無援。
直到薛恕迎他回朝。
他們之間原本不過一樁不摻、利益互換的易,卻因糾纏了數年,間隔了生死,也變得濃郁厚重起來。
有幸重來一回,他本不再與薛恕生出糾葛。
可每至深夜,那一雙著偏執的暗沉眼眸便自眼前晃過,耳邊是一聲聲著譏諷的質問:“陛下亦鄙夷咱家這等閹人,恥與為伍麼?”
陛下亦鄙夷咱家這等閹人,恥與為伍麼?
這樣自輕的話薛恕只對他說過一次。
他似乎從未自卑于自己宦的份,床笫之間,也總是霸道而強勢,就算沒了那件,也總有層出不窮的法子他認輸求饒。
但他卻從未當著他的面寬解帶過。
仔細想來,多還是在意的罷。
而如今,改變薛恕命運的機會就在眼前。
殷承玉滿心煩躁地起,站在窗戶邊吹了許久的涼風,才平靜下來。
找,還是不找?
今日是隆十七年臘月初五,薛恕曾與他提起過,他是在臘月初八那日在蠶室凈了,之后使銀子拜了直殿監某個老太監為師,才被帶了宮。
臘月初八正是臘八日,日子特殊,殷承玉當時只聽了一耳朵,便牢牢記住了。只是京城中蠶室亦有數家,他并不清楚薛恕當初去的是哪一家。
若要找,恐怕得花些功夫。
但每每想到那人曾用在他上的惡劣手段,又覺心氣難平,無法下定決心。
在窗前立了許久,殷承玉才復又睡下。
這一覺依舊睡得不安穩,前世之事在夢中紛雜而過,翌日早晨殷承玉醒來時,只覺得一陣頭昏腦漲,眼下也浮起濃郁青黑。
原本尚未痊愈的,越發顯得孱弱。他掩著咳嗽幾聲,召了心腹太監鄭多寶進來。
“殿下怎麼咳得更厲害了?”鄭多寶剛進門就聽到低的咳嗽聲,頓時便顯了急,手里穩穩端著湯藥,上卻已經在催促小太監去請太醫來。
“無礙,只是昨晚吹了涼風。”殷承玉接過湯藥一口飲盡,用帕子按了按角,朝鄭多寶招了招手:“孤另有事代你去辦。”
鄭多寶附耳過去,聽完之后神詫異,一副想問又不敢問的樣子。
殷承玉正心煩著,不多加解釋,只揮了揮手:“盡快。”
鄭多寶見狀只得下疑,匆匆出門辦事。
要說在這京城里打聽蠶室,恐怕沒有人比凈了的太監們更清楚。
大燕建國二百余年,最初時宦地位低下,不許讀書習字更不許議論朝政。但隨著時間推移,朝堂上文臣黨派愈發勢大,皇帝為了節制文臣,便越發親近倚重邊的侍,不僅在宮中增設了書堂,教導太監讀書識字。甚至還允許宦參與朝堂政務,致使宦權勢愈大。
到了如今,廷二十四衙門之首的司禮監的掌印太監掌批紅之權,連閣首輔亦要以禮相待;秉筆太監提督東廠,錦衛亦要屈居其下。
宦權勢之盛,可見一斑。
世人逐利,閹人雖名聲不好聽,但利字當頭,便有越來越多百姓自愿將家中男丁凈送宮中,博一個富貴前程。
燕王宮中并未專設凈的蠶室,宮中一應侍都由有資歷的大太監自宮外招收,是以京城開設了不蠶室。若家里心慈些,便會將孩子送至專門的蠶室凈;但也有那心狠的,舍不得銀錢,便走偏門尋那劁牲畜的手藝人,只當牲畜一樣劁了,生死由天。
鄭多寶按照殿下的命令,派遣數人暗中尋訪了兩日,找遍了大大小小的蠶室,卻并未找到殿下所說之人。
眼見著臘八之期將近,所尋之人卻沒有半點蹤跡,他只能死馬當活馬醫,命人擴大了范圍,連帶著將那些劁牲畜的手藝人也都探訪一遍。
*
三日之期轉眼即至。
大燕恢復古禮,遵循前朝舊制,每年立春、元宵、端午、重、臘八日都要行嘉禮,于午門外設宴,宴請群臣。
按例皇帝當出席與群臣同宴,以示親近之意,但隆帝素來不喜應付朝臣,自然將這差事推給了已經參政議事的殷承玉。
殷承玉是嫡長子,外祖父虞淮安又是閣首輔,剛滿七歲就被立為太子,至十四歲便已朝參政。自小便被當做儲君教導。早早明白自己肩上擔著的重任之后,更是嚴于律己,從不敢有半分懈怠,努力去做一個眾人心中完的儲君。
隆帝給他的事,不論大小,他皆不計利益得失,全力以赴。
上一世這個時候,他因思勞過度染風寒病倒,病反復,纏.綿病榻十日之久。還未痊愈,就又接到隆帝讓他負責臘八宴的旨意。
為太子,為君分憂,為父解愁,他都沒有推拒的理由,仍拖著病接了下來。
結果臘八宴之后,他病加重,發起了高熱,昏迷了整整兩日。雖然后頭病好了,底子卻虛了不,還落下了頭疼的病。
那時年倔強,明明不適也不肯出半分,還要謝父皇信重,配合隆帝演足了父慈子孝的戲碼。
可實際上呢?
他克己復禮,凡事追求盡善盡,在朝臣和市井百姓當中名聲愈盛。又有強有力的外家支持,聲甚至快要高過皇帝,早就了隆帝的眼中釘中刺,恨不得拔之而后快。
所以后來大舅舅遭人攀誣構陷,牽扯進私鹽案里,外祖甚至整個虞家也都牽扯其中,他幾次請命徹查,隆帝卻連查都不肯細查,便匆匆定罪發落。
說到底,虞家不過是了他的連累罷了,隆帝從始至終想要除掉的威脅,是他。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先是君臣,才是父子。
只可惜這個道理,殷承玉直到被褫奪太子之位的那一刻,才深刻的明白。
是以重來一次,他并不打算再做個為父分憂的孝子。
思緒流轉間,殷承玉笑著推拒了吏部尚書的敬酒,他掩咳了幾聲,雪白的面因此添了幾分紅,卻反而更顯病弱。
舉起面前的清茶,殷承玉笑了笑,道:“孤近日不適,不宜飲酒,便以茶代酒與盧大人共飲一杯。”
盧靖連道不敢,敬完酒回到座位上,與邊上的吏部侍郎慨道:“太子殿下當真勤勉,生了病還不忘我們這些臣子。比起那位來真是……”他朝著東邊努了怒,用氣音小聲道:“強了不是一星半點。”
臘八日賜宴群臣,原就是君王親近群臣之意。
但隆帝寵信宦,又因孝宗在位時太過荒,君奪臣妻,發生過臣子當宴刺殺皇帝之事,是以對他們這些朝臣十分防備。
除了剛登基那兩年,后來隆帝從不在宴會面,直到太子年歲大了,才太子出面。
如此遭君王猜忌,朝臣們口上不敢說,心里多是有疙瘩的。加上隆帝雖然比不上孝宗的荒無度,卻也不是什麼明君。他能力平平,又耽于聲樂,荒廢朝政。若不是太子早早立了起來,又有虞首輔坐鎮閣,這朝堂早就不知道了什麼樣。
兩人換了一個眼神,默契地打住話題,沒有再往下說。
只不過心里都想著,幸好還有太子。
殷承玉故意在宴上了病態,朝臣們殷切關心一番、勸說他保重之后,便沒人再來敬酒。殷承玉樂得清凈,捧著暖爐有一搭沒一搭地喝茶。
暖融融的熱茶熨帖了腸胃,他愜意地瞇了眼。
這樣可比上一世時,他強撐著不病,一杯接著一杯喝酒來得舒心。
宴至半途,鄭多寶神匆匆進來,附在他耳邊道:“殿下,人尋到了。”
殷承玉神微振,看到下方好奇看過來的朝臣,下意識想說“宴罷再議”,但接著又想起他沒必要再循著上一世的模樣來活,索便捧著暖爐站起來,朝看過來的群臣頷首道:“孤有些不適,便先行一步,諸位大人盡興。”
猜你喜歡
-
完結1099 章
鳳女重生:侯爺夫人要複婚!
前世,許瑾瑜將豺狼虎豹當成了良人,闔府被斬首,自己也落得個葬身火海的下場。最後她才知,那個冷心冷情的人將自己愛到了何等地步。重活一世,許瑾瑜想要馬上上了花轎,跟那人和和美美的過完這一生。可是還冇走兩步,就看到了那人,一本正經的說道。“雖家父與叔父早已有言在先,可婚姻大事並非兒戲,既大姑娘不願,我亦是願意就此解除婚約。”許瑾瑜握緊了自己的小拳頭,眼裡起了一層薄霧,直接噠噠噠的走了過去。“侯爺戰功顯赫,為世人敬仰,理應知道流言不可儘信,現如今又怎可因為流言就要解除婚約呢?”孟敬亭冷心冷情,從未對任何人動過心,可是卻被這眼前的小姑娘給軟了心腸。
131.7萬字8 50226 -
完結77 章

奪金枝(重生)
虞莞原本是人人稱羨的皇長子妃,身披鳳命,寵愛加身。 一次小產后,她卻眼睜睜看著夫君薛元清停妻再娶,將他那個惦記了六年的白月光抬進了門。 重活一次,本想安穩到老。卻在父母安排的皇子擇婦的宴會上,不期然撞進一雙清寒眼眸。 虞莞一愣。面前此人龍章鳳姿,通身氣度。卻是上輩子與薛元清奪嫡時的死敵——模樣清冷、脾氣孤拐的的薛晏清。 迎上他的雙目,她打了個哆嗦,卻意外聽到他的一句:“虞小姐……可是不愿嫁我?” - 陰差陽錯,她被指給了薛晏清,成了上輩子夫君弟弟的新娘。 虞莞跪于殿下,平靜接了賜婚的旨意。 云鬢鴉發,細腰窈窕。 而在她不知道的上輩子光景里—— 她是自己的長嫂,薛晏清只能在家宴時遠遠地看她一眼。 再走上前,壓抑住眼中情動,輕輕喚一句:“嫂嫂。” 【又冷又甜薄荷糖系女主x內心戲起飛寡言悶騷男主】 1V1,男女主SC 一些閱讀提示:前期節奏有些慢熱/女主上輩子非C,介意慎入 一句話簡介:假高冷他暗戀成真。 立意: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20.2萬字8 39694 -
完結139 章
我以為我拿的救贖劇本
一朝穿越,虞闕成了修真文為女主換靈根的容器。好消息是現在靈根還在自己身上,壞消息是她正和女主爭一個大門派的入門資格,她的渣爹陰沉沉地看著她。虞闕為了活命,當機立斷茍進了一個不知名的小門派。入門后她才發現,她以為的小宗門,連師姐養的狗都比她強…
62.6萬字8.33 16859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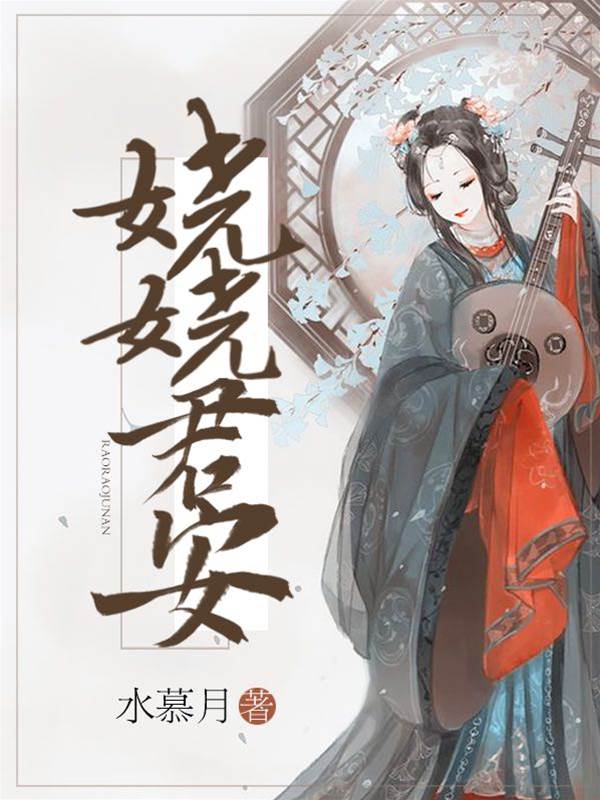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