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補習班》 第二零五章 章節名是什麼
“都……都督。”趙白臉很不願的的了一聲,板著臉一本正經道:“以前的事不說也罷,今日職下已經前來,不知今後你對我有何安排。”
“這個不急。”李昊笑盈盈的問道:“趙都尉剛剛從勳府調過來,要不要先休息幾天,等悉一下況之後再來?”
“不必。”趙文遠冷冷拒絕。
雷耀眉頭皺了皺,心底生出一厭惡。
丫有背景怎麼了,我家都督也不是白,年紀輕輕居高位,能做到如此地步已經很不容易了,爲何這姓趙的依舊如此不識擡舉。
李昊不聲點點頭:“那好吧,既然趙兄執意如此那便先去船上悉悉水。咱們畢竟是水師,第一要務便是悉水上環境,學會鳧水,所以上船之後無論職務高低統統聽從原長安水師那些兄弟的指揮,這一點還趙兄理解一二。”
趙文遠撇撇,有些不屑。
數年的錦玉食生活讓他忘記了什麼人爲刀俎我爲魚,轉出門上跟隨自己而來的小廝,又臨時抓了一個守在門口的守衛帶路,向著停靠在碼頭上的戰船而去。
來此之前,趙文遠就已經料到李昊必然不會讓自己有好日子過,事實也證明的確如此,這傢伙沒給自己派上任何職務便打發自己上船,想來是要給自己一個下馬威。
來到船邊,著高達十餘丈的五牙戰船,趙白臉哼了一聲,暗道李昊小看人,不讓給老子安排職務怎麼了,老子一明鎧,難道船上的人都是傻子,看不出老子都尉的份?
邁著八爺步,打發了守衛離開,趙文遠帶著小廝上了船。
戰船上,數百條漢子站在船邊,手裡拉著繩子,互相之間打著哈哈對下面指指點點。
Advertisement
趙文遠不明所以,正打算走過去看看,不想卻被人攔了下來:“站住,你是何人,爲何來此?”
“你又是何人?本都尉左領軍衛趙文遠,奉……奉都督之命前來悉水。”趙文遠翻了個白眼,每次想到以後要李昊都督,心裡就膈應的不行。
左領軍衛?攔住趙文遠那人上下打量他一眼,善意勸道:“都尉,若要悉水……你最好把這一明鎧換下來。”
趙文遠聞言大怒:“憑什麼?你什麼份也配讓老子換服?”他還要靠這一裝備撐門面呢,換下來誰還拿當個打幾。
阻攔趙文遠那漢子也是個妙人,被罵了也不著腦,只是一揮手:“來人,給趙都尉上裝備,趙都尉要悉一下水。”
趙文遠混到今天這個位置靠的就是一張,和老丈人的扶持,他哪裡知道什麼悉水,懵懵懂懂被兩個漢子用繩子套在腋下,著跟他們來到船邊,還沒等看清下面水裡的況,屁上已經被人重重踹了一腳。
“我··你大爺……”
一頭栽向水中的趙文遠還沒罵完,“噗通”一聲便砸進水裡。
明鎧四十多斤,穿在上就算水再好都不一定能浮起來,更不要說趙白臉一個旱鴨子,水之後連掙扎都省了,連個泡都沒冒直接沒了影子。
跟著趙文遠上船的小廝臉都綠了,好半晌才悽慘的聲:“我的姑爺啊……,快,快把我家姑爺拉上來。”
拉上來?還早呢,拉著繩子的傢伙任由手中繩子不斷往水中著,淡淡瞥了一眼小廝,理都沒理他。
這幾天下來,船上這幫傢伙經驗富的不得了,很清楚多長時間能把人淹死,多長時間能把人淹的半死不活。
一個左領軍衛跑來驗生活的倒黴孩子罷了,只要沒淹死,上面就不會追究。
自從更名遠洋水師之後,長安水師每一個人都膨脹了許多,兄弟單位的都尉算什麼,國舅爺家的大公子,盧國公、英國公家的大公子老子們都踹下去過。
正所謂蝨子多了不,債多了不愁,老子憑本事踹下去的,想啥時候拉上來就啥時候拉上來。
大概過了二十多個呼吸的功夫,幾個布漢子覺得時間差不多了,幾人一齊手,將已經被淹到半死,兩眼已經翻白的趙文遠拉上了船。
不容易啊,老子就是想裝個,就是不想失了份而已,至於這麼灌老子麼!
剛剛到遠洋水師報到不足兩刻鐘,趙文遠就被半死不活的擡了回去。
著遠去的車隊,李昊慨道:“這傻·腦子裡裝的都是粑粑麼,明知在老子手裡不會有好果子吃還敢來,真以爲老子怕了他那個老丈人不。”
雷耀:“……”
長就是長,不計名利,不計得失,快意恩仇,果然是我輩之楷模,跟著這樣的長以後可得小心著點,否則鬼知道哪天會不會被坑死。
幾個新羅匠人又再次被了回來,圍在一起討論起李昊給他們的設計方案,嘰嘰咕咕的新羅語聽的人頭疼。
不過雷耀不在乎這些,他在乎的是那些造型詭異的大船。
以他的經驗來看,這船本就是在扯蛋,畢竟古往今來所有的船都是平底的,可新任都督拿出來的設計方案卻是尖底的。
慶底船?那還不翻了?
可是……,想想趙文遠那倒黴孩子的悽慘結局,雷耀還是理智的閉上了。
反正又沒花自家的錢,想咋折騰就咋折騰唄。
新羅船匠其實也是懵的,如果不是考慮在大唐吃的好,喝的好,還有工錢可拿,只怕早就掀桌子不幹了。
尖底船啊,這到水裡非翻嘍不可,喝在船翻了死的是唐人,可誰又能保證上頭不追究船匠的罪責,萬一上面追究起來,人頭可就要保不住了。
商量了半天,其中一個匠人來到李昊面前:“爺……”
“怎麼了?”聽著半生不的大唐話,李昊皺了皺眉:“老樸啊,不是我說你,你能把舌頭拉直了說話不。”
老樸的頭更低了,但在衆同伴鼓勵的目中,還是起頭皮說道:“爺,您設計的船似乎有些問題,這尖底船我等從來沒有造過,只怕造不出來。”
老僕深諳爲人世之道,功勞是領導的,責任是自己的,爺設計的船是沒有錯的,錯的是他們手藝不,造不出尖底船。
雷耀不得不替這位來自異國他鄉的船匠挑起大拇指,姜果然是老的辣,並且跟地域無關。
“確實造不了麼?”李昊拉過桌上圖紙,看了看:“若真是這樣,你們就回去吧,我會跟金俊英說一聲,讓他再給我換一批人來。”
釜底薪這一招還是蠻厲害的。
在大唐數月的生活讓新羅船匠嚐到了甜頭,初時他們是不想來,現在嘛……誰要趕他們走他們就跟誰急。
老僕聽到李昊要換人,當下連忙搖頭:“不,不是這個意思,小人的意思是說,我們需要好好研究研究,需要的時間可能稍微長上那麼一些。”
李昊出亮閃閃的門牙,似笑非笑的問道:“只是時間長一些?”
“呃……,爺放心,最多半年,一定可以造出來。”
“那好,既然這樣,你們就先回莊子上吧,把人手調配好,半個月後等這邊的船塢建好,就開工。”
“諾!”老僕無奈點頭,本想借著本事不夠的理由能夠打消這位小爺的不切實際的念頭,結果卻給自己找來一大堆麻煩。
……
……
金勝曼已經在李家莊子上待了半年了,就算再遲鈍,也搞清楚了這莊子是屬於誰家的。
每每想及此,金勝曼公主就恨的咬牙切齒。
虧自己還以爲已經逃出魔掌,虧自己當初還覺得這莊子的主人低調奢華有涵,可沒想到,一切都是自做多,到頭來是非敗轉頭空。
估計那該死的傢伙應該早就知道自己在他的莊子上吧。
可惡的傢伙竟然如此榨自己的勞力,明明賺那麼多錢,卻只肯付給自己十五貫的月錢,想自己堂堂公主,貌如花,竟然被一個小人算計……。
算了,還是別想那麼多了,去看看那些可憐的船匠吧,那些可憐的人自從來到大唐就一直被丟在莊子上無人理會,每天只能以大米餬口,連點都沒有,真是太可憐了。
帶上莊子分配給自己的小丫鬟,坐上莊子分配給自己的馬車,上莊子分配給自己的車伕以及四個護衛,帳房金先生直接殺奔莊外新羅船匠的聚居地。
……
……
衛國公府,李靖在看書,紅拂在清理帳冊,窗外月明星稀。
在一連串‘我兒子真能幹’,‘我兒子真了不起’,‘也不知將來誰家姑娘運氣好能嫁給我兒子’的慨中,李靖的書終於看不下去了。
“夫人,我說你這是怎麼了。”
“夫君,你知道咱家現在有多錢?”紅拂把手裡帳冊擋住,神的問道。
“那誰知道……”在老婆大人漸漸冰冷的目中,李靖臨時改口道:“估麼怎麼也有幾十萬貫吧,那小子雖然賣酒賺了錢,可這段時間也沒。”
“幾十萬貫?”紅拂撇撇,一副嫌棄的樣子:“夫君,你就不能把眼放長遠點,若只有幾十萬貫,妾還會問你?”
猜你喜歡
-
完結4306 章
魔帝纏身:神醫九小姐
“夫人,為夫病了,相思病,病入膏肓,藥石無醫,求治!”“來人,你們帝尊犯病了,上銀針!”“銀針無用,唯有夫人可治,為夫躺好了。”“……”她是辣手神醫,一朝穿越成級廢材,咬牙下宏願︰“命里千缺萬缺,唯獨不能缺男色!”他是腹黑魔帝,面上淡然一笑置之,背地里心狠手辣,掐滅她桃花一朵又一朵,順帶寬衣解帶︰“正好,為夫一個頂十個,歡迎驗貨。
385.4萬字8 113543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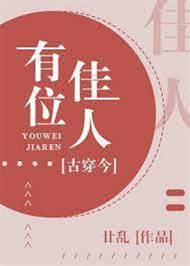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241 -
完結251 章

鳳馭天下:無情狂后
她是二十一世紀某組織的頭號殺手,因同伴背叛而中彈身亡,靈魂穿越到北越國,成為侯爺的女兒。而他則是深沉睿智的年輕帝王,運籌帷幄,步步為營,只想稱霸天下,當無情殺手遇上冷情帝王,當殺手與帝王共創霸業,結果會怎樣呢?…
70.2萬字8 17556 -
完結527 章

穿成五個反派的後孃
一朝穿越,竟然成了彆人的後孃,而且幾個孩子,個個都長成了大反派。究其原因,是因為這個後孃太壞太狠太不靠譜。喬連連汗顏,還好老天讓她穿過來,從此以後溫柔善良耐心矯正,幾個孩子從豆芽菜變成了胖多肉。可就在這時,孩子們的爹回來了。
91.5萬字8 302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