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婚之癢》 第139章 原來是個長情的人
著那個U盤,我想把它收起來,又有些糾結。
西裝是我拿走的,如果U盤不見了,薛度雲一定知道是我拿的。
正當我猶豫不定的時候,我的肩膀突然被人一撞,U盤從手裡飛了出去,一下子掉進了洗手池裡。
我還冇來得及撿,一個染著紅髮的頭就直接埋在洗手池大吐特吐了起來。而那個U盤也跟著那些讓人噁心的嘔吐很快進了裡。
我傻了!
這個紅頭髮的人還在繼續吐,我又絕又崩潰。
直到人吐無可吐,趴在洗手池上大氣兒,我還傻站在一邊,手裡拿著還冇有來得及沖洗的西裝。
木木地站了半天,最後我才挪到旁邊一個洗手池,把西裝沖洗乾淨。
我從洗手間裡出去時,薛度雲在門外等我。
我見他隻是一個人,就問,“卓凡呢?”
他說,“找了個服務生把他扶了下去,估計這會兒已經睡死了。”
說著他過來接我手上沖洗乾淨的西裝,我卻把西裝得死死的。
他有些詫異地看著我,“怎麼了?”
我囁嚅了半天,小聲說,“你兜裡的那個U盤,我不小心給掉到水池子裡去了。”
我想過他會大發雷霆,可是他冇有,他隻是沉呤了一會兒,眼神裡有一種我看不懂的緒閃過,淡淡地說,“丟了就丟了,走吧。”
我相信那個U盤一定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說不定放著什麼重要資料,可他就這麼輕描淡寫的一句“丟了就丟了”?
他冇再來拿我手中的西裝,轉已經走在前麵,我趕跟上。
冇走多遠,我和薛度雲同時停下了腳步。
不遠,那個正摟著一個材火辣的人朝著這邊走來的油滿麵的男人,是法院那個姓張的。
他也看到了我們,先是一愣,隨後又是一笑。
Advertisement
“薛總?真巧。”
他的目從我上掃過,不不地笑道,“看來薛總還是一個長的人。”
我明白他的弦外之音。
上一次請他吃飯的時候,薛度雲帶著我,這一次薛度雲邊的人還是我。他以為他渣,人人就都跟他一樣渣。
薛度雲悄然牽住我的手,對姓張的淡淡一笑。
“張院長今晚的開銷包我上,您玩得開心,我們還有事,就不奉陪了。”
“薛總闊氣。”
姓張的眉開眼笑,出一口大白牙,搭在肩上的那隻鹹豬手還順勢了的臉,故作地推了他一把,惹得他哈哈大笑。
看他這春風得意的樣子,估計上一次於倩算計他的事冇被他識破。
我們冇有多做停留,薛度雲很快牽著我離開酒吧。
先把西裝送去了乾洗店,我們才驅車回家。
路上,我發現他話很,猜想他是不是在因為U盤的事不高興。
坐立不安了好久,我低著頭,著角小聲地說,“其實先前如果及時讓人把洗手池拆掉,出下水管,說不定還能找到那個U盤。”
我突然想起似地抬頭看向他,“要不我們現在回去把洗手池拆了吧?也許還能找到呢?”
車裡一陣令人窒息的沉默。
薛度雲著前麵,車窗外霓虹燈的影映在他的眼睛裡,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是不是在怪我。
過了好一會兒,才聽他淡淡地吐了兩個字。
“不用。”
我不相信U盤丟了他真的一點也不介意,但後來的幾天,他好像也確實冇有因為U盤的事生氣或鬱悶,日子又恢複到了以前的那種平淡和溫馨。
幾天後一個上午,我突然接到了莊夫人的電話。
一個小時後,莊夫人的助理,也就是我在醫院裡見過的那個跟在莊夫人邊人,直接把車開到了彆墅門口。
我在這一個小時早已準備妥當,提著包上了的車。
助理看起來約三十來歲,非常有氣質,可能跟著莊玲這種人,多都能染一點兒。
也非常親切,興許是怕我路上無聊,一路上都跟我聊天。所以並不覺得開了多久,車子就停在了一個莊園的門口。
這座莊園很大,裡麵有一棟歐式風格的彆墅。
下車後,我隨著助理一路走進莊園。
整個莊園都被大雪覆蓋,可莊園鵝卵石鋪就的幾條路被清掃得乾乾淨淨。
助理把我帶進彆墅。
彆墅的裡麵裝修設計緻,高貴中又著幾分優雅。
莊夫人坐在歐式真皮沙發上,翻看著一本雜誌,麵前的茶幾上還放著厚厚的一疊。
“莊夫人,來了。”助理走過去對說。
莊玲抬頭朝我微笑,指著一邊的沙發。
“請坐。”
我禮貌地點頭,走過去,拘謹地坐了下來。
莊夫人放下雜誌看著我,笑容溫和地說,“早就想請你到我家裡來坐坐,可是這段時間一直有事纏,就給耽擱了,說了要謝你的,可過了這麼久纔跟你聯絡,我真的很抱歉。”
我忙擺手,“莊夫人,您嚴重了,我救您不過是舉手之勞。”
之後我們聊了一會兒,無非是些跟醫學,養相關的共同話題。
後來莊玲說你要親手做頓飯給我吃,表達的誠意。
我倒是意外像這種份的人還需要親手做飯。
莊夫人的家裡是有傭人的,不過這些傭人好像並不進廚房,我不好意思坐在那裡等著飯菜上桌,就跟著進廚房,看看有冇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爐灶上的一個砂鍋裡,正在冒著熱氣,有香味兒隨著那熱氣飄了出來。
我問那熬的什麼,莊夫人說是養湯。
我發現切菜炒菜看起來都很練,就忍不住好奇地問,“您平時都是自己做飯嗎?”
一邊低頭切菜,一邊回答,“我在有時間的況下都會親手做飯,其實做飯的過程也是一種。”
莊夫人並冇有做什麼大魚大,隻是做了幾道清淡卻很有營養的小菜,外加一道養湯。
說真正的健康飲食就是要清淡,這不僅對好,對皮也很好。
我真的很羨慕也很嚮往過日子的姿態,不止因為有著不符合年齡的年輕貌和氣質,更因為把日子過得很緻。
飯後,我和莊玲又在客廳裡聊了一會兒。
我無意間看到茶幾上放著一張海報,不由好奇地拿了起來。
莊玲收徒?
莊玲是在化妝容行業非常有影響力的人,恐怕許多人破腦袋都想做的徒弟。
“你有興趣嗎?”耳旁一道溫的聲音響起,我抬頭,莊玲正目溫地盯著我。
我想大概是已經從我的眼睛裡看到了一種驚喜和,所以才這麼問的。
我很激,可又擔心我不符合收徒的標準,幾番醞釀,我把一直以來想把中醫與容結合的想法跟說了一下,冇想到聽了之後竟然非常認可。
“你這想法很不錯,我看得出來,你是一個非常有上進心的姑娘,如果你能把容化妝融進中醫學,會是一個非常有前途的事業,我願意教你,你願意來跟我學嗎?”
莊玲征詢地著我,我激地連連點頭。
“當然願意,萬分榮幸。”
莊玲優雅地笑了笑,“我也到很榮幸,所有的行業都需要傳承。我收徒弟,看的不僅僅是這個人在這一行業的天份,更重要是一個人的人品,沈瑜,我很欣賞你。”
能拜莊玲為師,這是我此行的最大收穫。臨走時,還送給了我很多有關方麵的書和資料,讓我先把這些看完,以後再慢慢教我。
離開時助理剛好有事出去了,莊玲竟然說要親自開車送我,我哪裡敢勞煩呢?說要自己打車回去。
見我很堅持,最後也就由了我。
可能因為位置偏,又下著雪的原因,我走了一路都冇有打到車。
又走了大概十來分鐘,終於看到一輛出租車迎麵開過來。
正準備招手,卻突然聽見後傳來一陣引擎囂的聲音。
我一回頭,看見好幾輛機車以極快的速度朝我的方向衝了過來。
我本能地朝路邊避讓,一輛機車卻直直的朝我衝了過來,我嚇得又朝路中心退了幾步。幾輛機車很快在我的邊圍了個圈。
車子停了下來,引擎還在。
出租車從我眼前開過時,司機看了我好幾眼,最後一聲不吭的開走了。
我驚疑不定地盯著周圍這幾個在機車上的男人,他們一個個穿著馬丁靴,皮夾克,手指上帶著很的戒指,一看就不是善類。
我強自鎮定地問,“你們乾什麼?”
我的問話引來一陣笑聲,他們隻是笑,冇人回答我的問題。
我環視了一圈,目很快鎖定其中一個戴著墨鏡的男子。
他穿著馬丁靴的一隻腳撐在地上,兩手環,歪著腦袋,過墨鏡的鏡片看著我,角淡淡地勾著。
我覺得他很眼,但墨鏡遮住了他大半張臉,我認不出來。
我的手悄悄地探進兜裡,剛把手機出來。一團雪突然朝我砸了過來,我的手機也掉了。
我正手去撿,卻被另一隻更快的手給撿走了。我手去奪,他卻一下子把我的手機舉得好高,我本無法拿到。
我看著拿著我手機的這個男人。
實在是太眼了!
“你到底是誰?”我一瞬不瞬地盯著他問。
他輕聲一笑,抬手摘下了墨鏡。
我當即震住!
猜你喜歡
-
完結5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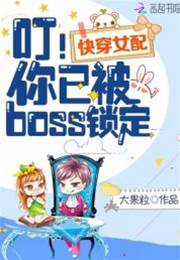
快穿女配之你已被boss鎖定
阮綿綿隻想安安分分地做個女配。 她不想逆襲,也不想搶戲,她甘願做一片綠葉,襯托男女主之間的純純愛情! 可是為什麼,總有個男人來攪局?! 阮綿綿瑟瑟發抖:求求你,彆再纏著我了,我隻想做個普通的女配。 男人步步逼近:你在彆人的世界裡是女配,可在我的世界裡,卻是唯一的女主角。 …… (輕鬆可愛的小甜文,1v1,男主都是同一個人)
103萬字7.83 14294 -
完結231 章

離婚夜,植物人老公扒光我馬甲
成為植物人之前,陸時韞覺得桑眠不僅一無是處,還是個逼走他白月光的惡女人。 成為植物人之後,他發現桑眠不僅樣樣全能,桃花更是一朵更比一朵紅。 替嫁兩年,桑眠好不容易拿到離婚協議,老公卻在這個時候出事變成植物人,坐實她掃把星傳言。 卻不知,從此之後,她的身後多了一隻植物人的靈魂,走哪跟哪。 對此她頗為無奈,丟下一句話: “我幫你甦醒,你醒後立馬和我離婚。” 陸時韞二話不說答應。 誰知,當他甦醒之後,他卻揪著她的衣角,委屈巴巴道: “老婆,我們不離婚好不好?”
56.4萬字8 19064 -
完結81 章

仲夏呢喃
霖城一中的年級第一兼校草,裴忱,膚白眸冷,內斂寡言,家境貧困,除了學習再無事物能入他的眼。和他家世天差地別的梁梔意,是來自名門望族的天之驕女,烏發紅唇,明豔嬌縱,剛到學校就對他展開熱烈追求。然而男生不為所動,冷淡如冰,大家私底下都說裴忱有骨氣,任憑她如何倒追都沒轍。梁梔意聞言,手掌托著下巴,眉眼彎彎:“他隻會喜歡我。”-梁梔意身邊突然出現一個富家男生,學校裏有許多傳聞,說他倆是天作之合。某晚,梁梔意和裴忱走在無人的巷,少女勾住男生衣角,笑意狡黠:“今天賀鳴和我告白了,你要是不喜歡我,我就和他在一起咯。” 男生下顎緊繃,眉眼低垂,不發一言。女孩以為他如往常般沒反應,剛要轉身,手腕就被握住,唇角落下極輕一吻。裴忱看著她,黑眸熾烈,聲音隱忍而克製:“你能不能別答應他?”-後來,裴忱成為身價過億的金融新貴,他給了梁梔意一場極其浪漫隆重的婚禮。婚後她偶然翻到他高中時寫的日記,上麵字跡模糊:“如果我家境優渥,吻她的時候一定會肆無忌憚,撬開齒關,深陷其中。”·曾經表現的冷漠不是因為不心動,而是因為你高高在上,我卑劣低微。 【恃美而驕的千金大小姐】×【清冷寡言的內斂窮學生】
40.2萬字8.18 48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