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妃傾城:王爺,請下榻》 第三百六十五章 父女聯手
顧淮的這個理由很站不住腳,如果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疼兒的父親說不得這個理由還能相信。可是他是安國公,而且是位高權重,武學也是天下第一的安國公。顧淮看著池君墨那一臉不相信的模樣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不過也毫不影響這個男人在他心中的印象。糟了,什麼腌臜玩意兒。
顧淮揚起了眉,不得不說人揚眉的樣子都是很好看的。簫卿是帶著獨有的魅而的父親卻是清冷之中帶著不怒自威的威嚴。難怪說顧家一定是一個狐貍窩,不然怎麼有這麼多風各異的人,只不過這些人都是天生帶毒的。
池君墨被這一眼神嚇得打了一個激靈,覺渾被冷水澆過一遍一樣。
簫卿看著池君墨那慫樣,抿了抿忍住了笑容。池君墨還真不是一個好命的,或者說他的幸運說不定就在那一次被原救起的時候全用了。這些年一連串的事下來,池君墨還真是被拖累慘了。
簫卿將早餐用必才開口了:“爹,今日中午你還會下廚麼?”
“現在深秋了,該吃點好點東西,中午的時候選幾樣你最的菜怎麼樣,我特地帶了食材過來。”顧淮聽到兒的聲音笑著說,那模樣分明是一個溺兒的父親。池君墨看著有一些啞然了,那種神在他記憶之中只有先皇對池君塵做過。池君墨苦笑一聲,這世間的父親還真是各種模樣的都有,或許也只不過是對一人慈罷了。
池君墨拱了拱手說:“就算安國公思心切也該是安著規矩來,不然引起了兩國之間的誤會就不好了。不若小王今日就給安國公遞一份折子?這樣的大事皇兄怎麼都該知道的。”
Advertisement
前一句話是詢問,后一句話就是肯定了,雖說兩兄弟在窩里斗得厲害,可是面對敵人的時候還是要一致對外的。
顧淮聽著池君墨的話懶洋洋地笑了,纖長的手了自家兒的腦袋之后開口了:“是麼,沒想到本座這麼重視啊,三年前你們可不是這樣的。”
聽到顧淮提到了三年前,池君墨心里口就堵得慌,想到三年前簫卿墜崖的形就害怕了,服毒,刺穿心臟,沒有人能夠活下去,可是為什麼簫卿會用一假尸來糊弄眾人?
池君墨看著顧淮咬了咬牙問出了心中最想要問的事:“既然安國公提到了三年前,那麼我想問安國公,三年前你們是不是帶走了一尸。”
顧淮聽到池君墨的問話愣了,隨即一笑:“沒錯,本座確實是帶走了城郡君的尸,這也是城郡君本人的要求,葬在異鄉,至可以免打擾不是麼?”
聽到顧淮這樣說,池君墨聲音有一些激:“那麼兒到底葬在哪里?能不能將運回來……”
聽到池君墨這話,父兩人同時都揚起了眉,就沖這一模一樣的反應,沒有人能夠懷疑這兩人不是父。顧淮看了一眼池君墨一臉的嫌棄:“故人之自當妥善置,為了不被你們打擾,自然是葬在了蠱圣教的地之中。戰王爺,本座勸你一句能不要去打擾就不要去打擾,人都死了裝深哄鬼呢?”
簫卿聽到顧淮這樣說撲哧一聲笑了,池君墨臉上的尷尬是擋不住了,但是卻還是說了話:“至讓我與道一個歉吧。”
顧淮聽著這話更無奈了,道歉,道什麼歉?自家兒好好的,要的就是你生不如死,難道一句道歉就能讓你心安理得了不?再者蠱圣教地之中確實是有簫卿的墳墓,不過那是一座空墳,等著簫卿百年之后葬其中的,這種墳墓教主,圣,五使都有,要騙過池君墨很簡單。可是都說了是地,怎麼可能讓池君墨這一個閑人進去。
池君墨看著顧淮那一臉戲謔的面容,便知道此事絕無可能,此時郝叔收走了碗碟,簫卿便站了起來:“王爺,您剛才不是還在說要遞折子與梁帝陛下麼,怎麼這會兒就嚷著要出北梁東晉去尋那城郡君的尸了?”
池君墨看著簫卿心頭有一恨意直接躥了起來:“郡主,小王多次詢問你與城的關系,可是你就是避而不談,誰知你們已經將城下葬了。郡主,小王斗膽問上一句,戲耍小王很好玩麼?”
顧淮見池君墨不敢對他說重話,反而責問簫卿也不高興起來,合著柿子撿的不?簫卿見狀反而到了顧淮的后將手搭在了顧淮的肩膀上示意他稍安勿躁。只聽簫卿輕輕一笑:“戰王爺一直以來就只問本郡與城的關系,可是沒有問過城的事。這答非所問,本郡可是做不出來的。”
池君墨被簫卿那一聲輕飄飄的話語給堵得說不出話來了,簫卿的角一勾繼續說:“戰王爺還有和話可說,言歸正傳,戰王爺何時遞折子與梁帝陛下?總歸我父親并非是敵國細可是也怕旁人將這莫名其妙帽子給我父親戴上,不若現在請戰王爺做個引薦如何?”
簫卿的話給池君墨敲醒了警鐘,安國公的分量可是比簫卿要重上許多,如果池君煜劍走偏鋒將安國公扣在皇宮之中?池君墨不敢想了,如果他沒有記錯的話,池君煜邊的木老可是曾經重傷安國公的存在。池君墨這樣想著連忙笑道:“不過是普通的父相見,沒必要驚皇兄。皇兄可不是小王這樣的閑人,民生大事多著呢。”
池君墨的言語和之前來了一個大轉彎,簫卿一眼便看出來了池君墨的顧慮。畢竟池君煜曾經讓木老扣下過,要是池君煜來上一個故技重施,池君墨可沒有把握了,扣下安國公責令東晉出兵亦或者是修改協定都是極為簡單的事。只可惜木老已經了蠱蟲的盤中餐了,連帶著力都了他們父倆的腹中食了。
簫卿用手指繞了繞自己的頭發,顧淮一見這個作就知道自家兒又要什麼鬼主意了,只要是能整治到了眼前這個腌臜玩意顧淮是一萬個愿意配合的。
只見簫卿將手指放了下來輕笑著說:“沒有想到戰王爺也是一個哥哥的存在,本郡還以為你們兄弟倆恨不得和烏眼一樣呢。”
簫卿的諷刺,池君墨都已經習慣了也不反駁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這事總要分輕重緩急的。”
顧淮見池君墨不會將此時張便笑著說:“其實戰王爺也不必多費筆墨,寫一份折子與梁帝陛下,因為本座下午就要走了。”
池君墨聽到顧淮要走的消息立馬抬起了頭,其實他心中是懷疑顧淮前來的目的的,顧淮的份地位擺在那兒,他的一舉一絕對不會是無意之舉。可是池君墨一直都被這父兩人牽著鼻子走沒有找到關鍵的突破點,現在這兩父竟然直接開口說要走了?池君墨只覺得自己就像是這兩父眼中的愚人任由他們愚弄。
簫卿見池君墨一臉驚訝但是眸子之中卻著怒火的模樣只覺得可笑,簫卿笑著說:“看來戰王爺對我父親很興趣,不若等到午膳的時候你們好好聊聊?”
簫卿的建議讓池君墨的憤怒平息了一些,他笑著應了下來,推說現在有事理便離開了大廳只說中午一定準時赴宴。
簫卿看著池君墨的背影消失在大廳之中才勾了勾說:“戰王爺或許還在想著我們父二人是不是拿它當傻子耍呢?”
顧淮笑著刮了刮簫卿的鼻子:“說吧,你要做什麼?”
猜你喜歡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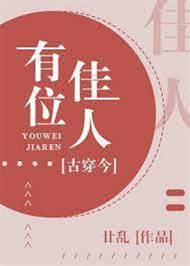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241 -
完結1550 章

穿成惡婆婆后,我讓全村心慌慌
二十歲的林九娘一覺醒來,成為了安樂村三十五歲的農婦五個兒女跪著求她去‘寄死窯’等死,兩兒媳婦懷著娃。母胎單身二十年的她,一夜之間躍身成為婆婆奶奶級的人物調教孩子、斗極品、虐渣已經夠困難了,可偏偏天災人禍不斷。慶幸的是,她空間有良田三千畝,還愁小日子過不好嗎?不過她都老大不小了,他們個個都盯著自己做啥?
302.2萬字8.33 176397 -
完結118 章
穿成沖喜王妃后我成了病嬌王爺心尖寵
從小寄人籬下的傻女,被害死在鄉下后依然難逃被賣的命運。 美眸初綻,傭兵女王穿越重生,夢魘散去后必將報仇雪恥。 沒錢??活死人肉白骨,值多少錢? 亂世?空間在手,天下我有! 蒙塵明珠閃耀光華之時,各路人馬紛紛上門,偽前任:你既曾入我門,就是我的人。 偽前任他叔:你敢棄我而去?! 「傻女」 冷笑:緣已盡,莫糾纏。 掃清障礙奔小康,我的地盤我做主。 某天,一個戴著銀面具?神秘人邪氣一笑:「聽說你到處跟人說,你想當寡婦?」
35.7萬字8 126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