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嫡女狂妃:太子別惹我》 第五百五十八章俗人,世人無恥
沐于婷東陵玨那一笑給笑得當即愣住,后靠著的石壁上冰冷的氣息好似穿過的直直刺進骨頭里,整個人都如同凍在寒冰里一般不能彈。
東陵玨便這般靜默無言,只角微微嗤著笑地睨著沐于婷,見愈發驚恐的面容無于衷,終于,沐于婷在這眼神的強之下,一時間想起從前東陵玨同沐纖離對自己做過的種種,又想起自己兒子棄自己離去時候是那樣的絕。
那深宮中的人死時候的眼神是那樣的可怕,還有冷宮時候的那群瘋人,一個個蓬頭垢面,見到的時候,那目恨不得吃了,心生膽。
不知為何,沐于婷在這時候想起了這些事來,越想越怕,越想越怕,漸漸將自己的子抱得更,終于,在片刻之后,腦海中的那跟弦,徹底地崩了。
“不……別過來,你們別過來!”不知道看到了什麼,沐于婷忽然手在空中舞,東陵玨便就這般靜靜地瞧著那,看著自己發瘋,大喊著,“不是我,不是我!是你們該死,你們要搶本宮的后位,是你們該死!你們該死。”
沐于婷驚聲尖著,那聲音回在這空曠的牢房之中,刺得東陵玨蹙眉了耳朵,邊兒上的影衛見著,便提著那桶熱水走到了沐于婷旁,徑直將水從頭上澆了下去。
“啊——!我沒有推你,你自己掉下去的,你自己掉下去的。”那熱水放了一會兒倒是沒一開始這麼燙了,是以這都已經淋在了沐于婷的頭上,還是卻還能夠大喊出聲,“藍心蓮!你該死,你該死,啊——”
沐于婷正抱頭大喊著,忽然驚一聲撲到了一旁,左手的小臂上有一道新鮮的紅痕,而東陵玨的手邊,便擱著一只長鞭,那鞭子上帶著細細的倒刺,有那麼一小段,還等著新鮮的跡。
Advertisement
沐于婷蜷在地上,抱著自己那只傷的手臂瑟瑟發抖,漉漉的頭發將整張臉都蓋了起來看不清面容,并不再敢言語。
東陵玨靠著椅背,兩手的指尖輕輕搭在一起,漫不經心地看著那頭一如死狗模樣的沐于婷,淡淡開了口,道:“你便是真瘋了,也沒資格提的名字。”
藍心蓮,東陵國蓮貴妃,如今追封為皇后,乃東陵玨生母。
東陵玨揮手旁的影衛將方才屋中點著的煙給掐了,看著那頭慢慢爬起來,瞧模樣清醒許多的沐于婷,問道:“城中的那些流言,是誰你放出去的。”
“呵。”沐于婷冷笑了一聲,而后道:“你怎知那些流言是本……”
險些口而出的自稱到底是東陵玨方才那一眼看得猶豫了片刻,而后沐于婷這才接著道:“怎知是我放出去的,沐纖離就該,什麼安遠將軍,最后還不是落得個藏深院的下場啊——!”
沐于婷話還未完,東陵玨那邊的鞭子便直直了過來,正正在的臉上,那鞭子上的倒刺撕拉著的面皮,力道之大沐于婷面上的都翻了出來。
沐于婷不敢自己的臉,只敢虛虛地捂著,趴在一旁小心地看著那邊的東陵玨,咬著牙不敢出聲,生怕那閻羅一個不樂意便又是一鞭子。
便這時,東陵玨又淡淡地開了口,道:“離兒的名字也不是你能說的,離兒喜歡做什麼便做什麼,還不到你來評頭論足。”
東陵玨明晃晃的維護之意聽在沐于婷的耳中顯得那麼刺耳,想當初,方宮之時,皇上又如何不待溫,后來,卻因為那個人,藍心蓮,皇上便再沒來過的坤寧宮。
一想到這兒,沐于婷一下忘了這面上的火辣辣是如何而來,眼中滿是恨意地瞪向東陵玨,惡聲惡氣地說道:“我說的難道不對嗎?”
“沐纖離從前便在外頭拋頭面,日在男人中廝混啊——!”沐于婷又被一鞭子翻在地,上那多了的一條痕也攔不住如今逐漸瘋魔的模樣,只見又爬起來大吼道:“子干不干凈都不知道!還你個瞎了眼的娶了回去啊——!”
又挨了一鞭子的沐于婷非但不知停歇,還大笑著接著喊,“哈哈哈!如今倒想要安分了!他早干嘛去了!”
“沐纖離!你該!你該死!你早便該去死了!”那鞭子一道一道地在沐于婷上也攔不住的,甚至越喊越大聲,“當初就不該你被生下來,和你那個娘一樣,都是個狐子!”
東陵玨見此皺了皺眉頭,便也放下了手頭的鞭子,目極其冷地看著地上撒潑打滾的瘋婦,低聲道:“方才那煙點的倒是重了些,罷了,將舌頭拔了。”
一旁影衛領命向著沐于婷走去,東陵玨也轉要往外出去,便這時,后沐于婷又喊出的一句話,他駐足。
“哈哈哈,沐纖離,你大限要到了!下地獄去吧哈哈哈!”沐于婷一下被影衛抓住了手腳,又住了下顎,眼見著就要沒了舌頭,東陵玨卻走了過來,冷冷地盯著,低聲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沐于婷看著東陵玨走進,目略有些渙散,整個人也開始顯得瘋癲,口中好似很高興地念著,“你要死了,你就要死了,沐纖離你活該,活該去死!”
東陵玨眉頭蹙,又想起沐纖離如今的狀況,便在這兒一刻也待不下去,轉便走,同時對后吩咐道:“不管是瘋沒瘋,都把這事兒給本宮問清楚了。”
話畢,東陵玨便從這出牢房走了出去,卻不過才出了牢房門,便忽地察覺邊兒上好似站著什麼人,他眼神冷冷地看過去,便見那頭牢房的石墻邊上,正站著沐纖離,他不由得一愣。
沐纖離見他看來,便微微笑了笑,道:“這兩日,你都沒同我一齊歇息,我便有些想了,就來尋一尋你。”
東陵玨看著沐纖離沒敢出聲,方才沐于婷的那些喊聲也不知道聽去了多。
而沐纖離看著東陵玨立在那頭好似傻了一般地一不,便上前拉了拉他的手,笑著說道:“走罷,早些回去歇著,我瞧你這兩日神也不大好。”
“嗯。”東陵玨小聲地應了聲,而后就由著將自己帶出了水牢,看著眼前人的背影,一時間有些不大確定如今的想法。
水牢這地知道,下來時候影衛也不會攔著,可影衛沒有知會他便說明是吩咐的……說好要護一世安穩,不想還是聽到了這些污言穢語。
東陵玨想著,不由得往前快走了兩步,將沐纖離攬在懷里,見沐纖離看來,便沖溫一笑,而后便一齊回房去了。
次日,街邊的一餛飩攤子。
這位于鬧市區的餛飩攤子,是金文常來的早食攤子,每每日頭好的時候他便會來這兒吃上一碗熱騰騰的餛飩,這一天就都舒心了,而這餛飩攤主也與金文是識,曉得他吃餛飩時不放蔥,便會多給他來兩勺油花。
今兒的天正好好,眼見著漸漸了春,微風拂面,涼爽中好似還帶了一迎春的清香,金文這跟攤主要了一碗餛飩,在自己的座上呼哧呼哧吃得正香,忽旁桌上人的閑談引了注意。
若是些什麼尋常的家長里短他倒也不會去多管,只這其間總有那麼幾個字眼,每每聽到就他的耳朵都能豎起來,也不是旁的什麼東西,就是無非是同沐纖離有關的那麼些個稱謂。
以往每每聽到他家頭兒的那些個稱呼的時候,哪一個不是伴隨著各夸獎,可今兒,倒是他聽到了個別致的。
旁桌上的人也不知從哪兒就聊到了安遠將軍沐纖離,這會兒便有人道: “哦?不是剛生完孩子麼。”
這話說完便又有人道:“我家婆娘都生了幾個了,哪個不是一生完就能下地干活兒的。”
“人那是太子妃,可金貴著呢,你家那糙婆娘有得比麼。”話畢,這桌上的人還紛紛笑了起來,便連方才說自己妻的那個人也不例外。
金文聽著這些話,雖心中略有不快,卻到底不是自家事,便也沒去管他,不想旁桌上的這群人話倒是越說越寬敞了。
“你看看這太子妃,從前不還有個稱號什麼,安遠將軍的麼。”一人說著,邊兒上一人聽了這話還故意挪揄道:“還真別說,你今兒要不提醒,我都忘了還是個將軍。”
聽到這兒,金文的眉頭地皺了起來,連手中的勺兒也不自覺地停了下來,直到后一人開口,這才他又舀了一勺餛飩。
“你可別胡說,安遠將軍的名號可不是白來的。”一人說道,而后便又有另一人反駁道:“可那些輝煌功績是嫁人生子以前的事兒了,這人啊,一旦嫁了人,還不得事事以夫為天,那兒還能整日拋頭面的,丟人現眼。”
幾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地高聲談論著,也不知誰給的底氣他們大白天還在外頭議論皇親國戚,那頭人一個勁地說個不停,無非是些人就該是待家里頭生孩子的,沒事兒去當什麼將軍,狗拿耗子多管閑事。
后邊的話更是越發地不堪耳,聽得這邊坐著的金文怒火騰地一下燒了起來,一想自家老大當初拼了命的在陣前廝殺才換來了這些狗東西的安寧,不想如今竟還要被這些狗東西在背后嚼舌。
金文心中氣極,便一下站起來,連后的長凳都給撞翻了,一個邁步就到了邊兒上那桌人的前。
猜你喜歡
-
完結1258 章
天尊溺寵:腹黑萌妃太囂張
她是二十一世紀特工界首席特工,一朝穿越成為火鳳國蘇族嫡女……傳聞,她廢物膽小如鼠!卻將一國太子踹廢,並且耍的團團轉……傳聞,她是整個火鳳國最醜之人!當麵紗掉下來時,又醉了多少美男心?麵對追求的桃花她正沉醉其中,某天尊卻隨手掐死丟進河裡……麵對強勢的男人,她氣呼呼的罵道:“你是強盜啊!”某天尊瞇起危險的眸子,強勢地圈她入懷道:“你知道強盜最喜歡乾什麼嗎?”
226.6萬字8.18 77800 -
完結1334 章
重生九零:肥妻,要翻身
葉姚重生回到1990年,跟大院男神訂婚的時候。這個時候的她,還是人人厭惡的大胖子,受盡欺淩。所有人都在唱衰(破壞)這段戀情。葉姚笑一笑,減肥,發家,狂虐人渣,漸漸變美成了一枝花。葉姚:「他們都說我配不上你,離婚吧。」厲鋮強勢表白:「想的美。婦唱夫隨,你在哪兒,我就在哪兒!」
154.2萬字8.18 145318 -
完結3036 章
龍魔血帝
生來隱疾困前程,蓋因魔龍盤神魂。龍血澆灌神魔體,孤單逆亂破乾坤。 原本想要平凡度過一生的少年,卻不斷被捲入種種漩渦之中,從此他便改變人生的軌道。 什麼是道?吾之言行即使道。什麼是仁?順我心意即是仁。不尊道不順仁者,雖遠必誅。
831.4萬字7.58 37944 -
完結521 章

帶著物資穿到年代搞事業
出生在富裕家庭從小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文舒念,從冇想過自己有天會得到傳說中的空間。 本以為是末世要來了,文舒念各種囤積物資,誰想到自己穿越了,還穿到了一個吃不飽穿不暖買啥都要票的年代當知青。 在大家都還在為每天的溫飽而努力的時候,文舒念默默地賣物資搞錢讀書參加工作,一路上也結識了許多好友,還有那個默默陪伴在自己身邊的男人。 本文冇有極品、冇有極品、冇有極品,重要的事說三遍,因為本人真的很討厭極品,所以這是一本走溫馨路線發家致富的文。 最後:本文純屬虛構。
86.7萬字8 33679 -
完結16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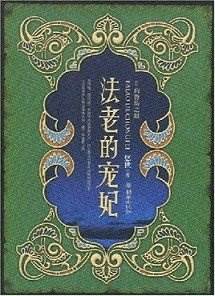
法老的寵妃
埃及的眾神啊,請保護我的靈魂,讓我能夠飛渡到遙遠的來世,再次把我帶到她的身旁。 就算到了來世,就算已經過了好幾個世紀,我和她,以生命約定,再相會亦不忘卻往生…… 艾薇原本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紀英國侯爵的女兒,卻因為一只哥哥所送的黃金鐲,意外地穿越時空來到了三千年前的古埃及,而那只黃金鐲就此消失無蹤。艾薇想,既然來到了埃及就該有個埃及的名字,便調皮地借用了古埃及著名皇后的名字——「奈菲爾塔利」。 驚奇的事情一樁接著一樁,來到了古埃及的艾薇,竟還遇上了當時的攝政王子——拉美西斯……甚至他竟想要娶她當妃子……她竟然就這麼成為了真正的「奈菲爾塔利」!? 歷史似乎漸漸偏離了他原本的軌道,正往未知的方向前進……
71.2萬字8 57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