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妃,你的鞋掉了》 第一百八十三章 這帽子戴不得
祠堂神像的事不知結局,只是晚膳時飯桌似乎不再那麼擁,在人群中逡巡一圈,沒有看到楚妃影。
其他側妃看的眼神微變,驚疑之下藏著探究與打量。
起初們只當是一個貴客,可隨祭祀在前,神像在后,們逐漸發現王爺比想象中更加溺。
無條件的信任,以及不計后果的偏袒,不像是王爺的一貫作風。
這次晚膳,側妃們沒有再爭相邀乾陵悅,反而借故在飯桌邊打轉,誰都不肯先坐下去。
項天義面如常地落座,香妃跟著坐在他邊,分辨不出喜怒。
乾陵悅看了一圈,大家似乎都在等,沒得選的人懵懵地在項天義另一側坐下,謹慎小心,收斂格,屏住呼吸。
“陵悅怎麼如此張?”耳邊驟然想起他的關懷,嚇了一跳,坐直脊背,下意識拉開距離。
“沒有張,只是有點不習慣。”尬笑著回答。
“還是不習慣嗎?看來太勉強你了。”無視旁人,項天義點點頭,苦惱,“還想著陵悅或許能夠習慣,日后常來。”
別了吧。抿著禮貌的笑,微咳一聲,低聲音提醒他,“您的側妃還未座。”
似乎被提醒才注意到,他抬頭時溫斂跡,“都坐下吧。”
側妃們這才座,往日還有約約的談聲,今日卻靜若寒蟬,木筷偶爾與瓷盤發出的撞都足以驚得在座僵。
一貫引導氛圍的香妃格外沉默,全程專注用膳,反而是項天義時不時與乾陵悅搭話,還會溫聲為介紹桌上的新菜式。
這哪里是把當貴客,本是把當親祖宗。
“南王,我用完了。”備煎熬地用完晚膳,果斷放下碗筷,聲音清脆,目掃視后停在項天義上,行禮起。
Advertisement
“嗯,我陪你轉轉。”他跟著也放下,,不顧其他妃子的異,亦步亦趨地跟在后。
乾陵悅走了幾步,實在不解,回頭著他,“二哥,你是不是與香妃起了爭執?”
往日他對充其量是比較照顧,絕不會像現在甚至有越矩之嫌。
他起先沒有說話,又走出兩步了才娓娓道來,“近日對我頗為冷淡。”
所以?皺眉等著他的下文。
“所以我不得已……”
“利用我來氣,是嗎?”乾陵悅自然接話,無語搖頭。
“……不是利用,”他還想解釋,說到一半發現無法自圓其說,只能垂首承認,“我太不會理這些事。”
抿片刻,“方便和我說說理由嗎?冷淡的理由。”
邊的人頓了頓,走到一邊就近坐在石凳上,“說來有些難以啟齒,覺得我不夠關心。”
“香妃是你的結發,也是最了解你的人,怎麼會無端說這種話,難道最近有哪里不同嗎?”乾陵悅作為一個局外人也不知從何著手,試探地發問。
項天義心思極放在上,更無從揣度人的想法,被問得呆了片刻。
打消從他那兒得到答案的想法,清清嗓子,主發問,“你往日都是在那兒留宿嗎?”
“是。”他面上的不解很真實,似乎不知如此詢問的緣由。
“這幾日也在那兒睡?”繼續追問。
“這幾日政務繁忙,便在書房睡了。”
好的,找到一個點。
乾陵悅腦袋飛速轉,在言劇里搜索相似的劇,充分發揮著平日里閑來無事的知識累積,“你和還有什麼固定的習慣嗎?”
項天義斂眉思考片刻,“每日清晨會親自為我換,一起用早膳,送我出府。”
哦,還恩的,想想和項天禮,什麼儀式都沒有,難怪南王妃都生了一對龍胎了,安王府里還什麼靜都沒有。
“不用太擔心,你按照之前的習慣對待香妃就好了。”拍拍他的肩,雖然他還算是自己的男神,卻已經不是讓小鹿撞的那個男神了。
眼下只是真心實意地想解決他的問題。
“這樣就可以了嗎?”他不太相信地問。
“嗯。”乾陵悅篤定點頭。
人嘛,一個人在家總會想七想八,沒有寄托就會開始盤男人的人際關系,或者事的各種細節。
小事放大,大事推演,最后便了“他不我”的罪證。
此刻出現任何一個不曾出現的異,就會讓如臨大敵,甚至怒火泄。
顯然乾陵悅就是那個炮灰。
好難。
思及此,忽然凝神,轉頭問項天義,“你邀我過來小住,也是這個原因吧。”
“……是。”
完全在意料之中呢。乾陵悅疲倦地閉閉眼,不過這樣也好,至讓的心輕松許多,權當給自己放三天的假,做一回人也不錯。
按照的建議,隔日項天義便與香妃并肩走在一起,與肩而過時甚至還沖笑了笑,乾陵悅寵若驚。
只要香妃不主找的事,就謝天謝地了。
又過半日,午膳各自用膳,香妃被額外召到項天義寢殿里,想來是一頓溫馨的午餐。
不知道說項天義領悟能力強,學會舉一反三,還是指點得一針見,兩人的關系飛速升溫,連其他房的丫鬟都看出項天義對香妃的寵,紛紛頭接耳。
雖然投接耳的容乾陵悅并不怎麼喜歡,諸如——
“我就知道王爺最疼的還是香妃你,那個什麼安王妃簡直太自大了,竟然還想挑撥王爺王妃的關系。”
“是啊,哼,這下要好看。”
對不起,我本來就很好看。乾陵悅腹誹著經過,目不斜視。
其實并不在意丫鬟們的看法,比較在意的是這些流言傳播范圍,若是傳出了南王府,就意味著京城里各個角落都會充斥著這樣那樣的言論。
這不是在打項天禮的臉嗎。
才被教訓過的人可不想老虎屁,暗自吩咐綠竹出去轉一圈,打聽打聽。
借著出去購置品的理由,綠竹隨著南王府里的采辦小廝一同出門,乾陵悅則待在房間里,寫寫方子,讀讀書。
正冒出新點子打算記下,敲門聲便響起,微怔,這個點綠竹才剛出去,不會這麼快。
難道又是哪個想搞事的妃子?
“進。”高聲回應,門應聲而開。
是香妃。
手里提著一個糕點盒,后面一個人都沒有,看樣子是自己來的。
“香妃,好久不見。”兩人只是路過會偶爾對視,其他多余的接并沒有。
“的確好久不見。”香妃聲音一如既往地溫,聽得人心俱暢,但乾陵悅沒有心思欣賞,畢竟這是南王府,不是安王府。
“找我有事嗎?”趕說完趕走,可招待不起。
香妃訕笑著將糕點盒放在桌面上,發問,“不請我坐下嗎?”
“您坐。”也許是乾陵悅屬太直,對彎彎繞繞的孩子實在看不上眼,避之不及。
就算再溫,對而言也是笑里藏刀,不定什麼時候就能背后捅一刀。
也許是看出不怎麼歡迎自己,香妃也有幾分尷尬,尷尬后是無奈與悵然,“我與陵悅之間,誤會太多了。”
誤會倒談不上,非要說的話是對彼此的偏見罷了。
也是,但凡至上的人都看不慣自己的人對其他人溫備至,哪怕是弟媳。
“香妃,既然你我之間嫌隙不可逾越,不如就此忘。”乾陵悅開門見山,這嫌隙一時是填不滿的,也不指一次談話就能改變香妃對的看法。
偏見總是深固。
“此話怎講?”沒料到如此直接,打得香妃措手不及。
“日后我會與二哥保持距離,你也不用擔心我對他有非分之想,他是我二哥,僅此而已。”盡量把話說得通俗易懂,盯著的表,觀察著的反應。
“陵悅這是什麼話,我不曾懷疑過……”
“香妃,你我都是人,你的想法,我大概也能知道一些,如果你真的沒有懷疑,自然更好,若是有,也請您盡早打消這個念頭。”打斷的場面話,直視著,“這樣的帽子,我戴不起。”
香妃不再作聲,盯著桌面,半晌沒說出話來。
該說的都說了,乾陵悅深吸一口氣,才抬手為沏了杯茶,“現在,香妃來意為何?”
一時沒能接住。
來能是為何?不過是試探對項天義的。
可說得清清楚楚,干干凈凈,任誰都挑不出錯來。
還有什麼好問的。
“后廚新做了一些糕點,口味不錯,所以我拿來給你嘗嘗,這可是西涼的廚子,別的地方未必吃得到。”香妃表一換,一派和氣。
乾陵悅眉尾微挑,配合地,“這里竟然會有西涼的廚子。”
說著手拿了一塊放在里,味道確實還不錯,甜而不膩,回味悠長。
“是琳妃帶過來的,托的福,我們也嘗到許多新鮮。”絕口不提方才短暫的鋒,香妃面溫,打開第二層,將另一種推到的面前,介紹著用料及手法。
看上去其樂融融,可兩人眼底都各藏著心思。
猜你喜歡
-
完結1566 章

來人開棺,王妃說本王還有救
啥? 身為王牌軍醫的我穿越了, 但是要馬上跟著王爺一起下葬? 還封棺兩次? 你們咋不上天呢! 司夜雲掀開棺材板,拳拳到肉乾翻反派們。 躺在棺材板裡的軒轅靖敲敲棺材蓋:開棺,王妃說本王還有救!
282.6萬字8.18 227621 -
連載1841 章

重生後我嫁了未婚夫的皇叔
前世,她是貴門嫡女,為了他鋪平道路成為太子,卻慘遭背叛,冠上謀逆之名,滿門無一倖免。一朝重生回十七歲,鬼手神醫,天生靈體,明明是罵名滿天下的醜女,卻一朝轉變,萬人驚。未婚夫後悔癡纏?她直接嫁給未婚夫權勢滔天的皇叔,讓他高攀不起!冇想到這聲名赫赫冷血鐵麵的皇叔竟然是個寵妻狂魔?“我夫人醫術卓絕。”“我夫人廚藝精湛。”“我夫人貌比天仙。”從皇城第一醜女到風靡天下的偶像,皇叔直接捧上天!
331.1萬字8 71759 -
完結332 章

首輔寵妻錄
侯府嫡女沈沅生得芙蓉面,凝脂肌,是揚州府的第一美人。她與康平伯陸諶定下婚約後,便做了個夢。 夢中她被夫君冷落,只因陸諶娶她的緣由是她同她庶妹容貌肖似,待失蹤的庶妹歸來後,沈沅很快便悽慘離世。 而陸諶的五叔——權傾朝野,鐵腕狠辣的當朝首輔,兼鎮國公陸之昀。每月卻會獨自來她墳前,靜默陪伴。 彼時沈沅已故多年。 卻沒成想,陸之昀一直未娶,最後親登侯府,娶了她的靈牌。 重生後,沈沅不願重蹈覆轍,便將目標瞄準了這位冷肅權臣。 韶園宴上,年過而立的男人成熟英俊,身着緋袍公服,佩革帶樑冠,氣度鎮重威嚴。 待他即從她身旁而過時,沈沅故意將手中軟帕落地,想借此靠近試探。 陸之昀不近女色,平生最厭惡脂粉味,衆人都在靜看沈沅的笑話。誰料,一貫冷心冷面的首輔竟幫沈沅拾起了帕子。 男人神情淡漠,只低聲道:“拿好。” 無人知曉,他惦念了這個美人整整兩世。
53.2萬字8.33 67799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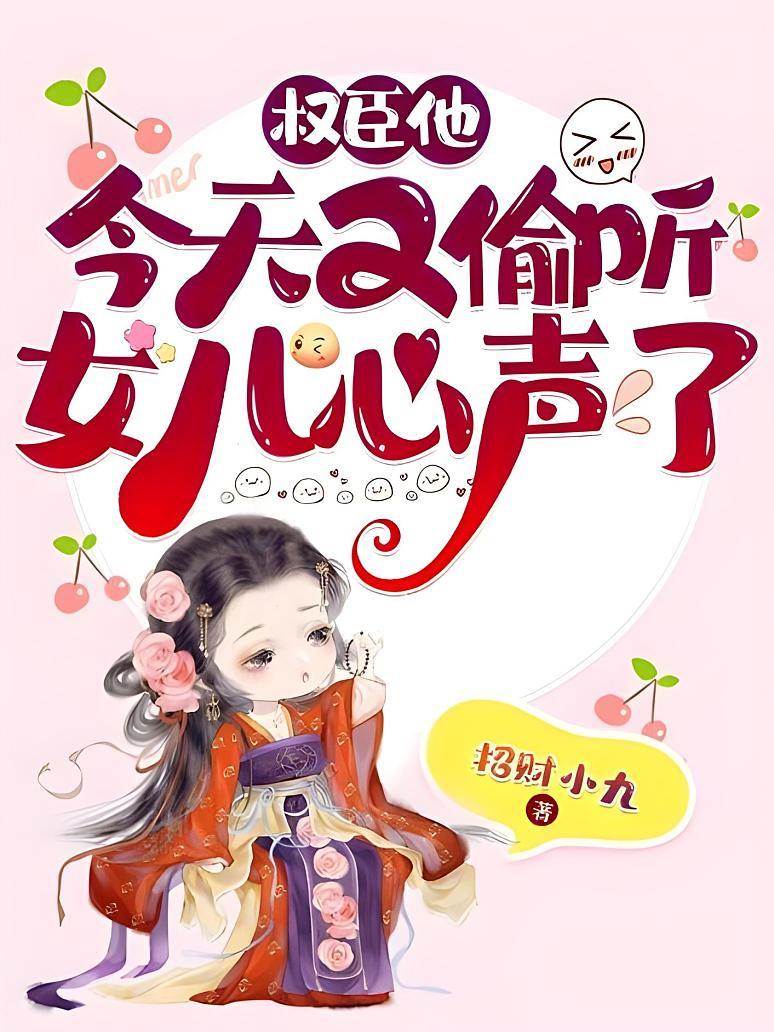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18 1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