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妃重生:盛寵太子爺》 第252章 花田奇影
第二日一大早,許錦言就坐上了馬車,車軲轆一圈一圈的打著轉兒,在土地上出一行長長的印記,一路向北蜿蜒而去。
北明京城四環山,得天獨厚的易守難攻之地形,尤其以北面的山最高也最險。而孫白娘邀請許錦言見面的地點便是定在了那山峰的北麓。
北麓多林,忍冬駕著馬車過去一路上都是遮天蔽日的林,那些茂而展的枝葉不斷的刮蹭著馬車,發出「吱嘎吱嘎」的詭異聲響。
雖然已到了春深之時,但是如此茂的枝葉還是讓人有些意想不到。
「小姐,這裡的樹葉為什麼這麼多啊。」半夏頗有些心悸的看著那些彷彿怪手一般的樹枝。
許錦言輕笑了一些道:「這種深山老林一般甚有人進,樹枝無人看管,長一些也是有的。」
半夏一聽此話,便更是憂心道:「可是小姐,那這個人約您到這種深山老林里見面,是不是居心不良啊。上次就想謀害您,這回來了這不見人煙的地方豈不是更加給了機會。」
許錦言點了點頭道:「孫白娘這個人很難捉,誰也說不清的心思。很有可能會繼續算計我,但是也有可能不會。不過努爾布一直在盯著孫白娘,以努爾布的武功制服一個孫白娘應該沒有問題。」
許錦言接下來還有一句話,但是並不敢告訴半夏。
孫白娘一個人自然好制服,但怕就怕孫白娘有幫手。前世那場腥風雨雖然說是出自張正之手,但是孫白娘在其中煽了多的風那就很難說了。
但這些日子努爾布一直盯著孫白娘,如果孫白娘真的和什麼人聯繫了的話,應該逃不出努爾布的監視。
思及此,許錦言稍稍放了心下來。馬車繼續前行,不一會兒就到了孫白娘在信上寫明的地點。
Advertisement
一下馬車,許錦言便深深蹙起了眉。
半夏環視了一下四周便警惕了起來,「小姐,這地方我怎麼覺得不太對啊。」
忍冬也點頭附和半夏的說法,「小姐,這地方的確不對。四都是大霧,連一戶人家都沒有。怎麼會有人約在這裡見面。」
眼前是一副白霧茫茫,白霧之下約可見一片不到邊際的花田。花田種的不知道是什麼花,只是紅的詭異,像是流淌的鮮。而這一整片花田,紅聚集在一起,就像是流河。
這些隨風而舞,在白霧裡搖曳生姿的花令人完全覺不到,只覺得骨悚然。「這花可能有問題。」許錦言在腦海里飛速搜尋著有關於這種紅到詭異的花的信息,但是頭腦中一無所獲。此刻,許錦言才清晰的知道了什麼是書到用時方恨。
雖然想不到這花是什麼花,但是許錦言瞧著那詭異的紅,直覺此花必定大有蹊蹺。
下意識的後退了一步,剛想抬頭對旁邊的半夏和忍冬說一句「向後退」,但是在抬頭的一瞬間,許錦言僵住了,隨後飛快的上前了幾步,死死的盯住了那片花海之中的一抹影。
海一般的花田中央,端站著一個小小的孩,那孩乖巧而可,穿著一淡月的繡花小襖,臉龐圓圓,那一雙眼睛似琉璃寶石,清而明亮,小孩正沖著許錦言微笑,甜甜的笑容能把人心暖化。
「佩玉……」許錦言不可置信的喊出了聲。——
街角一側,努爾布正在盯著作畫的孫白娘,他覺得有些奇怪。許小姐不是說這孫白娘今日要同見面麼,但現在日頭都快中午了,這孫白娘可沒有一點要的意思。
孫白娘今日同往常本沒有任何區別,日出之前就支了攤子,直到現在已經畫了五六副畫了。努爾布逐漸意識到了不對勁。午時剛過一刻,努爾布實在是等不下去了,直接飛進了許府,一路直奔桂念院。但剛一進去,努爾布的心就驟然一頓,他知道…。出事了。
桂念院里空空的,除了院子里灑掃的婢還在忙碌,但是主子卻不見了蹤影。
許小姐必定是去赴約了,但是孫白娘卻沒有去……
努爾布不敢再繼續想了,他腦子笨,想不來事,但是這世上自有聰明的人。
努爾布完全沒有停留,直接從許府飛去了張府。但彼時張正恰好不在,南邊出了點子,所有的閣員都被慶裕帝招進了乾清宮。
努爾布進去張府之後卻發現幾個黑人也在著急的轉。
努爾布心裡不詳的預越來越強烈,他知道張大人在許小姐邊設有保護的高手,這些高手都是被張正下了死命令的,絕對不可以離開許錦言半步,但是如今這些黑人卻擅離職守離開了許錦言,到了張府,明顯是出了事來找張正拿主意的。
努爾布搖了搖頭,將心裡的不詳之甩掉,立刻上前向這些黑人問道:「兄弟,你們是不是保護許小姐那一撥的?」
幾個黑人忙不迭的點頭。
努爾布抖著聲音問,「許小姐……是出事了麼?」
——
山谷里,半夏和忍冬莫名其妙的看著神激的許錦言,們順著許錦言的視線看了過去,當時目所及之空空,只有一片輕輕搖曳的紅花田,花田裡什麼也沒有,白霧繚繞間,氣氛詭異而恐怖。
明明花田裡什麼都沒有,但是許錦言卻盯著一點激的出了聲,若是這個時候,半夏和忍冬還察覺不出有問題,那們也真是笨到家了。
半夏立刻上前搖了搖許錦言的胳膊道:「小姐!小姐!你千萬別中計啊!」忍冬也急切的看著雙目激到赤紅的許錦言,焦頭爛額的想著對策。
但許錦言此時已經完全被花田中央的人吸引住了目,毫不理睬半夏的呼喚。盯著花田中央的那抹小小影,眼神里是強烈的震驚和激,輕輕的翕,一臉的不敢相信。
花田裡的小小影突然旋轉了起來,似乎是跳起了一支舞,像是花蝴蝶一般在紅的海里翩然。
許錦言眼裡的激之更甚,那支舞蹈記得,那是教給佩玉的。趙斐三十歲生辰的那一回,佩玉想在趙斐的生辰宴上給最尊重的父親獻舞,許錦言便親自給佩玉排了這支舞,佩玉練習了整整一個月,可佩玉畢竟是個孩子,練的再多,也只是將將目而已,那圓圓滾滾的胳膊舞起來,賞心悅目的分很低,只能擔的上一個可而已。
那段日子趙斐新得了一個舞姬,生辰宴上看那個活生香的舞姬還看不過來,哪裡有空看不喜歡的兒跳的「可」舞蹈。
於是佩玉練了一個月的舞蹈都了無用功,生辰宴之上,佩玉委屈卻不敢哭,只能紅著眼睛坐在席位上。許錦言看的心裡難,在生辰宴會結束之後,讓佩玉在月之下為跳了一次。
一邊喝酒一邊看兒跳舞,最後喝的酩酊大醉,眼裡流了整整一晚上。
前世月之下起舞的影與現在花田裡的影重合,一都不差,那真的是的佩玉。
那雙與花田裡小小人兒相似的琉璃眼眸里滿是欣喜,淚水已經止不住了,洶湧的從眼眶裡滾了出來。本以為再無相見之機的人再一次出現在了的面前,試問如何不激,如何不震驚,如何不喜悅。
是的,那是佩玉。
那是虧欠了太多,以為自己再也無法彌補的佩玉。
許錦言再不遲疑,提起子就往花田裡跑去。半夏和忍冬怎麼可能放任許錦言這般妄為,忍冬出手就要攔,但是許錦言像是被什麼附了一般,發瘋般的推開忍冬,本就不看一眼一邊聲嘶力竭呼喊的半夏和忍冬。
忍冬怕傷到許錦言所以不敢使力,但卻讓許錦言得了空,使了個巧勁兒就把忍冬推了到。忍冬摔下去的地方剛好有一塊石頭,的胳膊狠狠的撞上了石頭,吃痛的喊了一聲。
但任憑忍冬痛呼,許錦言也沒有毫的反應,連忍冬看都沒有看一眼,只自顧自的提起子,拚命的向那片花田奔去。
半夏在後面追許錦言,但是一進花田,白霧瞬間就浮了上來,將半夏的視線全部遮住。許錦言今日本就穿了淺白的服,白霧一起,許錦言的影更是消失的無影無蹤。
半夏焦急的跺腳喊道:「小姐!小姐!」
但是茫茫花田,白霧濃重,沒有一個人的回答半夏。只有半夏自己的聲音在這片空的土地上發出迴音,一圈又一圈,縹緲又令人心驚。
白霧遮住了紅的花田,同時也遮住了一些其他的東西。遠遙遙站著一男一,因為遙遠,影本就難以窺測,白霧還太厚,半夏四張,但是卻毫看不到這兩個人的存在。
男子拄著拐杖,眼眸霾,看著深白霧的許錦言冷笑,笑容森而可怖。
「呵,這麼深的執念。我還真是有些好奇,看到的是什麼人。」男子邊站了一子,那子面帶薄紗,出一雙勾人妙目,眉中心用鮮紅的料點了一個紅點,在雪白的皮映襯下,顯得妖嬈多姿。
子帶的面紗上自兩邊垂下長長的兩道由紅珍珠串的裝飾,隨著子一舉一而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面容紗雖然遮住了子的面容,但是仍然可以依稀窺見藏在紗巾背後的那張極的容。
許宗面激的看著這個子道:「多謝你替我收拾了這個賤人。」
「不急,別急著弄死。我有事想要從那裡知道。」帶著面紗的子抬起頭看著白霧裡跌跌撞撞尋找著什麼的淺白影。角漸漸勾出一個嘲諷的弧度,眼神狠而冰冷。
衡昭,這便是你在北明相中的人?
那就讓我仔細看看這個人到底有什麼本事。
許宗看著旁立著的子,漸漸出迷醉的眼神。這子自找上他之後就一直帶著面紗。從前他一直在全心的想著如何除掉許錦言,所以抑著那些心思,但是現在許錦言已經了攥在掌心裡的東西。許宗的心裡大松,再一看旁邊自面紗下約出絕頂貌的子,不由頓時就起了些旖旎的心思。
許宗還記得那一段日子,他斷了,日日活著苦痛之中,天天想著如何才能殺了許錦言。可是他毫沒有辦法,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許錦言從許家蠢貨變寧安翁主又變寧安郡主。
母親和妹妹沒一個中用的,全被許錦言那個賤人在手裡玩兒,他有斷了,毫沒辦法對許錦言下手。就是這個時候,這個子找到了他,說是想同他合作,一起除掉許錦言。
許宗躺在床上的這些日子以來算是長了些心眼,他一看這子的談吐氣度便知不是尋常人,且這子邊四隨行黑護衛,一看便知有著極大的背景。
許宗也沒多猶豫就答應了,反正他早就想殺了許錦言,有人自送上門當然是好事。
但許錦言實在是太難下手了,院子里幾乎滴水不,而且據這子說暗幾乎布滿了保護許錦言的高手。許宗想不明白,許錦言是自己的妹妹,知知底,就算現在不傻了,但也不可能突然擁有這麼大的能力,還請了那麼多的高手隨保護。
許宗覺得很奇怪,便試圖問那個子,但卻一句話都不說,只是一直冷笑。而且許宗看的很清楚,這個子笑的時候,不止冷,而且滿含嫉妒。
為了躲過這些保護許錦言的高手,他們等了很久才找到了這麼一個時機。那子說,這些高手武功極高,而且背後有人在管,若是貿然對許錦言下手,將這些高手背後的人引來就難辦了。所以要除掉許錦言,就一定要讓自己離這些高手的保護。
猜你喜歡
-
完結184 章
冷王盛寵魔眼毒妃
一朝醒來,她不僅成了需要坐輪椅的殘疾人,還被替代胞姐扔進了陵墓陪著一個躺在棺木裡的男人,沒錯,她就是那個活人陪葬. 在這不見天日的陵墓中度過漫漫黑夜,一朝突然被匆匆換走,因爲帝王有旨,欽點她這個殘廢嫁給戰功赫赫的九王,其實只爲羞辱! 九王帶領千軍萬馬守衛邊關,戰績輝煌天下皆知.但某一天,聖旨下來,要他娶一個雙腿殘廢坐在輪椅上的女人.這是個偌大的羞辱,他暫時接受;不就是個殘廢的女人麼?和一件擺在角落裡接灰塵的花瓶有什麼區別? **** 然而,當做了夫妻後,才發現對方居然如此與衆不同! 這個打小混在軍營裡的九王有三好,成熟,隱忍,易推倒! 這個實際上根本就不是殘廢的女人有三毒,嘴毒,眼毒,心更毒! 火熱的生活開始,其實夫妻之間也是要鬥智鬥勇的. **** 紅燭搖曳,洞房花燭. 男人一襲紅袍,俊美如鑄,於紅燭輝映間走來,恍若天神. 走至喜牀前,單手拂去那蓋在女人頭上的蓋頭,眸色無溫的掃視她一遍,他的眼神比之利劍還要鋒利.審視她,恍若審視一個物件. 女人任他審視,白紙一樣的臉上無任何表情,眸子清亮,卻獨有一抹高傲. 對視半晌,男人拂袖離去,女人收回視線閉上眼睛。
99.9萬字7.54 45971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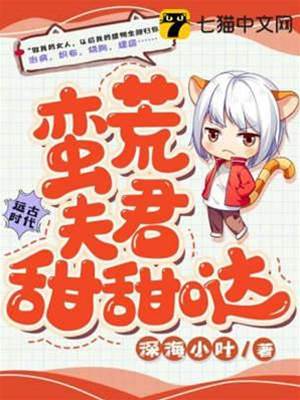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8714 -
完結347 章

穿越第一天,我逼婚了攝政王
整個京城都炸了鍋。 京城第一花癡草包沈驚鴻糾纏溫雅如玉的三皇子不成,竟然破罐子破摔,轉頭去逼婚了冷麵閻羅一般的攝政王! 更令人驚掉下巴的是,攝政王他、他居然還答應了! 面對或同情憐憫、或幸災樂禍的各種目光,攝政王蕭千決嗤之以鼻:「我家王妃的好,你...
62.9萬字8 29712 -
完結439 章
鸞鳳重華
重活一世,沈君兮只想做個坐擁萬畝良田的地主婆,安安穩穩地過一生,誰知她卻不小心惹到了一臉高傲卻內心戲十足的七皇子!“做我的皇妃吧!”“不要!人家還只是個孩子!”“沒關系,我可以等你……”這是一個關于青梅竹馬的故事……
81.2萬字8 155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