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我是黑蓮花》 第32章 看來你還記得
第二天,溫念南開車去了樂晴大街,這次他把車停在了離唐朔近的地方下車走了進去。
顧言笙自從昨天聽到溫念南經常來樂晴大街,心中疑他到底來做什麼,猶豫再三后還是在開完會后去了樂晴大街。
他把車停在街邊,坐在車里點燃了煙,眼睛不由自主的往外瞥。
突然看到對面街道溫念南的車停了下來,車上的人從容的下車走進了旁邊的店。
顧言笙就這麼冷著臉坐在車里煙,約一個半小時后溫念南才走了出來,后還跟著個人。他微瞇眼睛看向那人,待看清后臉瞬間變了,咬牙切齒的開口:“好啊,又是唐朔!”
手里的煙被他扔了出去,開車離開了這里。
溫念南還沒上車就被唐朔著車門不肯撒手,委屈的眼神看著他說道:“今天怎麼回去的這麼早?再陪陪我好不好,就一會。”
Advertisement
“真的不行,我回去后還要改一下曲譜。”
“好吧,那等你寫好后彈給我聽。”
溫念南回家后用電腦錄了今天寫的容,發現有兩不對的地方,可他改了幾遍還是覺得不對。
突然他回頭看向一直放在房間的那架琴,眼中閃過一抹悲傷,那是媽媽生前最的琴,可自從顧言笙不讓他彈琴后就再也沒過。
溫念南走了過去輕著琴鍵,想起當初顧言笙說的話面猶豫。
就一次…就這一次應該沒事…
顧言笙回公司后一直心不在焉的,跟書隨意代了幾句便離開了公司。
剛一進門就聽到了琴聲,他卻沒有急著上去,而是轉坐在了客廳沙發上閉目養神。
一旁的徐叔擔心的著他,他是知道先生說過不許夫人再琴的,很怕先生暴怒后再次打傷夫人。
樓上的琴音停了,沙發上的顧言笙也睜開了眼睛,他抬眼看了眼徐叔,隨后緩緩走上了樓。
溫念南彈奏的是母親教自己的第一首曲子,他低頭趴下子滿是懷念的著琴,沒注意到房門被打開了。
“彈的不錯啊。”后突然傳來狠狠的聲音。
溫念南聽到聲音后臉瞬間慘白,僵著轉過。
看到顧言笙臉上駭人的可怕表,他心中一陣發涼,不自覺的開始發抖,卻還是強出一抹僵的笑:“你…你回來了。”
“又是這副令人惡心的表!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你還真是厲害,在我面前裝的這麼鐘,在你人那里倒是笑得開心。”
顧言笙一看到他這副虛假無比的笑就覺得諷刺,原來不是不會笑是只對舊人笑。
“人?”溫念南出疑的表,隨即想到了什麼臉更加慘白。
“呵,你今天去了哪里你自己清楚,溫念南你還真是厲害,用這種稚的理由去勾引唐家小爺,也只有他那種智商的人才能被你騙到!”
“我沒有勾引他,我只是為了去彈琴,所以我才…”
顧言笙突然走上前,嚇得對面的人后退了一步,站在離溫念南不遠的地方,厲聲問道:“當年我跟你說過什麼?”
聽到這句話溫念南臉更加白了幾分,眼中閃過恐懼,說道:“說…以后不許我再彈琴。”
“很好,看來你還記得。”
猜你喜歡
-
完結301 章

丈夫的秘密
一場車禍,意外得知丈夫出軌的秘密,更可怕的是丈夫正計劃一場巨大陰謀等著她。果真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她要讓他付出慘痛的代價,等著瞧吧...然而,事實真相又是如何,誰是背后操手,誰又是最大贏家....陰謀論就此展開。
29.4萬字8.18 12715 -
完結199 章

替罪情人:我曾愛你比恨深
十年前他一句為什麼死的人不是你。 讓她心如死灰,從此畫地為牢。 十年后再遇,那人卻抓著她不肯放。 蘇澈你不是要我死麼,何苦再來糾纏? 隋益不,我改主意了。這次,我要你跟我一起萬劫不復……
45.1萬字8 19738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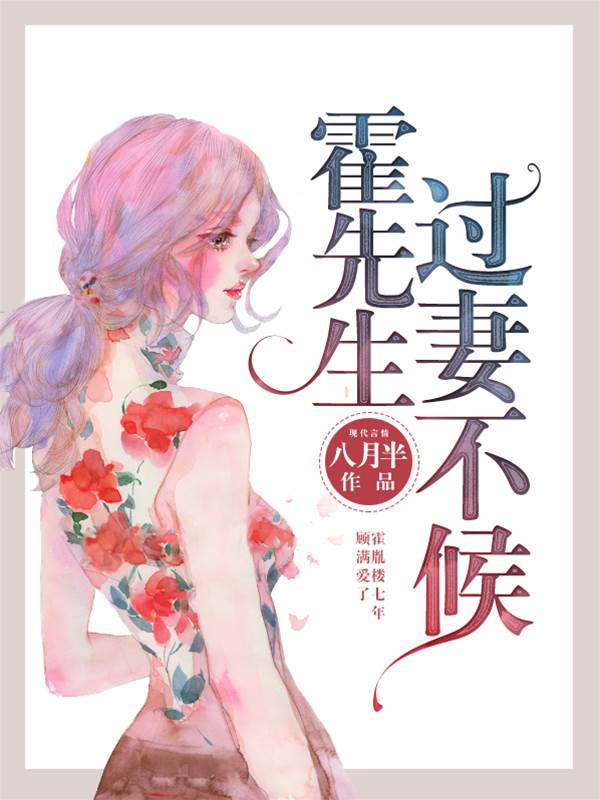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8451 -
完結169 章

于春日熱吻
室友口中的江轍:衆星捧月的天之驕子,浪蕩恣意,誰碰誰上癮。 陳溺安靜聽着,未置一詞。 游泳館內,她以爲他溺水,伸出手時反被他攬腰一起下沉。 水花四濺,男生挑眉,覆在她耳笑得惡劣坦蕩:“沒告訴過你?我人渣來的。” 沒人敢想過多年後,他會因爲一個女孩喝得酩酊大醉。 長廊處,陳溺擦着嘴邊被咬亂的口紅,語氣譏諷:“你是狗?” 江轍俯身貼近她後頸,任憑菸灰灼燙長指,自嘲勾脣:“是,你的狗。”
26萬字8 5593 -
完結872 章

誘捕玫瑰
五年前,溫棉被人戳着脊樑骨,背上爬養兄牀的罵名。 所有人都說她是個白眼狼,不懂得感激裴家賜她新生,反而恩將仇報。 只有她自己知道,這所謂的恩賜,只是一場深不見底的人間煉獄。 五年的磋磨,溫棉險些死在國外。 重新回來時,她煥然一新,發誓要讓裴家的所有人付出代價。 本以爲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死局。 卻沒想到,這個將她送到國外的養兄,卻跟個甩不掉的牛皮糖一樣跟在身後。 她殺人,他遞刀,她報仇,他滅口。 終於,溫棉忍不住了—— “你到底要幹什麼?” 而那隱忍多年的男人終於露出了尾巴:“看不出來嗎?我都是爲了你。”
84.4萬字8 21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