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吹一夜滿關山》 第57章 故夢回(3)
把頰邊發往耳后,臉嚴肅起來,低聲道:“姑母早年,曾在西境邊關跟著我祖父在梧州住過幾年,也因此結識了當時在關游歷的一名西涼王侯,這位王侯在西涼不得志,是被排在權利中心外的,這兩人相后離別,彼此約定都要在自己的國家里拿到最高的權力……”
謝瑾也穿上中披上外袍坐起來,靜靜聽說著,間或一的肩頭。
“姑母進了宮,一連生了三個子,長子就是現在的皇上,次就是阿旋,第三子,也就是現在的宣平王,他是早產,孱弱,但聰明伶俐,先帝甚喜,姑母得以正位中宮,長子也被封為太子,沈氏一門從此炙手可熱,但和你們謝家一直都有明里暗里的爭斗……”
謝瑾握住一只手,笑道:“這個你不用說了。”
“就說怎麼了?”沈蕁睨他一眼,“總之,謝家樹大深,又一直掌著西北邊境的兵權,姑母和太子的地位不算穩固,好不容易西境北境劃開,我爹拿到了西境軍兵權,但況你也知道,幾名謝家舊部并不服他,姑母心里很不滿,想把我爹換下來但又一直沒有合適的契機。”
謝瑾聽說到要,心也沉重起來。
“八年前西涼發攻擊,策劃這場戰事的便是已在西涼國拿到軍隊統帥權的那名西涼王侯,他給姑母帶了信,說他需要一場戰事來穩固他在西涼的地位,正好姑母也想重整西境軍,把不服我爹號令的吳將軍等人除掉,也借機把我爹換下來……”
謝瑾點著頭,沒說什麼,兩國的掌權者借由相互間的戰爭來控制邊關軍隊,掌控軍權,以達雙方在自己國家權利斗爭中的某些目的,實現自己的和野心,這種事并不是沒有先例。
Advertisement
翻云覆雨間他們既對立,又依賴,彼此博弈,相互撕咬,是權利催生出來的一種邪惡危險而暗詭異的關系。
“……兩人約定西涼這次的目標是吳將軍統領的四萬騎兵,一旦達到目的西涼便退兵,姑母給當時在西境軍里擔任我爹親衛的沈淵下了指令……”
那時沈淵還小,沈煥很看中這個侄子,特意讓他做自己的親衛,時時刻刻教導他,這事謝瑾也是知道的。
“探得西涼準備大舉發戰事后,我爹娘和西境軍的幾名主要將領制定了應對方略和戰,這場議事連我都沒能參與,是完全保的,但作為我爹親衛的沈淵卻很清楚。”
沈蕁繼續說著,聲音有了幾不易覺察的抖,謝瑾馬上覺到了,雙臂環過來,把攬在自己懷里。
“我后來猜想,應該是我爹接了個別人的建議,由吳將軍率領騎兵先發制人,埋伏在西涼軍必經的翠屏山谷中,等西涼大軍一經過此便發伏擊。而提出建議的人應該得到了事先的授意,不無導我爹之意……”
皺著眉頭,繼續道:“西涼軍來勢洶洶,大敵當前,這次吳將軍等幾人應該是對我爹的決議認可了,所以當夜便開始召集將領,制定詳細的伏擊戰。”
謝瑾聲音也沉了下來,“沈淵把這個消息給了那位西涼王侯?”
“對,”沈蕁道,“西涼軍事先就已準備好,一得到消息,立刻出埋伏在翠屏山谷周邊,等吳將軍等人一到,便展開了大肆屠殺,這一戰,吳將軍率領的四萬西境軍騎兵全軍覆滅……”
兩人的心都同時絞了,指尖發冷,往他懷里了,“姑母雖想把我爹換下來,但也不想讓他背太多的罪責,所以把過錯都推到了吳將軍頭上,扣了個不聽主帥命令,私自發兵的罪名。只是沒想到,西涼軍殺紅了眼,勢如破竹殺到了寄云關的關墻下,西境軍守兵幾乎潰不能擋,而北境援軍來得太晚,我爹和我娘在城墻上督戰了兩天兩夜,我爹被沖上來的西涼人一刀封,我娘中五六刀,被抬下城墻時還未斷氣,……”
眼前出現了那暗無天日的一刻,語聲雖還平穩,但眼眶已經紅了,角微微著,沒再說下去。
那是噩夢一般的回憶。
城墻上下大火熊熊,利箭石砲飛,西涼人的云梯一架架靠過來,壯的木樁一下下撞擊著城門,蝗蟻般的西涼人悍不畏死地冒著燃著火的箭矢和長矛,一波波地從云梯上沖上城墻,到都是尸殘肢,鮮汪了一片片的泊,染紅了整個墻頭,又匯集河順著墻角往下淌。
十七歲的彼時正率領城墻上的守軍與西涼人廝殺,被人拽下城墻,去見娘最后一眼。
娘的上著箭矢,中了好幾刀,鎧甲破得不樣子,全都是鮮,而爹就被人抬在娘邊上,大半個頸脖被劃開,頭顱歪在一邊,猙獰的斷裂汩汩的鮮還在不停地往外涌。
而娘掙扎著抬起模糊的手臂去抹臉上的眼淚,用盡最后一力氣對說:“眼淚是懦弱的表現,阿蕁,我希你以后,可以流、流汗,但不要流淚。”
謝瑾什麼也沒說,只沉默地摟了。
太后何嘗料不到西涼軍不會退兵?破而后立,不過是想從這樣的絕境和廢墟中重新建立一支能完全把控的軍隊罷了。
沈煥和他統領的西境軍達不到的要求,那就把這支軍隊完全地打碎再融合,看誰能從這個困境里穎而出。恐怕在整個計劃里,唯一的意外就是沈煥夫婦的雙雙陣亡。
否則不會故意拖延時間,等相鄰的北境軍終于等到援救指令時,寄云關已經被困許久。
他想起了那時的形。
西涼大舉發進攻后,謝戟一直在等朝廷支援西境的指令,指令一下達,他即刻調撥了三萬大軍往西境趕,謝瑾統領的重騎營麟風營是最早到達的一批。
但也是西涼軍在寄云關城墻下發第一波攻勢的第十天了。
他率領麟風營騎兵沿著蒙甲山邊緣行進,趕到正在攻打城墻的西涼軍背后,從后往前殺開一條路,沖到城樓下時,一眼便看見墻頭上揮舞著長刀一刀斬下一名西涼人手臂的沈蕁。
他無瑕和說話,帶領麟風營騎兵配合城墻上的西境殘軍,在城墻下一刻不停地沖殺,終于將西涼軍這一波的攻勢殺退。
千瘡百孔的城門打開,謝瑾進了城門,沈蕁卻還留在城樓上,部署應對西涼軍下一波攻勢的戰。
正好這時第二批北境援軍趕到,久攻不下的西涼人吹響號角,開始大舉撤退。
沈蕁從城墻上下來,找到他問他:“謝瑾,你帶了多騎兵?”
他道:“八千,剛折了一些,七千不到吧。”
“我這里還有一千騎兵,夠了……”揩揩臉上的跡,通紅的眼睛直直地盯著他,“你把這七千人暫時借給我,我保證原封不地還你。”
“……你瘋了?”謝瑾猜到了的意圖,“不行。”
沈蕁沒說話,也沒移開目,臉上和眼睛里都是恨意和堅持。鮮凝固在骯臟的臉頰邊,把頭盔下的發全凝在了一塊兒。
謝瑾往地上吐了一口混著和沙的吐沫,□□往地上一,“五千人,我借你五千,不過沈蕁,你可聽好了,一個我回頭都要找你算賬!”
沈蕁角輕了一下,沒跟他討價還價,從腰里出一塊骯臟的領巾,丟到一邊的火堆里。
那塊布在火中并沒有燃起來,反而不一會兒就變得鮮麗如新。
謝瑾很小的時候就聽在他面前炫耀過,說他父親得了一塊西域上好的火浣布,用來給母親做了一塊領巾。
他幾天前聽說了沈煥夫婦戰死的消息,想來這塊領巾就是沈蕁從母親尸上取下來的。
他瞧著把那塊鮮紅如的領巾從火中挑出來,拿匕首從邊上割了幾布條,余下的塞回腰里。
把那幾細布條編一紅繩,編繩的手微微抖著。
謝瑾一言不發地看著編。
猜你喜歡
-
完結1082 章
爆笑王妃:邪魅王爺澀澀愛
太師府剋夫三小姐,平生有三大愛好:食、色、性。 腹黑男八王爺,行走江湖有三大武器:高、富、帥。 當有一天,兩人狹路相逢,三小姐把八王爺全身摸了個遍,包括某些不該摸的地方,卻拒絕負責。
213.7萬字8.18 88415 -
完結861 章
龍鳳雙寶神醫娘親藥翻天
天才藥劑師一朝穿越成兩個孩子的娘,還是未婚先孕的那種,駱小冰無語凝噎。無油無鹽無糧可以忍,三姑六婆上門找茬可以忍,但,誰敢欺負她孩子,那就忍無可忍。看她左手醫術,右手經商,還有天老爺開大掛。什麼?無恥大伯娘想攀關系?打了再說。奶奶要贍養?行…
156.3萬字8.18 81645 -
完結1025 章

農家小福妻有法術
【無所不能滿級大佬vs寵妻無度鎮國將軍】 現代修真者楚清芷下凡經歷情劫,被迫俯身到了一個古代農家小姑娘身上。 小姑娘家八個孩子,加上她一共九個,她不得不挑大樑背負起養家重任。 施展禦獸術,收服了老虎為坐騎,黑熊為主力,狼為幫手,猴子做探路官兒,一起去打獵。 布冰凍陣法,做冰糕,賣遍大街小巷。 用藥道種草藥,問診治病,搓藥丸子,引來王公貴族紛紛爭搶,就連皇帝都要稱呼她為一句女先生。 為了成仙,她一邊養家,一邊開啟尋夫之路。 …… 全村最窮人家,自從接回了女兒,大家都以為日子會越來越艱難,沒想到一段時間後,又是建房又是買地…… 這哪是接回的女兒,這是財神爺啊! …… 連公主都拒娶的鎮國大將軍回家鄉休養了一段時間,忽然成親了,娶的是一位小小農女。 就在大家等著看笑話的時候,一個個權貴人物紛紛上門拜見。 太后拉著楚清芷的手,“清芷,我認你做妹妹怎麼樣?” 皇帝滿意地打量著楚清芷,“女先生可願意入朝為官?” 小太子拽住楚清芷的衣擺,“清芷姐姐,我想吃冰糕。”
177.3萬字8.46 176072 -
完結60 章

春閨嬌
一上一世,沈寧被死了十年的父親威逼利誘嫁給喜愛男色的東宮太子秦庭。 身為太子妃,她公正廉明,人型擋箭牌,獨守空房五年,膝下無子無女,最終熬壞了身子,被趕出東宮死在初雪。 重回始點,她褪去柔弱,步步為營,誓要為自己謀取安穩幸福,提起小包袱就往自己心心念念的秦王秦昱身邊衝去。 這一世,就算是“紅顏禍水”也無妨,一定要將他緊緊握在手裏。 二 某日。 沈將軍府,文院。 陽光明媚,鳥語花香,突傳來秦昱低沉清冷如玉般的聲音:“阿寧,你年紀小,身子弱,莫要總往我府上跑了。” 正抱著茶盞喝的開心的沈寧暴跳如雷——她跑啥了跑?倒是您一個王爺,沒事少來行嗎? 三 問:該怎麼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嫁入秦·王·府? 天鴻清貴的秦昱勾了勾薄唇:王妃,床已鋪好,何時就寢? ps:男女主雙潔 ps:關於文中的錯別字,過完年我會抽時間整改一次,另外是第一次寫文,許多細節可能沒有完善好,但我日後會更加努力,謝謝觀看。 內容標簽: 情有獨鍾 宅鬥 重生 甜文 主角:沈寧
18.5萬字8 21891 -
完結1055 章

最小反派:團寵魔女三歲半
魔女變成三歲半小團子被迫找爹,可是沒想到便宜老爹一家都是寵女狂魔。從此,小團子開始放飛自我,徹底把改造系統逼成了享樂系統,鬧得整個江湖雞飛狗跳。小團子名言:哥哥在手,天下我有。什麼?有人找上門算帳?關門,放爹!
192.7萬字8 28556 -
完結4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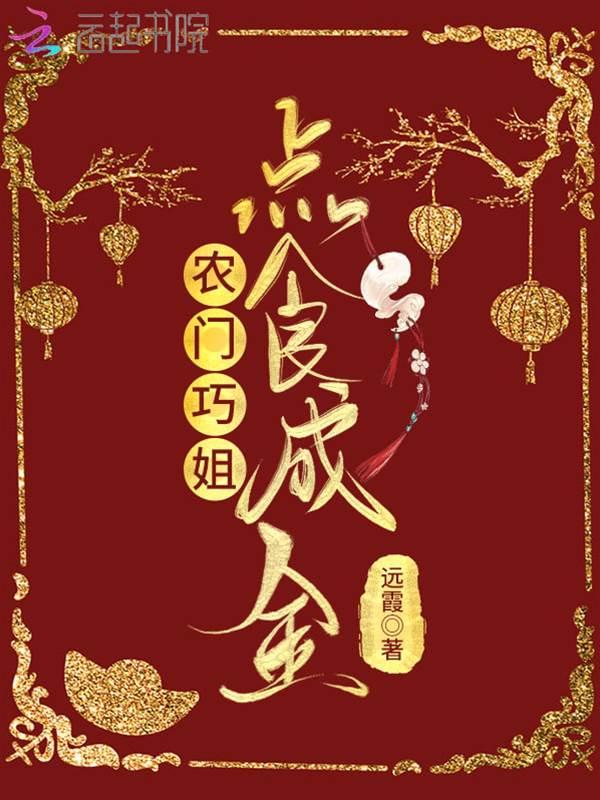
農門巧姐點食成金
高級點心師意外穿成13歲彪悍小農女-包蓉。後奶惡毒,親爺成了後爺。,爹娘軟弱可欺,弟弟幼小,包蓉擼起袖子,極品欺上門,一個字:虐!家裏窮,一個字:幹!爹娘軟弱慢慢調教,終有一天會變肉餡大包,弟弟聰明,那就好好讀書考科舉,以後給姐當靠山,至於經常帶著禮物上門的貴公子,嗯,這條粗大腿當然得抱緊了,她想要把事業做強做大,沒有靠山可不行,沒有銀子,她有做點心的手藝,無論是粗糧、雜糧、還是精糧,隻要經過她的手,那就都是寶。從此,包蓉銀子、鋪子全都有,外加一個自己送上門的親王夫君,氣得後奶一概極品直跳腳,卻拿她無可奈何。
77.6萬字8 3790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