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乖》 第85章
空氣中有尤加利葉清冷的木香。
周尤眼前一片模糊,只能一直睜著眼睛,才能忍住落淚的沖。
接過江徹送來的玫瑰花束,手有些不自覺地抖,而江徹扯了扯,這才騰出手,打開紅絨的首飾盒。
“周尤,你愿意嫁給我嗎?”
眼睫撲簌,還是沒有忍住,大顆淚珠砸在的玫瑰花上,花瓣輕。
也不知道是淚水模糊視線,還是鉆石太過閃耀,周尤都看不清江徹的臉,手錯了方向,江徹及時握住的手,了白的手心。
在往無名指上套戒指時,江徹忽地一頓,抬頭道:“你還沒有回答愿不愿意。”
周尤哽咽著點頭,“愿…愿意,我愿意。”
江徹角上翹,這才將戒指套的指節。
“親一個!親一個!親一個……”
就在這時,不知從哪里冒出一大群江星的員工,在不遠起哄。
Advertisement
周尤手忙腳地眼淚,江徹卻很干脆,直接站起來,順便將周尤一起拉起,然后捧著的臉,吻掉眼角淚水,又吻上的。
大家起哄得愈加厲害。
一片歡呼聲中,約還能聽到陳星宇調侃,“差不多得了啊,場地要超時了!場地費自理啊!”
“哈哈哈哈陳總你也太摳門了吧!”
“陳總這是來自單狗的嫉妒!”-
晚上,江星在君逸辦慶功宴,江徹雙喜,被人灌了不酒,趁大家不注意,他拉著周尤提前離開。
冬夜的帝都,空氣不如星城潤,風吹來,有些干冷。
暖黃路燈盞盞,六角雪花輕輕飄落在燈下,晶瑩剔。
“怎麼樣,腦袋還暈嗎?”
江徹搖頭。
周尤仔細打量他幾眼,還不放心,“回去我給你煮點醒酒湯。”
江徹這才點點頭。
周尤不認識路,心里也沒點數,“我們往哪邊走?”
江徹隨便指了個方向,又拉住的手,揣自己的外套口袋里,“陪我走走,醒醒酒。”
周尤乖巧地“嗯”了聲。
其實這座城市才是江徹從小生長的地方,它大而包容,繁華也老舊。
時飛逝,很多小時候的東西都已幾經更迭面目全非,可仍有些東西仿佛被刻意忘,始終停在那里。
江徹一路都在和周尤說話,有他年喜歡吃的零食,有他讀書時買過CD的店,還有很多往事。
“我十九歲的時候,有次一個人去意大利,晚上還要飛黎。去機場的時候誤了點,本來我想改簽第二天的航班,在機場睡一晚算了,可你知道嗎,那個機場晚上竟然關門,我被關在機場外面,就那麼坐著坐了一整晚。
“我那個時候和我爸吵得很厲害,所以也沒打電話讓人幫忙,那晚特別冷,我從來沒有覺得一個晚上會那麼難熬,也從來沒有那麼想念過帝都。”
“你怎麼總跟你爸爸吵架。”
江徹輕哂,又想起了什麼,“話說回來,我不跟他吵,可能也不會跟你在一起了。”
周尤抬眼,有些不解。
“在迪拜的時候,也是因為跟我爸吵架,我才住到那家酒店,也才會在那家酒店的酒吧被你潑了一酒。”
咳,潑酒什麼的……
周尤頓了頓,很快轉移話題,“對了,你什麼時候又去了迪拜?那個視頻……”
江徹在掌心撓了撓,角微微上翹,“你猜。”
“我怎麼知道。”
“那你猜到了,我再告訴你。”
“江徹!”
“不然你親我一下?或者我一聲老公也可以。”
“你無恥!”
地上的雪積了厚厚一層,兩人在帝都北風清冷的冬夜馬路,留下一深一淺兩串長長的腳印,時而拉遠些距離,時而纏在一起。
答案其實已在周尤手中,的求婚戒指側,刻了一個紀念日。
那是江徹趁著出差繞道迪拜跳傘的日子,往前一年,他們在那天相遇。
今年冬日,江星上市前最重要的一場新品發布會,他向周尤求婚,周尤答應了。從此值得紀念的日子又多了一個。
故事沒有辦法以long long ago開端,卻能以after a long long time結束。
很久很久以后,他們也還記得帝都冬日這場初雪。
(正文完)
猜你喜歡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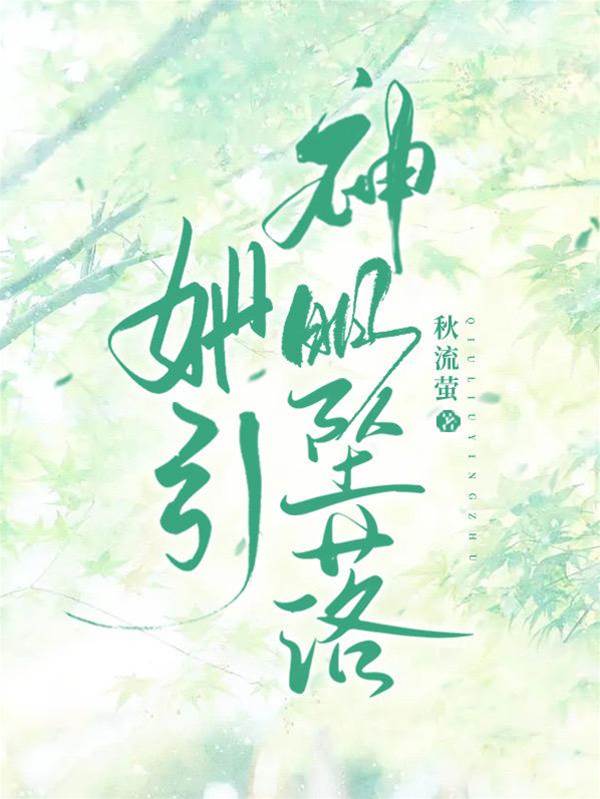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69 章

溫先生的心尖月
(蓄謀已久 細水流長 甜寵 雙潔 無虐 年齡差五歲左右)(女主醫生,非女強)*【溫婉清麗江南風美人 & 內斂沉著商圈大佬】容煙出身書香門第,自小跟隨外公生活。聽聞外公給她尋了門親事,她原以為聯姻對象是同為醫生的溫二公子,殊不知卻是接管溫家的溫景初。煙雨灰蒙,寺廟裏,容煙瞥見與她擦身而過的男人。上一次見他還是四年前,可他從不信神佛,為何會出現在這裏?朋友生日聚會結束,溫景初送她歸家。車內,容煙壓住心中疑惑,終究沒問出口。*容煙本是溫吞的性子,喜靜,信佛。她自認為婚後的兩人是相敬如賓,搭夥過日子。而他卻步步誘她淪陷。某日,容煙在收拾書房時看到了寺廟的祈福袋,裏麵白色宣紙上寫著她的名字,似乎珍藏了許久。而此時溫景初正接受電視臺采訪,清肅矜貴,沉穩自持,淡定從容與人交談。主持人問,“溫先生,聽聞您並不信神佛,但為何每年都到靈山寺祈願?”容煙手中拿著祈福袋,略帶緊張的等待著他的回答。男人黑眸如墨,思忖片刻,緩緩啟唇,“因為溫太太信佛。”簡單一句話卻擾亂她的心。
33.1萬字8.09 265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