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宴》 第35章 十個面首 帶1150鉆石加更 (2)
。”
翻了一頁文書,江玄瑾沒好氣地道:“你說。”
懷玉咧就道:“我是整個北魏最的姑娘!”
江玄瑾:“……?”
“你這表什麼意思?”懷玉氣得瞪眼,“讓你重復第一個字,又沒讓你承認這句話!”
不管要不要他承認,能說出這句話就無恥的好嗎?神復雜地一眼,江玄瑾重復:“我。”
“就是這樣,回答得再快點兒。”懷玉嘿嘿笑著,飛快地道:“春天的?”
“春。”
“秋天的果實?”
“秋。”
“你心悅的人?”
“你。”
字吐得快,說完才覺得哪里不對勁,江玄瑾抬頭,就見床上那人抱著被子笑了一團。
“你心悅的人是我。”一邊笑一邊道,“自己說的話,可記好了啊!”
反應過來又被誆了,江玄瑾額上的青筋跳了跳,微惱道:“無恥!”
聽著這兩個字,李懷玉不僅不生氣,反而笑得更歡,滾來滾去的,差點從床上摔下來。
乘虛進來的時候,就看見白四小姐抱著被子在傻樂,自家主子則坐在離床老遠的椅子上,不知道是被氣著了還是怎麼的,耳微紅。
“主子。”來不及細究這兩位之間又發生了什麼,乘虛小聲稟告,“當真抓著人了,還是不止一個。”
“嗯?”江玄瑾抬眼。
乘虛著他的耳朵說了幾句,聲音極小,懷玉支長了耳朵也沒能聽見。只見聽完之后,江玄瑾“刷”地就站了起來。
Advertisement
“怎麼啦怎麼啦?”連忙問。
吩咐了乘虛兩句,江玄瑾走到床邊,心甚好地道:“你也算幫了我一個忙,可有想什麼要的東西?”
方才還沉著臉呢,突然就這麼高興了,還要送東西?懷玉很意外,沒回答他的問題,倒是問:“是不是之前給你出的主意起作用啦?”
“算是起了一半。”他道。
懷玉急了:“你說話能不能直接點?起了一半是什麼意思?”
看好奇心重,江玄瑾便解釋道:“你之前不是教我套人話?我想了想,抓著的那個人的話實在是不好套。與其套,不如用來套別人。所以我用當了餌,釣著了上次跑丟的魚。”
李懷玉聽得愕然,心里猛地一沉。
“方才乘虛說,這魚還大。”江玄瑾道,“也算你半份功勞。”
懷玉:“……”這半份功勞真的不想要。
是想制造機會讓陸景行他們去救青的,結果差錯,竟然害了他們?微微拳頭,李懷玉氣笑了,這紫君是不是天生跟八字相克?不然怎麼挖好的坑,反而被他用來把埋了?
“能讓你這麼高興的人,我倒是想見見。”收斂住氣憤,懷玉掛上一副醋意,“你不是問我有什麼想要的嗎?那我要跟你一起去看熱鬧!”
江玄瑾一頓,繼而皺眉:“這有什麼熱鬧好看?”
“我不管!”懷玉耍賴,“咱倆是即將婚的夫妻,我可不能‘什麼都不知道’!從今日起,你興趣的事,我都要知道!”
這一副蠻橫不講理的模樣,又可惡又有些可,江玄瑾覺得頭疼:“你一個姑娘家。摻和這些事干什麼?”
“誰說我是摻和事啦?”懷玉叉腰,一本正經地道,“我是想摻和你!”
“……”
說兩句沒沒臊的話,就以為他會心?江玄瑾冷漠地轉。
半個時辰后,他把白珠璣抱上了馬車。
不是,這真不是他心,實在是這人太能鬧騰,他想一個人走,就抱著他的腰不撒手,又是撒又是裝可憐的,還跟風哭訴說他過河拆橋、兔死狗烹……
且不說過河拆橋是怎麼回事吧,能把自己說狗,也真是豁出去了。再不帶一起走,他仿佛就要了北魏第一負心漢。
罷了,江玄瑾想,區區眷,又不是什麼正經公事,帶上也無傷大雅。
于是,李懷玉就以一種裝傻充愣的姿態,一路著紫君的懷抱,然后被放在主樓的屏風后頭。見著了那些被抓的人。
一瞧見就梧,心里就震了震,再一瞧見后頭齊齊整整的九個人,李懷玉眼前一黑,好懸沒直接暈過去。
這些人怎麼被抓住的?怎麼能被抓住的!不是都該離開京都了嗎?
江玄瑾坐在主位上,沉默半晌才開口:“各位別來無恙?”
就梧可沒心思跟他寒暄,直接冷聲道:“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他們這些人,多多都曾與這位紫君有過節。紫君看他們不順眼,覺得長公主留他們在宮里很是荒唐,他們也看紫君不順眼,覺得這人管得實在太寬。
昔日有丹在,紫君沒能對他們做什麼。如今丹沒了,他們又落在這個人手里,還能有什麼好下場不?
下頭十個人,都已經做好了赴黃泉陪長公主的準備。
然而,江玄瑾沒要殺也沒要剮,任憑他們怒目而視,他臉上一片平靜:“你們只需回答本君一個問題,便可以離開這里。”
就梧有點不敢置信,皺眉道:“你耍什麼花樣?”
怎麼可能這麼輕易放他們走?
“質疑之前。不如先聽聽本君的問題,看你們能不能回答得了。”江玄瑾道。
就梧皺眉:“你說。”
江玄瑾起,目掃過屋子里這十個人,沉聲問:“在司馬旭死的那個時辰里,丹究竟在何?”
竟是問這個?眾人都有些意外,相互看了看,又齊齊沉默。
當初長公主被問罪,就是因為無法證明案發之時自己不在場。的確是不在場的,但不能說自己去了哪里。況且就算說了,也不會有人信。
“怎麼?當真回答不上來?”等了一會兒都沒聽見聲音,江玄瑾不耐煩地皺了眉。
一片沉默之中,清弦開口說了一句:“人都死了,你問這個干什麼?”
江玄瑾也不瞞:“自然是想知道司馬旭究竟是不是長公主殺的。”
“自然不是!”清弦怒聲反駁,“殺司馬丞相干什麼!司馬丞相是個好人!”
“哦?”江玄瑾側頭看了看他,“那你知道當時在何?”
清弦一噎,下意識地看了一眼就梧,后者打量了江玄瑾一一會兒,冷聲道:“回答了,你當真就放我們走?”
“自然。”
“那好,我告訴你。”就梧道,“長公主當時不在宴會。也不在福祿宮,在……”
呯——
倏地一聲巨響,嚇得就梧即將出口的話猛地咽了回去。眾人都都是一驚,齊齊循聲側頭往旁邊看去。
巨大的梨木雙繡屏風不知為何倒了下來,震得整個屋子都了。那屏風后頭,是個坐在椅子上的小姑娘。像是也被嚇著了,茫然地眨眨眼,然后朝他們傻笑:
“嘿嘿!”
猜你喜歡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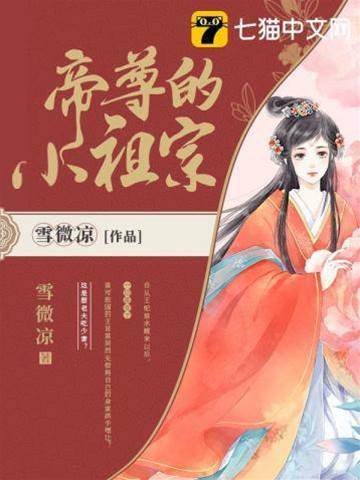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1327 -
完結506 章

媚婚之嫡女本色
陌桑穿越了,穿越到曆史上沒有記載的時空,職場上向來混得風生水起的白領精英,在這裏卻遇上讓她恨得咬牙切齒的克星,高冷男神——宮憫。 他嫌她為人太過陰詭狠毒。 她嫌他為人太過高冷孤傲。 本想無事可做時,虐虐渣女渣男,逗逗小鮮肉。 豈知一道聖旨,把兩個相互看不順眼的人捆綁在一起,組成嫌棄夫婦。 自此兩人過上相互猜測,彼此防備,暗裏算計,夜夜心驚肉跳的生活。 豈知世事難料,兩個相互嫌棄的人看著看著就順眼。 她說“你是護國賢臣,我是將門忠良,為何跟你在一起,總有種狼狽為奸的覺悟。” 他說“近墨者黑。” 陌桑點點頭,確實是如此。 隻是,到底是誰染黑誰啊? 再後來…… 她說“宮憫,你是不會笑,還是從來不笑?” 他看了她十息,展顏一笑“陌桑,若知道有一天我愛你勝過愛自己,一開始就不會浪費時間防備你、猜疑你,而是把所有的時間用來狠狠愛你,因為一輩子太短,我怕不夠愛你。” 陌桑咽著口水道“夫君,以後千萬別隨便笑,你一笑,人就變得好風騷……” 宮憫麵上黑,下一秒就露出一個魅惑眾生的笑容“娘子放心,為夫隻對你一人笑,隻對你一人風騷。” 某女瞬間流鼻血…… 【這就是一個白領精英穿越到異世古國,遇上高冷男神,被帝王捆綁在一起,相殺互撕,最後相親相愛、強強聯手、狼狽為奸的權謀愛情故事。】
187.7萬字8.18 335163 -
完結639 章

萬毒狂妃懷個寶寶來虐渣
她,本是藥王谷翹楚,卻因圣女大選而落入圈套,被族人害死。 一朝身死,靈魂易主。 楚斐然自萬毒坑中醒來,一雙狠辣的隼目,如同厲鬼蒞臨。 從此,撕白蓮,懲惡女,不是在虐渣,就是在虐渣的路上。 她醫毒雙修,活死人,肉白骨,一手精湛的醫術名動。 此生最大的志向就是搞到賢王手上的二十萬兵馬,為她浴血奮戰,血洗藥王谷! 不料某天,他將她抵在角落,“女人,你懷了本王的孩子,還想跑路?”
110.9萬字8 124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