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屋暗燈》 第54章 微博情人節520番外
宋星闌不配過人節。
宋謹和宋星闌在餐廳吃過晚飯后,回了鄉下。
今天也只是普通的一天而已,他們都是節日觀念很淡薄的人,更別提是520這種日子。
但兩個人還是出門吃了飯,往城外開車的時候,宋謹看到路邊有人在賣花,是個老,花旁邊還擺著菜,準確地說,應該是賣菜時順便賣賣花。
“在這里怎麼賣得出去。”宋謹坐在副駕駛,看著前路,說,“應該拿到人多的地方賣的。”
宋星闌停了車,降下了副駕駛的車窗。
他沒有說話,但宋謹知道是什麼意思,正好他也有這個想法。
于是他開門下車,蹲到老面前,問:“,玫瑰花多錢一支?”
“五塊。”老說。
在花店的玫瑰被炒上天價的這一天里,這個價格簡直令人順舌。
“我全買了吧。”宋謹把那捧玫瑰拿起來,不算多,二十幾支左右。
他上沒現錢,老的攤子上也沒擺二維碼,宋謹扭過頭,問:“有現金嗎?”
宋星闌沒說話,拿過車上的皮夾,了幾張紅鈔出來。
宋謹起拿了錢,然后塞到老的手里,說:“謝謝您,那我們就先走了。”
Advertisement
“多了多了……”老著急地站起來,“哪里要這麼多……”
“花店里買這麼一束,比這還貴呢。”宋謹朝笑笑,然后上了車,說,“您拿著吧。”
宋星闌車子開得毫不猶豫,轉眼就駛出了一大段距離。宋謹抱著花,這捧玫瑰什麼都沒有,沒有包裝,沒有帶,赤的一整束,散發著植的青味道。
“拿回家起來,說不定能養活幾。”宋謹看著懷里的玫瑰,“很新鮮。”
“嗯。”宋星闌應了一聲。
“葡萄柚一個人在家里,也不知道怎麼樣了。”才出來一頓飯的時間,宋謹已經開始心葡萄柚的生存狀況。
“不是一個人。”宋星闌說,“是一只貓。”
宋謹無語。
初夏的風很怡人,宋謹看著窗外飛速劃過的風景,說:“上次回去的時候,劉叔說地里的玉米快了,今天應該能摘幾嘗嘗。”
“哦,還有。”宋謹憋著笑,說,“還到小強和大俊了,問我你去哪里了,他們還等著你帶他們打籃球。”
宋星闌面無表地目視前方,說:“太菜,帶不。”
“你還真好意思跟他們比?”宋謹笑起來,“還有你麻將桌上的牌友,問我你腦子好了以后,是不是打麻將打得更厲害了,我說我不知道。”
他轉過頭,問宋星闌:“你現在還會打麻將嗎?”
良久,宋星闌說:“不知道。”
宋謹笑得肩膀都在抖,他是真的覺得好笑,宋星闌當時失憶的時候,宋謹沒覺得哪里好笑,但是現在把兩個人一對比,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非常好笑。
宋星闌轉頭看他一眼:“笑什麼。”
“沒什麼。”宋謹了笑意,說,“我沒笑。”
宋星闌又看他一眼。
到了鄉下,天有點暗了,宋謹跟宋星闌去了山坡上的菜地,宋謹心滿意足地摘了玉米和菜,準備帶回城里吃。
房子里許久沒住人,有些生灰了,宋謹去房間收拾書和資料,宋星闌在院子里站了會兒,然后去了二樓。
宋謹收拾好之后沒在外面見到人,于是也上了二樓,看見宋星闌站在落滿灰塵的書架前,正在翻看著什麼。
那是當年的判決書,母親和宋向平的離婚司,母親爭取過宋星闌的養權,可惜敗訴。
聽到腳步聲,宋星闌回過頭,和宋謹對視。
“我沒騙你。”宋謹說,“媽媽當時,是想帶你走的。”
“我知道。”宋星闌回答。
然后他把判決書放回了屜里,和宋謹一起走出了屋子。
天黑了,月亮的廓漸漸清晰,星約閃爍,宋謹問:“去天臺看星星嗎?”
宋星闌沒說話,握著宋謹的手,往去向屋頂的小樓梯那邊走。
地面干燥,兩個人干脆就這麼坐下了,距離上次這樣坐在一起,宋謹都記不清已經過去多久。
他以為不會再有這種機會了的。
宋謹看著天空,說:“不知道葡萄柚……”
宋星闌轉頭看他。
宋謹識趣地截住話題,轉而說:“星星好像又變亮了。”
“天黑了。”宋星闌說。
“你還記得嗎,之前有一次,沒月亮,那天晚上星星特別特別亮。”
宋星闌:“不記得。”
他確實不記得,因為他失憶的時候,每次和宋謹一起看星星,他都沒有抬頭看過天空,目里永遠只有邊的那個人。
他的哥哥就坐在旁,誰會在意那晚的星星有多亮。
宋謹皺了一下眉,說:“你現在在跟我裝失憶嗎?”
宋星闌很坦然:“確實不記得。”
宋謹扭過頭看著他,說:“那你現在好好看一看,記一下,下次我還要考你。”
宋星闌微微歪頭,朝宋謹湊近了一點,問他:“考我什麼?”
“……”宋謹的眼神飄了一下,“考你今天晚上的星星有多亮。
“有多亮?”宋星闌又問他。
宋謹不了地推了他一下:“你干嘛呢,說好了上來看星星的。”
宋星闌還是問他:“誰跟你說好了?”
宋謹回想了一下,他說上來看星星的時候,宋星闌確實沒說話。
他不知道兄弟倆之間居然還要搞這種嚴謹的話斗爭,這也太艱難了。
“不看那就下樓,回家。”宋謹說,“要不你就認真看。”
“在看了。”宋星闌說。
距離很近,他們自然地親在一起,許久之前的記憶與此刻重疊,宋謹突然覺得,好像也沒什麼不同,畢竟對方一直是他的弟弟。
甚至現在的宋星闌,比失憶時還要可靠一些,起碼他們在清醒地相。
那可能是,也可能是缺席已久的親,但已經不重要了,只要確定彼此無法分開,對于他們來說,就足夠了。
猜你喜歡
-
完結8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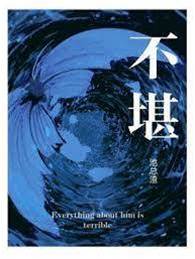
不堪
和他有關的所有事,都是不堪 【三觀不正,狗血淋頭,閱讀需謹慎。】 每個雨天來時,季衷寒都會疼。 疼源是八年前形如瘋魔,暴怒的封戚所留下的。 封戚給他留下了痕跡和烙印,也給他傷痛和折磨。 自那以后,和他有關的所有事,都是不堪。 高人氣囂張模特攻x長發美人攝影受 瘋狗x美人 封戚x季衷寒 標簽:HE 狗血 虐戀
20.2萬字8 6022 -
完結178 章

浮京一夢
蘭燭見到江昱成的那天,她被她父親帶到他面前,父親卑躬屈膝地討笑着,叫着對方江二爺。 江昱成隨意翻着戲摺子,頭也不擡,“會唱《白蛇》?” 蘭燭吊着嗓子,聲音青澀的發抖。 江二爺幫着蘭家度過難關,父親走了,留下蘭燭,住在江家槐京富人圈的四合院閣樓裏。 蘭燭從那高樓竹窗裏,見到江昱成帶回名伶優角,歌聲嫋嫋,酒色瀰漫。 衆人皆知槐京手腕凌厲的江家二爺,最愛聽梨園那些咿呀婉轉的花旦曲調, 不料一天,江家二爺自己卻帶了個青澀的女子,不似他從前喜歡的那種花旦俏皮活潑。 蘭燭淡漠寡言,眉眼卻如秋水。 一登臺,水袖曼妙,唱腔哀而不傷。 江昱成坐在珠簾後面,菸灰燙到手了也沒發現,他悵然想起不知誰說過,“青衣是夢,是每個男人的夢。” 他捧蘭燭,一捧就是三年。 蘭燭離開江家四合院閣樓的那天,把全副身家和身上所有的錢財裝進江昱成知她心頭好特地給她打造的沉香木匣子裏。 這一世從他身上受的苦太多,父親欠的債她已經還完了,各自兩清,永不相見。 江昱成斂了斂目,看了一眼她留下的東西,“倒是很有骨氣,可惜太嫩,這圈子可不是人人都能混的。” 他隨她出走,等到她撞破羽翼就會乖乖回來。 誰知蘭燭說話算話,把和他的關係撇的乾乾淨淨。 江昱成夜夜難安,尋的就是那翻轉的雲手,水袖的輕顫。 他鬼使神差地買了名動槐京蘭青衣的票場子,誰知蘭燭卻不顧這千人看客,最終沒有上場。 江昱成忍着脾氣走到後臺化妝間,看到了許久的不見的人, 幾乎是咬着牙問到:“蘭燭,爲什麼不上場” 蘭燭對鏡描着自己細長的眉,淡漠地說:“我說過,不復相見。” “江二爺,這白蛇,實在是不能再爲你唱了。”
28.1萬字8 1560 -
完結161 章

離婚那天,傅少跪在她裙邊求原諒
結婚五年,她以為自己可以焐熱傅宴禮的心,等來的卻是他的一紙離婚協議,他前女友的回歸更是成了壓垮她們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姜瑤看著朋友圈老公為前女友慶生的照片徹底的心灰意冷,主動簽下離婚協議成全他。傅宴禮不愛姜瑤,這是一個圈子里皆知的秘密,當年傅宴禮是被逼婚娶了姜瑤,所有人都為他鳴不平,等著姜瑤被休下堂,傅公子可以迎娶心上人幸福一生。 然而,真到了這一天,一向尊貴無雙的傅公子卻固執的拉住她的手,紅著眼卑微祈求,“瑤瑤,我知道錯了,咱們不離婚行不行?”
30.2萬字5 125 -
完結93 章

晚一點愛上你
穿著自己媳婦兒設計的西裝完成婚禮,季則正覺得自己計劃周全,盡在掌握。自從遇見她,記住她,他開始步步為營,為她畫地為牢。 帶著傷痛的她,驕傲的她、動人的她,都只是他心中的陸檀雅。 這一回陸檀雅不會再害怕,因為冥冥之中上天早有安排,錯的人總會離開,對的人方能共度余生。 “遇見你似乎晚了一點,但好像也剛剛好。”
26.4萬字8 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