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枝》 第36章
床幔里頭傳來窸窸窣窣的靜,聞恕時不時抬頭看一眼,坐在小幾旁兀自添了一盞茶。
他大抵能想象出里頭的人此刻的神,約莫是下不去手。
以打小學的規矩,這種事,足以面紅耳赤,難堪至極。
中間素心進來送過一碗藥,還沒從床上下來。
男人食指一下一下叩在桌案上,耐心降到最低時,嘩啦一聲,床幔終于揭開。
付茗頌耳通紅,抬頭看了他一眼,隨即匆匆地下,手里的藥盒仿佛燙手山芋,迅速放下,就著架上的一盆冷水洗凈了手。
十手指頭,洗得干干凈凈。
在梨木架旁來回徘徊,又停至床前,咬著,視線在地上掃了一圈,不知所措地看了那頭安靜喝茶的人一眼。
聞恕眉梢一提,“找什麼?”
茗頌走過去,猶豫地張了張口,聲音還略有些沙啞,“想換裳,要去給太后敬茶。”
聞恕準確無誤的抓住了“太后”二字,不由一頓,好心提醒:“該改口母后了。”
臉一白,像犯了什麼天大的錯誤似的,連連點頭,“是,臣妾記下了。”
聞恕倒沒要同計較稱呼的問題,又提醒,道:“現在已至亥時一刻,母后也歇下了,明日再去敬茶吧。”
這話猶如驚天雷,面前的人一雙杏眸忽然抬起,茗頌呼吸滯了一瞬,亥時一刻?
那豈不是誤了時辰給太后敬茶?
這新媳進門,哪怕是在尋常人家也十分講究敬茶的規矩,何況是在宮里。
從前在付家,就是晚半刻鐘給老太太問安,都要黑著臉晾好一陣,又遑論現下是誤了給太后請安?
聞恕掌心著藥碗,直至覺涼了些,正要坐下喝藥,手去拉的手腕,卻發覺手背涼得很。
Advertisement
他蹙眉,道:“很冷?去添件裳。”
他算是瞧出來,這人有多弱,再風一吹,指不定病到幾時去。
付茗頌心下那弦“噔”的一下斷裂,只覺得天都要塌了。
忍不住酸了酸眸子,滿臉小心翼翼地試探道:“母后…可有說什麼?”
聞恕疑地看了一眼,“說甚?”
茗頌猶豫地抿了抿,瓣輕,更加謹慎地著他。
男人雙眸一覷,頓時了然。
是怕這一病,未去永福宮敬茶,得罪了太后?
聞恕一句“你想多了”呼之出,可見神張,張之下還帶著些許慌張,忍不住又將話給咽了下去。
十五年在付家,該就是這麼過來的。
謹慎,小心。
“母后今日來瞧過你,沒生氣,明日你再去敬茶就是了,既已婚,便不在乎這些禮數。”他破天荒得多說了兩句。
聞恕敢這麼說,并不是太后不尊禮法,恰恰相反,沈太后曾經是個再重規矩不過的人了。
這些年他這個親兒子氣得沒了脾氣,才了如今這樣的好婆婆。
付茗頌一顆心回了肚子里,下意識吞咽了一下。
當真是嚇死了。
聞恕也不廢話,將人拉過來坐在上,遞上藥碗給,“喝了。”
茗頌手接過,可神卻十分不自然,十分的,僵。
雖說已行夫妻之禮,可卻并未覺得與他關系有多親,莫說坐大這種作,就是牽個手,都心下惶惶。
何況……
何況渾上下,只套了,里頭空的,連都沒有,昨日不知道他扔到哪里去了……
是以,上的人難地挪了下位置…
聞恕眉頭一蹙,虛虛扶在腰上的手催促地了腰間的,“別,喝藥。”
茗頌一駭,忙仰頭將藥喝下,一口都不帶停的,全然不懼苦味。
饒是如此,在喝完藥后,聞恕還是塞了一塊方糖給。
姑娘子一頓,許是頭一回喝完藥有人給喂糖,又驚又恐地瞥了他一眼。
隨即,聞恕拍了拍的腰,是要起來的意思。
又過片刻,宮送來嶄新干凈的,還有牙白寢。
須臾,付茗頌在這張龍床上躺下時,才發覺有哪里不對。
許是喝了藥的緣故,眼皮沉沉,昏昏睡,正當思緒快飄散,忽的睜開眼。
新婚頭夜宿景宮沒錯,可第二日,應回皇后的昭宮的。
—
帝后大婚,普天同慶,宮里仍舊張燈結彩,掛紅。
深宮許久未有這樣大的喜事,難得喜慶。
一般都言“新人笑,舊人哭”,可這皇宮里頭,卻沒人能稱上一句“舊人”的。
正因皇上未曾偏寵過誰,連爾虞我詐的手段都實在見。
人無數,無于衷。
貴人們默契地將此歸結于那幅眾口流傳的畫,有的當皇上深義重,有的,則當是那和大師給皇上下降頭了。
總而言之,誰都得不到圣寵,倒也公平。
又加之曾有不知好歹的妃嬪意圖近,卻全都落的個凄涼下場,久而久之,沒人再敢起這個心思。
可如今,立后頭一夜,景宮一夜了三次水的事兒傳開,原本沉寂的后宮,忽然心浮氣躁起來。
們這才知道,皇上也并非誰也不,并非不可近之人。
長夜難明,閣樓上飛來一只信鴿。
立在雕欄旁的子一不,宮見狀,只好親自拆了信。
“娘娘,二公子來信,說是…”宮蹙眉,頓了頓,“他前幾日遞了折子上去,未有回應。”
這意思便是,想到皇上面前點兩句。
魏時薇煩躁地撇開眼,這種事都不知是第幾次了,魏時均還真當有幾分本事,皇上不愿搭理他的折子,豈能喚得?
思此,抬眼往景宮的方向看去,“你說,皇后究竟有何本事,竟能做到如此?”
宮嘆氣,回頭將信紙條丟進燭火中,燃盡。
—
辰時,鳥鳴四起。
沈太后喝了新媳敬的茶,一臉溫和將人扶起,上下打量了一眼,“子大好了?”
付茗頌點點頭,稍一思索準備好的腹稿,輕聲道:“昨日沒能來給母后敬茶,是臣妾壞了規矩,母后恕罪。”
沈太后一笑,眼神瞥向氣定神閑坐在一旁品茶的罪魁禍首,拍了拍手背,“與你無關。”
聞恕眉頭輕提,角劃過一笑。
按例,沈太后備了贈新媳的禮,一番賞賜,一番謝恩,又是一炷香的時辰過去。
接著,沈太后給許姑姑使了個眼,許姑姑立即帶了個嬤嬤上前來。
約莫五十上下的年紀,在主子面前腰板都的這樣直,付茗頌不由多看了一眼,應當不是一般的宮人。
聞恕見此,便明白太后用意了。
還未等沈太后先開口,他便皺眉打斷,“朕已安排了人在昭宮伺候,無須母后費心了。”
沈太后便知他會這般說,挑眉道:“哀家挑的孫嬤嬤可不是伺候起居的,皇后年紀小,未經事,這宮中庶務總要一點點開始學,孫嬤嬤自哀家當皇后那會兒便陪著了,有在邊,皇后總歸能學得更快,待到那時,哀家也好歸還印。”
提到印,付茗頌臉也不由認真起來。
見聞恕還要再拒,沈太后哼了哼聲,提壺倒了盞花茶,慢條斯理道:“哀家掌管后宮數十年,這點,皇上的人便比不得。”
母子二人四目相對,誰都不讓誰。
這形,永福宮的人見得多,倒不當回事兒,太后和皇上常有爭執,但總歸有人先服。
有時是太后,有時,皇上也得退一步。
可茗頌沒見過這陣仗,被兩道視線夾在中間,一不敢。
須臾,無人開口,殿氣氛一滯。
“要不就……”忽然開口,引得左右二人皆看過來。
小姑娘嚇得又閉上,端端坐好子,目不知放哪兒好,索看向孫嬤嬤,一本正經道:“臣妾瞧著,孫嬤嬤好,合眼緣,我喜歡的。”
左側的一道目落在臉上,付茗頌有意躲開,偏了偏頭,“謝過母后。”
沈太后一愣,旋即角上揚,拿起茗頌扣在腹前的小手,“哀家就知道,你是個好孩子,懂分寸,明事理。”
說罷,沈太后往后睨了一眼,“既如此,便讓孫嬤嬤帶你到室拿歷年記載的典錄,先從六局二十四司瞧起,東西二宮庶務,多經由此。”
付茗頌一看便知太后有話要同皇上單獨說,想也不想便點頭應下,起隨孫嬤嬤往室去。
眼瞧影走遠,沈太后微微一嘆,“皇上立的皇后,倒是個十分乖巧的。”
聞恕往室瞧了眼,“慣不會拒絕人。”
“怎麼,皇上覺得哀家欺負了?”
“兒臣不敢,只昭宮的人都已安置好,大可不必將孫嬤嬤放在前。”
沈太后側目瞧他,撐著子緩緩起,給籠子里那吱吱的鳥兒扔了幾顆花生米,語氣悠長,“讓你的人教,皇上舍得教?孫嬤嬤雖嚴,可嚴師出高徒,哀家能將當兒媳疼,可哀家,難不還能替掌管一輩子后宮?”
聞恕垂眸,他自然知道太后所言不錯,否則方才,便也不會退那一步。
“這皇后,不僅是你的皇后,還是大楚的皇后,那麼多雙眼睛盯著,不可出差錯,你就是心疼,也只能瞧著。否則你當初便不該立為后,抬個妃位進來放在邊疼著不就了?”
半響,他抿了抿,“母后說的是。”
—
艷高照,宮撐傘在一旁。
聞恕見孫嬤嬤隨在后,手里抱著比他書房的折子還高的典錄,大抵能想到后頭幾月得吃多苦。
驀地,他冷冰冰彎起角,“朕今日可是幫過你,是你自個兒要逞強的。”
茗頌腳步一滯,以為他是生氣了,聞言低下頭,也不敢說話。
走出好幾十步,才又仰起臉同他道了個謝。
那個生分。
聞恕這樣無意堵了一下,臉更難看了。
作者有話要說:
茗頌每天:
“臣妾不敢”
“皇上恕罪”
“謝皇上”
皇上日常被氣死
猜你喜歡
-
完結847 章

穿書後,我嬌養了反派攝政王
(章節內容嚴重缺失,請觀看另一本同名書籍)————————————————————————————————————————————————————————————————————————————————————————————————————棠鯉穿書了,穿成了炮灰女配,千金大小姐的身份被人頂替,還被賣給個山裏漢做媳婦,成了三個拖油瓶的後娘!卻不曾想,那山裏漢居然是書里心狠手辣的大反派!而那三個拖油瓶,也是未來的三個狠辣小反派,最終被凌遲處死、五馬分屍,下場一個賽一個凄慘!結局凄慘的三個小反派,此時還是三個小萌娃,三觀還沒歪,三聲「娘親」一下讓棠鯉心軟了。棠鯉想要改變反派們的命運。於是,相夫養娃,做生意掙錢,棠鯉帶着反派們把日子過得紅紅火火!後來,三個小反派長大了。一個是位高權重當朝首輔,一個是富可敵國的大奸商,一個是威風凜凜的女將軍,三個都護她護得緊!當朝首輔:敢欺負我娘?關進大牢!女將軍:大哥,剁掉簡單點!大奸商:三妹,給你遞刀!某個權傾朝野的攝政王則直接把媳婦摟進懷。「老子媳婦老子護著,小崽子們都靠邊去!」
145.2萬字8.33 120041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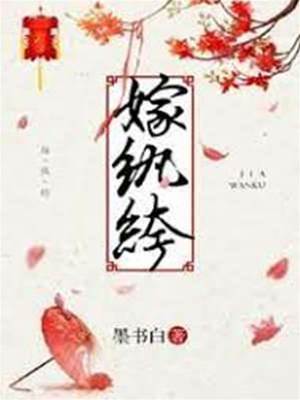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2012 章

戰神王爺是妻奴
一朝穿成被人迫害的相府癡傻四小姐。 從死人堆里爬出來,隨身攜帶醫藥實驗室和武器庫。 對于極品渣渣她不屑的冷哼一聲,迂腐的老古董,宅斗,宮斗算什麼? 任你詭計多端,打上一針還不得乖乖躺平! 絕世神功算什麼?再牛叉還不是一槍倒! 他,功高蓋世,威震天下的戰神王爺。 “嫁給本王,本王罩著你,這天下借你八條腿橫著走。” “你說話要講良心,到底是你罩我,還是我罩你呀?” “愛妃所言極是,求罩本王。” 眾人絕倒,王爺你的臉呢?
362.3萬字8 380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