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路敵國皇帝后我懷崽了》 34
“……”謝遮心里咯噔一聲,“陛下恕罪。”
一個小太監慌慌張張地沒端穩洗臉水,水濺到皇帝上了,登時跪下來連聲求饒。
蕭昀不耐煩道:“都給朕滾!”
宮人們如蒙大赦,魚貫而出。
蕭昀還是知曉輕重的,沉聲問:“什麼事?”
謝遮說:“長公主府上的眼線來報,說祁王忍無可忍準備對謝才卿下殺手了。”
蕭昀:“什麼時候?”
“謝才卿今日去翰林院報道,按理說就是這兩日。”
“昨夜祁王邊的書找到了張寧翰,張寧翰連夜去了長公主府,一個時辰后才出來,還是笑著出來的,除了張寧翰,祁王的人還找了當初逸仙樓那個被謝才卿罵的抬不起頭的書生,同時私下收買了不那日在逸仙樓的百姓。”
蕭昀一哂:“倒是想的齊全,也是豁出去了,朕這個當舅舅的,可不得再助他一臂之力。”
“你給老張帶句話,他以他的名義私底下給祁王寫封信,大致意思是求祁王得饒人且饒人,他不是正愁找不到夫麼,朕把夫送到他手上。”
“……”謝遮滿臉不可思議地看著他。
蕭昀一笑,謔道:“看朕作甚?朕可真是個好舅舅。”
謝遮:“……張公都七十多了,陛下要不換一個稍年輕點的?”
蕭昀聳聳肩:“可以啊,指揮使如何?反正對朕沒差。”
“……那還是張公吧。”
正事兒說完了,謝遮又往龍床上瞧了眼,咳了下,低聲問:“……小白兔呢?”
Advertisement
蕭昀轉頭瞪他,冷冷道:“誰讓你喊的?”“……微臣失言!”謝遮面不改,“陛下的小白兔呢?”
蕭昀嗤笑:“他可不是朕的。”
謝遮一愣,輕聲道:“昨夜他……他沒有……”
“有啊,”蕭昀皮笑不笑,“在榻上呢,你去找找。”
謝遮嚇了一大跳:“他在啊?!”
謝遮看向糟糟宮人還沒來得及整理的被褥,那里說不定還真藏個人,畢竟謝才卿這麼瘦。
“在。”蕭昀欣然點頭,用眼神鼓勵他去,“還沒起呢,你順便可以它起來。”
“……”謝遮搞不懂什麼況,只能遵命慢吞吞地走到龍榻邊,僵著手指掀了點被子,生怕看到個渾赤的狀元郎。
蕭昀在背后面無表。
謝遮做好心理建樹,提心吊膽地將被褥翻了一整遍,都沒瞧見人,一頭霧水地回頭看皇帝。
“看不見麼?就在你手邊,陪了朕一夜了。”
謝遮又轉回頭,看向空空如也的床鋪,目最后緩緩落向了枕頭邊躺著的那個黑金的香囊。
“…………”謝遮表有幾秒凝固了,麻溜地轉,單膝跪下了,“微臣有罪!微臣昨日不該胡言語多加揣測!”
“起來起來。”蕭昀也就跟他開個玩笑,不至于遷怒他,在一邊兒不耐煩地套著朝服。
謝遮兩手托著“謝才卿”磨磨蹭蹭來到了蕭昀邊,憋著笑:“他……他怎麼說的啊?”
怎麼會這樣?
這和他猜的差的可不只十萬八千里。
蕭昀“呵”了一聲:“他夸朕是君子,坐懷不,不僅沒趁人之危,還慷慨施藥相救,是他的救命恩人,天氣漸熱,他怕朕被蚊蟲咬了,親手做了個香囊送給朕。”
“禮輕意重,他主要想說,他激萬分,日后也會想方設法一點點報答朕的恩。”
“朕剛吼他要問呢,他自己先答答地跑了,送個香囊,屁大點事,得跟要獻似的,老子也是醉了,誤會了這能怪朕麼?”
“……”謝遮目瞪口呆。
這不僅沒順水推舟,還莫名其妙把話說死了,把所有的可能都掐沒了,他是一點兒這意都沒。
謝遮憋笑,鼻子:“陛下君子。”
“滾你媽的!”蕭昀笑罵,一腳踹了過去。
謝遮躲了躲:“那陛下打算如何?”
“什麼如何?”蕭昀沒好氣道,“朕就稀罕他?圖個樂子罷了,他沒這意,朕還要強迫他不?朕要真好這口,比他聽話懂事的多得是,用得著犯賤?他以為他是誰?隨他去。”
“陛下圣明!”謝遮想了想,過了一會兒說,“他也不是像是個傻的,可能還是太小,臉皮太薄,得慌,也沒往這邊想過,不過他不走這捷徑,他準備如何對付祁王?總不會自己一個——”
“誰想知道?”蕭昀穿好龍袍,甩袖風馳電掣地出去。
謝遮腦子里飄著尹賢那句“陛下龍虎猛、一柱擎天”,憋著笑,是難忍的。
第26章
第二天,江懷楚到翰林院報道,一起的還有新科榜眼和探花,職是正七品翰林院編修。
江懷楚翰林院修撰,六品,太小,除非皇帝特召,平時用不著上朝。
前輩領著三人在各個館和房里走了走,介紹悉了下,將三人領到事先已分配好的差使上。
江懷楚是修撰,按理來說初來乍到只能修修實錄,閱覽舊人草擬文稿學習,卻未承想直接被翰林大學士劉韞帶在邊,給他打下手。
一路寒暄下來,對謝才卿,翰林們基本都是不冷不熱的態度,儼然是準備先觀一段,也有不世家出的,眼里流出一不屑。
榜眼和探花瞧著謝才卿被人笑著引進了劉韞一人獨占的清風館,對視一眼,各自不忿地低下了頭。
劉韞見謝才卿進來,心道了聲風霽月,朗笑道:“別拘謹別拘謹!”
謝才卿含著三分淡笑點頭,尊敬而不失親昵道:“師傅。”
劉韞心下一暖:“好好好!”
“你這一個月幫襯著我點兒就行,你那麼聰明,也不肖我教什麼,多看多做,不懂直接問,別不好意思,我去哪兒你跟著就行,我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聽見沒?”
謝才卿點點頭。
“咱們是清水衙門,撈不到什麼銀錢,但日子好混,不過我不許你混,每天要檢查你進度,你還要多讀書,我會給你布置任務,完不還有罰,能接嗎?”劉韞暗中打量著他,刻板道。
謝才卿乖巧地點點頭,暗中有些疑為什麼劉韞對他那麼好且嚴格。
劉韞滿意地捋了捋胡子,果真不是個急功近利、傲氣凌人的,好好打磨,日后必大,又端方矜守,外頭并無毫浪行跡,規矩得很,仔細觀察一兩月,若無問題,贅做他的乘龍快婿再好不過。
劉韞指著桌上的一摞書和文稿:“今日值房那邊我當差,你待會兒抱著這堆東西跟我一道去便是。”
翰林院離皇帝寢宮很遠,翰林是天子近臣,為了方便皇帝用人,寢宮邊上不遠設了值房,翰林流去值房當差,隨時聽候皇帝命令。
謝才卿沒想到這麼順利,微笑點頭。
……
午間,蕭昀和張公謀往值房去,一個和悅,一個面有難。
面有難的張公不停抹汗:“陛下,這……老臣,這……”
“朕還能忽悠你不!”
“不……不是……只是……狀元郎和老臣……”
蕭昀不耐煩道:“別可是但是的了,辦好了朕許你告老還鄉頤養天年。”
張公眼睛一亮,沉默片刻,依然有些慌張:“陛下,你且給老臣個底,那玉到底是誰的啊,老臣也好安……安個心啊。”
蕭昀臉上笑意一閃而過:“你管呢,讓你辦你就給朕辦,哪那麼多廢話,好不了你的,別猴猴的。”
“……是。”張公著頭皮應下。
猜你喜歡
-
完結1291 章
寵婚撩人:總裁私寵小甜妻
"老公,今天有人和我表白."總裁大人眉眼輕挑,十分鍾後,某人就被套麻袋了. "老公,聽說李小姐從南非帶回來一顆鴿子蛋大小的彩鑽,戴在手上可好看了."總裁大人手一劃,一張天價支票立馬就出現在了曉童的手裏,"乖,老婆,有什麽需要的盡管找老公,老公不缺錢." "老公,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了一個大帥哥."某女眼冒小星星. "什麽?你居然敢看我以外的男人?"總裁大人聞言暴跳如雷,扒光衣服就準備行使自己作為丈夫的權力. 在她看來,外人眼裏冷峻無情,鐵腕狠絕的男人是完完全全隻屬於她一個人的
119.2萬字8 55144 -
完結83 章

回眸一笑JQ起
某日,天氣晴朗,難得兩人都在家,隨憶坐在電腦前悶著頭搗鼓了很久都沒動靜,蕭子淵看完最後一份檔走過去問,“你在幹什麼?” 隨憶抬起頭皺著一張臉抱怨,“我的狗病了!不會叫了!” 蕭子淵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奇怪的問,“哪裡有狗?” 隨憶指著電腦螢幕上的某軟體,“酷狗!不出聲音了!” 蕭子淵苦笑,他當初到底是怎麼看上這個不按照常理出牌的姑娘的啊? 若干年後隨憶早已不記得當初蕭子淵為什麼會看上她,可是她卻記得他曾深情而鄭重的在她耳邊對她說。 某人,我要讓你在我身邊,倡狂一輩子。 那一刻隨憶心中一動抬頭去看那雙清涼的眸子,眉梢溫婉。 這是個腹黑淡定男和大氣溫婉女的溫馨故事。
21.2萬字8.33 9193 -
完結163 章
春日信徒
驚蟄從小和奶奶住在鄉下山里頭,一身淳樸,要上高中的時候,被林叔叔接到了城里,去上重點中學,希望她給他門門掛紅燈的兒子做陪讀,幫助他好好學習。大城市很多車,樓很高,驚蟄很不適應,但一心記著要幫林驍。林驍打架她遞掃把。林驍記過她寫檢討。林驍餓了她煮飯。時髦值點滿的林驍看著她穿著奶奶款碎花襯衣,復古到不行的牛仔褲,在花園里種花生,拿蒜苗當盆景,自己給自己織毛衣,還試圖給他破洞牛仔褲縫布貼……認真說:“你別喜歡我,咱倆不合適。”驚蟄疑惑看著他,緩緩點頭。有學長跟驚蟄表白,驚蟄搖頭說不能早戀,但學長溫柔說,我們可以做朋友,驚蟄答應了,她給朋友寫作業,還給朋友送自己手織的圍巾。林驍越來越覺得不對味兒,有一天忍無可忍的林驍扯住驚蟄,“你在報復我?”驚蟄困惑看他,“嗯?”林驍問她,“你喜歡他哪里?”驚蟄想了想,“他長得好看,人也好,還喜歡我送的東西。”第二天,走在時尚尖端的林少爺,穿了一條中規中矩的直筒牛仔褲,襯衫嚴謹系到最上頭,拿著她送的環保手袋,抿著唇說:“我不比他長得好?”驚蟄依舊困惑看他,“你最近怎麼了?”林驍沉默了足足十秒鐘,“我想把花園的玫瑰拔了給你種花生。”驚蟄眼睛一亮,“真的可以嗎?”林驍表情嚴肅,“但你知道,城里地很貴的。我那塊兒地給我老婆留的。”驚蟄:“……”
25.2萬字8 4143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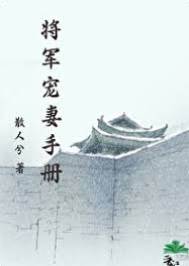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
完結159 章

她有七分甜
徐睿好覺得她和翟璟陽從小到大都互看不順眼。 上大學后,兩個人分別選了不同的專業。 徐睿好樂得自在,該吃吃該喝喝,抽空還幫室友牽線搭橋追男朋友,把翟璟陽忘在了腦后。 翟璟陽卻主動找過來,在宿舍樓下攔住她,質問道:“你是不是變心了?” “不行,你只能喜歡我一個。”
27.5萬字8 5876 -
完結254 章

炙火難熄
一場被家族安排的婚姻,盛焱心有所屬,若初心知肚明。 婚後第一年,他拋下她前往國外工作,兩人一年見不上幾次面; 婚後第二年,聽說他在國外玩得很花,她追去過國外,親眼見證他與金髮碧眼俏女郎打得火熱。 看看她難過,他卻惡劣笑道:“初初,既然我們都瞧不上彼此,又左右 不了婚姻,不如開放,各玩各的?” 婚後第三年,他宣佈工作重心調回,同時也帶回來一個與他舉止親密的女孩。 他的朋友說,這一次,焱哥是認真的。因爲那個女孩,像極了他心裏的那個人。 一場有名無實的婚姻,若初想,曾經她與盛焱哥哥那些細指可數的美好,大概早已揉碎在在這段荒誕的關係中。 而她,本是嬌豔玫瑰,不該成爲一朵日漸枯菱的花。 向父母求來離婚那天,她說:“盛焱,如你所願,以後你玩你的女人,我玩我的男人,我們互不相干。” 後來,有狗仔拍到,國外的某處度假海灘,周家大小姐周若初與國內新晉頂流小生在無邊泳池溼身戲水的香豔畫面。 次日凌晨,盛焱空降同一酒店,狠狠地將人堵在房間裏,紅了眼說着最卑微的話,“初初想玩男人,何必捨近求遠?哥哥給你玩!”
44.1萬字8 142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