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縛龍為后》 115
“夫妻一場,我從未后悔過。”
燕鳶僵地走過去,看著寧枝玉手中兩紋路相同的銀簪:“……哪支是后來給你的?”
頃,寧枝玉將右手中的銀簪遞了出去,燕鳶抬手輕輕接過來,視線被熱霧模糊。
后來寧枝玉還說了什麼,燕鳶都沒注意聽了,他拿著簪子回了乾坤宮,一路上未置一詞。
可以想象玄龍在買下這簪子時的心。
他必定是看見了什麼,看見他送了這簪子給寧枝玉,然后去買了一模一樣的。
那日乞巧節,真是格外熱鬧……現今想起來,還是覺得熱鬧,放眼四周卻是清冷冷的一片,玄龍當時的心境應當便是同他現在這般吧。
他將玄龍的深不悔作為嘲笑的話柄,將竊嫉妒的污名強加給他,哪知道那龍其實就是想將著他的那顆心藏起來,免去被他踐踏而已。
偏偏他惡劣到至極,非要他難堪,非要將他的尊嚴弄碎。
燕鳶抬頭向白茫茫的天。
今日又下了雪。
真冷。
……
鸞殿。
“再過半月,本尊的便能重現人間了,你當真不跟本尊走?”
殿中宮人退盡,從孩子生出來,寧枝玉便沒看一眼,他躺在床上,神是超悲傷的平靜。
“不走。”
“你寧愿住冷宮,也不愿跟本尊走?”腦中那聲音暴躁起來。
“這里是我家。”寧枝玉輕聲說。
“你果真狠心……連你自己的孩子都不愿看一眼。”
寧枝玉著上方的空氣:“我看見他,便想到你,覺得惡心。”
Advertisement
這句話功讓魔尊閉了。
過了一會兒,寧枝玉問:“如何破解魔蠱。”
魔尊低沉的聲線中含戾氣:“無法破解。”
寧枝玉雙手攥上被褥:“你說過,魔蠱不會對他的造傷害,你騙我……”
魔尊冷笑一聲:“是,原本的確不會造傷害。誰他重新上了玄龍,移別自得遭反嗜。”
“你難道不該高興?”
燕鳶的頭疾日漸加重,若再這樣下去,恐怕會活活病死。寧枝玉咬牙,道:“……你幫他解了蠱,我便跟你走。”
“可真是天地的。”
“本尊聽了都要流淚了。”
……
三年后。
日暮西沉,月上樹梢,小小的人兒獨自坐在乾坤宮外的臺階上,雙手放在膝頭,仰頭盯著上空那皎潔的玉圓盤看。
他一襲青綠的小錦袍,臉蛋白,頭頂生兩短的黑小角,綠瞳映著月,妖異漂亮。
旁邊有太監跑過來,彎著子問道:“小殿下,您怎麼啦?”
“大晚上的,怎得坐這里來了?快跟奴才進去吧,小心著涼……”
小人兒愣了愣,垂頭道:“父皇又喝醉了。”
父皇一喝醉,便要抱著他哭,對著他喊娘親的名字,哭得很傷人。
他不想父皇傷心。
“這……”太監猶豫一瞬,道。“那小殿下去勸勸皇上,他喝些,酒多傷。”
“旁人的話啊,皇上都聽不進去,他就聽小殿下的。”
燕執小聲道:“可是他看見我,便會更加傷心……”小手有一下沒一下摳著臺階隙中長出的雜草,仰頭看向太監,眼角泛紅:“娘親到底什麼時候回來啊……他不要阿執和父皇了嗎?……”
太監:“要的,小殿下這般可,皇后娘娘怎會不要您呢,他只是暫時離開了。”
“待小殿下長大之后,他便會回來了。”
寧枝玉被廢黜后位之后,燕鳶追封了新后,那新后便是太子的生母,寒泊。
眾人都知曉太子是帝王與一條龍生下的,從前妖邪妖邪地喊著,燕鳶派人坊間的說書人編纂了本有關玄龍舍救他命的書,每日在茶樓院大肆宣揚,這妖誕下的太子便了真龍天子轉世,綠瞳和龍角便是最好的證明。
帝王與玄龍相知相遇相以及生子的過程,漸漸為了一段佳話。沒有人會因此嘲笑阿執生得與眾不同,他被燕鳶寶貝似得疼著,在宮中活得天真快樂,唯一的煩惱就是娘親遲遲不回來。
待娘親回來了,他們一家團聚,父皇就不會總是流淚了,他也不用躲在被窩中想念娘親,還不敢父皇知道了。
“真的?……”
“那阿執要快些長大。”
太監蹲在小人兒邊,笑得滿臉褶皺:“自是真的。”
“那小殿下,現在可愿意跟奴才進屋了?”
燕執點點頭:“嗯……”
太監傾將小人兒抱起,送進了殿門。
“父皇……你答應過阿執的,要喝些酒。”
殿昏暗,羅帳高懸,長發披散的男子側倚于榻上,手中提著玉壺仰頭往口中倒酒。他白皙的面容著病態的蒼白,眼尾酡紅,聞言,醉眼朦朧地扭頭看過去,拎著酒壺的手臂垂至床沿,朝小人兒出手,含糊不清地吐著酒氣。
“阿執……”
“你去哪兒了,父皇好找。”
小人兒朝燕鳶走過去,停在床邊,抬起小手抹了抹燕鳶眼角的淚,小聲回:“阿執就坐在門外。”
“阿執不喜歡父皇喝酒。”
“今日是中秋節,父皇高興。”燕鳶笑了笑,將小人兒從床便抱起來,看著搖搖晃晃的,實際上格外穩。
阿執知道中秋是團圓節,他聽宮人說過,團圓節便是要一家人在一起開開心心地吃飯。阿執在燕鳶懷中轉了個,小胳膊環住燕鳶脖子,悶悶道:“父皇不哭。”
“嗯,父皇不哭。”燕鳶大掌覆在他小的背脊上,將臉埋進他頸間。“父皇不哭……”
他上說不哭,阿執卻覺到頸間有熱的淚意,環抱著自己的在不斷發,阿執低低喚了句父皇,燕鳶忽得哽咽出聲。
阿執見他哭,便也忍不住要哭,父子倆抱在一起哭一團,燕鳶口中說著他聽不懂的話。
“父皇對不起你……”
“阿執……父皇對不起你。”
大太監說,待他長大,娘親便會回來與他們一家團聚了。可他還未來得及長大,父皇便病倒了。
燕鳶的頭疾五年如一日地發作,他看似活著,實則就是一行尸走,強撐了五年,終是撐不住了。
父皇離開的那日,阿執守在他床前,握住他的大手哭得撕心裂肺:“父皇,你不要離開阿執……”
“你不要離開阿執……”
即便燕鳶從前做過再多錯事,但在小小的阿執眼中,父皇便是為他撐起天地的棟梁,他沒見過娘親,唯有父皇。
父皇的手那樣大而有力,可以輕易將他抱起來舉高,父皇的手很溫暖,他覺得安心。可為何父皇的手會變得那麼涼,涼得他害怕。
床榻上的人形枯瘦,目無彩,京城第一男的稱號再不適用于燕鳶。他今年不過二十五,便蒼老得好似垂暮之年行將就木的老者,半點生息都無。
燕鳶半瞌著眸看著床邊的小人兒,他的阿執沒比床沿高出多,哭得可憐,人心疼。
“阿執……父皇,是去尋你娘親,你莫要哭……”
小人兒哭著搖頭,雙手用力抓著燕鳶的大掌:“那父皇帶上阿執一起,阿執也要去……”
燕鳶氣若游地笑:“阿執乖……跟你花姨出宮去,會陪著你。”
“待阿執長大了……父皇便同娘親一起,回來看你……”
第一百零九章 天帝復位
阿執雖小,生來早慧,他約知曉父皇是在哄騙他的,若娘親真的那麼容易回來,哪里會他和父皇等那麼久。
猜你喜歡
-
完結239 章

替身受假死之后
許承宴跟了賀家大少爺五年,隨叫隨到,事事遷就。 哪怕賀煬總是冷著臉對自己,許承宴也心甘情願, 想著只要自己在賀煬那裡是最特殊的一個就好了,總有一天自己能融化這座冰山。 直到某一天,賀煬的白月光回國了。 許承宴親眼看到,在自己面前永遠都冷淡的男人,在白月光面前卻是溫柔至極。 也是這時,許承宴才知道自己只是一個替身。冰山是會融化的,可融化冰山的那個人,不是自己。 狼狽不堪的許承宴終於醒悟,選擇放手,收拾好行李獨自離開。 而當賀煬回來後,看到空蕩蕩的公寓,就只是笑著和狐朋狗y打賭:不超過五天,許承宴會回來。 第一天,許承宴沒回來。第二天,許承宴還是沒回來。 一直到第五天,許承宴終於回來了。只是賀煬等來的,卻是許承宴冷冰冰的屍體,再也沒辦法挽回。 三年後,賀煬依舊是那個高高在上的賀家大少爺。 在一場宴會上,賀煬突然看見了一道熟悉身影。賀煬失了態,瘋了一樣衝上前,來到那個黑髮青年面前。 “宴宴。” 向來都冷淡的賀家大少爺,此時正緊緊抓著青年的手不放,雙眼微紅。 “跟我回去,好嗎?”而耀眼的黑髮青年只是笑著,將男人的手移開。 “抱歉先生,您認錯人了。”渣攻追妻火葬場,1v1。 受假死,沒有失憶。假死後的受一心沉迷事業,無心戀愛,渣攻單方面追妻。
50.5萬字8.18 51834 -
完結16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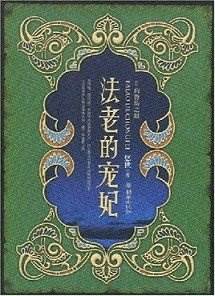
法老的寵妃
埃及的眾神啊,請保護我的靈魂,讓我能夠飛渡到遙遠的來世,再次把我帶到她的身旁。 就算到了來世,就算已經過了好幾個世紀,我和她,以生命約定,再相會亦不忘卻往生…… 艾薇原本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紀英國侯爵的女兒,卻因為一只哥哥所送的黃金鐲,意外地穿越時空來到了三千年前的古埃及,而那只黃金鐲就此消失無蹤。艾薇想,既然來到了埃及就該有個埃及的名字,便調皮地借用了古埃及著名皇后的名字——「奈菲爾塔利」。 驚奇的事情一樁接著一樁,來到了古埃及的艾薇,竟還遇上了當時的攝政王子——拉美西斯……甚至他竟想要娶她當妃子……她竟然就這麼成為了真正的「奈菲爾塔利」!? 歷史似乎漸漸偏離了他原本的軌道,正往未知的方向前進……
71.2萬字8 5714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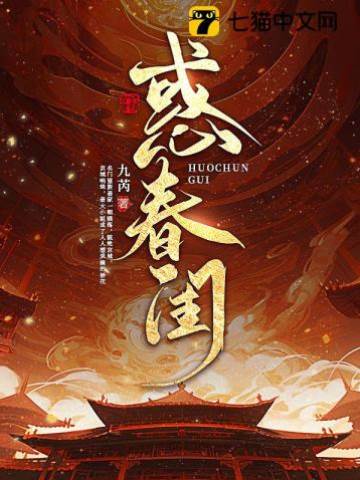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85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