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縛龍為后》 75
“我亦覺得,我真是可悲極了……”不僅可悲,且低劣,無恥,若魔尊所說無假,他便是霸占了屬于別人的東西,鳩占鵲巢,死后定會墜無間地獄。
可那又如何,他已回不了頭了。
青梅著急道:“那是因為皇上心疼您。”
寧枝玉合上雙眼,蒼白的輕。
“我累了,你且退下吧。”
青梅如來時那般悄然出去了。
殿安靜下來時,腦中響起悉的魔音。
“可笑,你不會以為模仿玄龍的穿束,就能變玄龍了吧?”
寧枝玉掀開眼皮,低聲回:“與你無關。”
魔尊冷哼:“他不你有那麼重要嗎?”
“你為何這般賤,好端端的一個男人,非上趕著雌伏于另一個男人下,還地要給他生孩子,你腦子沒生頑疾吧。”
寧枝玉重復:“與你無關。”
“愚蠢的人族。”那低沉的聲線聽起來有些惱怒,若是魔尊能現形,說不定會出來暴打他一頓。
“你簡直蠢笨至極……無可救藥。”
寧枝玉屬實覺得累了,緩慢地掀開被子側躺下去,安安靜靜地就要睡。
那聲音聲氣地說。
“本尊不允許你這麼做。”
“聽到沒!!”
寧枝玉到莫名其妙:“與你有何關系。”
對方加重語氣:“本尊如今附于你,并沒有看活春宮的好。”
“你可以暫時離開我。”寧枝玉平靜道。
“你——”
寧枝玉能清晰地覺到魂魄的憤怒,魔尊本就這樣反復無常,他早已見怪不怪,太過虛弱,不多時便陷了沉睡。
Advertisement
……
清早,殿外烏云布,眼看著要下雨,燕鳶起床被人伺候著穿上龍袍,帶上玉珠帝冕后,回到床榻邊,掀開明黃的羅帳。
玄龍還在睡,臉看著并沒有比昨夜好多,寧枝玉那邊昨夜就沒有藥引了,怕是不能再拖了,燕鳶思慮片刻,傾過去晃他的肩膀。
“醒醒。”
幾息后,玄龍茫然地睜眼。
燕鳶輕咳一聲,著男人冷峻的臉:“腹中還疼麼。”
玄龍間發燙,好似有火在燒,四肢百骸傳來酸痛與無力,他撐著床坐起,不是很想理對方,但還是搖了搖頭。
他知道被當作空氣的覺有多難。
燕鳶面有些不自然:“阿玉的龍鱗用完了。”
玄龍垂著眸,消瘦的背脊微弓著,長發半遮半掩地出削薄的膛,潔的皮上散落著青紫的吻痕,被褥所蓋的位置恰好擋住隆起的腹部。他的手臂上,后心口,還殘留著上回拔鱗時留下的傷,結了大塊的暗紅痂,到現在都沒好。
寧枝玉一日要服三片龍鱗,一次給出三十片,不過十日便沒有了,傷口愈合的速度遠遠比不過拔鱗的速度。
玄龍聲線沙啞:“槲樂還在牢中。”
燕鳶面一變,怒火翻涌:“你又要用他與我談條件?”
玄龍悶悶說:“我救他,本就不該是天經地義。”
從前是因為他以為燕鳶與他兩相悅,既了,為他看重的朋友拔些龍鱗又有什麼。后來是因為反正他已命不久矣,不想計較太多,只要燕鳶高興便好。
等他走后,燕鳶還要辛苦育他們的孩子,龍鱗便當作報酬。
可如今……
燕鳶冷笑著點頭:“好,這回我要一百片,你一次給我,我就將他放回你邊。”
玄龍:“好。”
沒想到男人會這樣平靜地答應,燕鳶愈發怒火中燒,本是逞口舌之快,如今已收不回來。
“等我下朝回來,就要看到龍鱗!”
留下一句話,燕鳶摔門而去。
玄龍回到偏殿,尋了套干凈的穿上。
門外太監見燕鳶走了,愧疚難安地湊到門邊問玄龍有沒有事。雖還未冬,長安的秋夜已足夠寒涼了,那麼桶冰水澆上去,魄健壯的人都不一定得了,何況是懷有孕的人。
那小太監多知道玄龍的況,他是個生得臉圓白凈的,看起來很面善。玄龍回他沒事,小太監又問他是否要傳早膳,玄龍走到門邊,隔著門低問。
“……你可是小氈子。”
門外人頓了頓,有些不安道。
“奴才是小氈子……”
玄龍:“勞煩你進來,幫我個忙。”
門外傳來撲通一聲,像是有人跪了下去。
“昨夜,昨夜是皇上命令奴才潑您水的,奴才若不從,便是違抗皇命,會被殺頭的,求寒公子寬恕,奴才也不想的……求寒公子寬恕……”
咚咚地,瞌起了頭。
玄龍沒想到對方會這樣驚惶不安,若開門扶他,臉上的疤說不定還會嚇到他,只得隔著門道。
“我知曉不是你的錯。”
“我只是,想勞煩你幫我做件事。”他自己做不。
“何事?……”小氈子呆呆抬起掛滿淚珠的臉,向閉的門。
片刻后,小氈子輕手輕腳地推開偏殿的門,按著吩咐進殿。
榻邊坐著個穿的男人,近五個月的肚子,已有些明顯了,形卻顯消瘦,他垂著眸,長發遮住臉上的疤,出高的鼻梁和英氣的眉眼。
“寒公子……”
玄龍合著目站起,拿起側的匕首遞給小氈子,小氈子嚇了一跳,但還是接了過來,“寒公子這是作何……”
玄龍沉默地轉過去,掀起后背的料,出后背皮,他彎下去,雙手撐在床沿,后背上顯出波浪般的紋路,漸漸化泛著澤的墨龍鱗,他淡聲開口。
“我是玄龍,你知曉的。”
“別怕,我不會害你。”
“替我將后背上的龍鱗拔下來便好。”
“這……這……不會疼嗎……”小氈子驚得發抖,他和小德子一樣,是陳巖的徒弟,被派來的時候陳巖特意將玄龍的況與他說明了,他捂嚴實,小心伺候,不了好。
饒是知道這殿中住著條龍,如今親眼見到,還是怪異得很,最重要的是,他分明看到那龍鱗包圍著的心口缺了一大塊。
“不會疼的,你手吧。”
第七十七章 誰是輸家
龍鱗堅無比,用刀子是割不斷的,唯有將刀鋒逆著龍鱗生長的隙切,連同一起拔下來。
小氈子按照玄龍所說,刀尖對準玄龍背上的龍鱗撬進去,刀刃的瞬間,玄龍形繃,泛著冷香的流順著刀刃淌下來,落在小氈子握著匕首的白指間。
“寒……寒公子……流了……”
玄龍額角滲出冷汗,啞道:“嗯。”
“繼續吧。”
小氈子原以為這拔龍鱗就和剪指甲似的,畢竟玄龍說得那樣輕巧,誰知道是會流的。拔龍鱗,分明就跟拔指甲差不多,這滿背的龍鱗要是都拔了,還能活嗎。
他哭喪著臉道。
“奴才、奴才不敢……”
“若是皇上知曉了,會殺了奴才的。”
玄龍早起時發著高熱,渾虛乏無力,扶著床側站了那麼會兒功夫,便有些撐不住了,只希小太監快些手。
“不會的。”
“是他親口,說要的。”
“你快些……我有些累了。”
這才剛醒怎麼就累了呢,皇上好端端為何要拔那麼多龍鱗,就算是為了救皇后,也不用一下拔那麼多吧……小氈子紅著眼,抖著手重新下了刀。
“寒公子,您若是不住了,便說一聲,奴才好輕些……”
他都開始說胡話了,刀子既已下去,哪里還分輕重,玄龍痛得神智模糊,也跟著應。
猜你喜歡
-
完結134 章

總裁離婚吧
婚後,單譯接手公司。沒多久集團員工傳,老板涼薄冷漠,唯獨對白家二小姐不同。後被扒出,白星悅是單譯前女友。林言不理會八卦。回辦公室交財務表,林言看正簽文件的男人:“單總,該下班了。應酬少喝酒。”單譯抬頭:“單太太,我回家吃飯。”兩人坐同一輛車被人看到:林秘書勾搭單總不要臉!後來,林言在會所洗手間撞見單譯和白星悅,她頭發淩亂,眼神閃躲。當晚林言把白紙摔單譯臉上,“單譯,離婚吧。”
26.9萬字8 54162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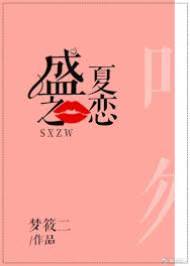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7.92 9024 -
連載917 章

她太撩,禁欲大佬淪陷攬細腰
都說殷家太子爺心黑手狠,城府極深,是絕不能招惹的北城權貴。可偏偏姜圓上趕著去勾他。 她天生媚骨,心里卻住著復仇的野獸。 他嘴上罵她不干不凈,卻為她掀了整個北城的天,幫她把仇人送進地獄。 她抽身跑路,反被他一手勾回,聲音低啞,暗含怒意,“撩完就跑?姜圓,你怎麼敢的?”
86.7萬字8 293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