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縛龍為后》 61
他只能屬于他!!
“你看著我!”
“給我說話!”
雙頰被重重掐住,玄龍被迫轉過臉,抬起眼皮,渙散的視線勉強聚焦在燕鳶臉上。
“你和燕禍珩是什麼關系?”
“你與他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說話!”
榻邊的窗戶大開著,雨霧被狂風吹殿,落在二人上,燕鳶的行為越來越兇狠,玄龍呼吸支離破碎,腹中絞痛、噬魂之痛、疊在一起的多重折磨,逐漸剝奪他本就在強撐的意識。
“我與他……不認識。”
“說謊!”燕鳶歇斯底里地朝他吼。
“沒有……說謊……”玄龍慘白的,很微弱地。
燕鳶猶如被奪走心玩的孩子,氣極了心底反倒生出幾分委屈:
“你就是說謊!我明明看到你與他抱在一起!”
“我讓你去殺他,你卻跟他攪合在一起,你是不是從未將我放在心上?!”
“你從頭到尾,也是騙我的,對不對?!”
“……沒有。”
燕鳶扣住玄龍肩膀,恨聲道。
“那你解釋,你跟我解釋!”
“我你去城外伏擊,為何燕禍橫能活著來參加我的壽宴?!”
“你又為何與他在保和殿外摟摟抱抱?!”
若玄龍真與燕禍橫茍合過,燕鳶了玄龍的服后不可能驗不出來,借著殿出來的那點昏弱燭,發現這上除去心口拔鱗所留下的傷口外,并沒有任何他不想看到的痕跡。
而他此時正強行侵占的地方,此前亦是干爽的。
Advertisement
但燕鳶無法接玄龍的世界里有任何人占據自己的位置,長廊那一幕,足以讓他失去理智,暴跳如雷。
“我與他……不認識。”
來來回回,玄龍就這麼一句話,燕鳶都聽煩了,干脆埋頭宣泄,將所有的怒火都由此發泄。
似乎有什麼溫熱的東西從玄龍下涌出來,先前兩人一起時,玄龍幾乎每回都會傷,他老說不痛,燕鳶便沒往心里去,這回亦沒往心里去。
“一句不認識就過去了?”
“你當我是三歲小孩?”
在玄龍昏迷前,燕鳶聽到他口中喃喃著什麼,就湊過去凝神聽。玄龍溫熱的氣息呼在他耳畔。
“……我待你,是真心。”
簡單的一句話,輕易將燕鳶取悅了,方才的霾散去大半,勾道。
“最好是。”
他可以不將玄龍放在眼里,但玄龍心里必須有他。
燕鳶知道這不講道理。
這世間本就不是任何事都有道理可言的,就好像人皆生而為人,卻不是每個人都能做人上人,做皇帝。
從出生那刻起,高低貴賤便已分明。
從遇見自己那刻起,玄龍便只能屬于他,任何人不得染指。
漸漸的……燕鳶終于發現了不對,玄龍下溫熱的似乎越淌越多了,如果只是普通的傷,是不會流那麼多的。
鼻間充斥著濃郁冷香,燕鳶停下作,正要查看,旁邊忽然傳來細微的靜。
殿有人出來。
“誰?!”
燕鳶迅速扯了服蓋在玄龍上,自己則順手披了件。那人影漸漸靠近,燕鳶看清來人樣貌之后,登時沉下臉。
“你怎麼在這里?!”
槲樂穿白、著腳、披頭散發地出現在玄龍所住的偏殿,容不得燕鳶不想歪,那張狐臉真是燕鳶討厭了。
“……你對他做了什麼?”槲樂盯著玄龍慘白的面容,聲問。
燕鳶想起之前在千年古潭被這狐妖辱的事,心中不快得很,沒想到這麼些時日不見,這狐妖又跟狗尾草似的纏上了玄龍。
“做什麼?自是你與玄龍做不得的親事。”燕鳶冷笑。
“他從頭到尾、渾上下,都被我用過了……就在剛剛。”
槲樂并未被他激怒,安靜地靠近玄龍,抬手去玄龍的臉:“阿泊……”
男人怎麼看都不像睡,而是昏迷……分明不久前他還好好的,與他說著話。
燕鳶怒從心起,一把將槲樂推開:“滾!”
槲樂踉蹌著退了兩步,一屁坐到地上,牽扯到上傷口,他痛得咬牙關,爬起來便沖上去要掐燕鳶的脖子。
“你這個惡心的人族——”
“我殺了你!!”
燕鳶條件反地一腳踹在槲樂肚子上,槲樂吐出一口,重重摔倒在地,半晌爬不起來。
燕鳶沒想到這狐妖變得這般不堪一擊,正稀奇得準備下地看看,就發現,玄龍下的跡,竟滲了小榻,滴滴落在地上,積一小灘。
燕鳶愣在當場。
怎麼會流這麼多……
槲樂從地上爬起來,爬到燕鳶腳邊,雙手抖著攀住燕鳶的。
“他有孕了……”
“你救他……快救他。”
燕鳶詫異地挑眉:“你說什麼?”
“阿泊……有孕了。是你的子嗣,已經四個多月了。”
“你救他……”
“求求你……”槲樂眼中淚閃爍。
阿泊很在意這個孩子的。
第六十六章 不要孩子
燕鳶戒備地盯著槲樂,都說狐貍狡猾,保不準這狐妖在玩什麼鬼把戲。
“你開什麼玩笑,玄龍可是男人。”
槲樂舌頭斷了小截,說起話來很是不利索,角的烏青尤其目,他藍眸中不斷淌出淚,輕聲道。
“有些龍生來便是雌雄同,阿泊與你行了夫妻之事,自是會懷孕的。”
“你救他吧,求求你……”
“我知道我從前欺辱過你,你恨我。只要你救他,從前的一切你都可以加倍還給我,我什麼都不怕。”
從前高傲無比的狐貍,在他最最厭惡的人族面前,跪下瞌了頭——
燕鳶見他這般模樣不像在撒謊,震驚之余一時也慌了起來,可心里還是無法接,低喝道。
“你別胡說八道了!他一條龍怎麼可能懷我的孩子!”
“你不是上天地厲害得很嗎,何須來求我!”
槲樂從地上抬起頭,笑得慘淡。
“我若有能力救他……何須來求你。”
散了一道行,他連這皇宮都不出去了,遑論是救玄龍。
燕鳶將手上玄龍蒼白的臉,溫度冰涼,他只得暫且相信這狐妖,焦急道:
“我該如何救他。”
槲樂呼出一口氣,輕聲道:“長安城中有一花,能救阿泊。”
“不準他阿泊!”燕鳶皺起漂亮的眉。
“這親昵的稱呼只能由朕來喚!”
槲樂回避,燕鳶給玄龍換上了干凈的玄袍。
他之前想哄玄龍開心,命司局的人給玄龍做了幾,都是玄袍,與玄龍本穿得樸素的料子不同,那全是宮中最上乘的布料做的,從沒見玄龍穿過,沒想到這時候倒是用上了。
然而干凈的不多時就玄龍涌出的跡給弄臟了。
燕鳶想起玄龍床頭暗格里藏的藥,昨日看見玄龍服用,問玄龍是什麼藥,他還不肯說,燕鳶直覺那藥跟今日玄龍大出有關。
他跑過去將藥瓶尋了出來,一腦倒出兩粒,放口中化開,渡給了玄龍。
上了馬車后,口中仍殘留著苦藥味,燕鳶吧咂著,心中煩躁,時不時用手探玄龍的臉,那反常的溫度他慌張。
“你說的那花在什麼地方?”
槲樂那白上出斑駁跡,前的雙手被糲的麻繩綁著,坐在靠車窗邊的小木凳上,他聽到燕鳶問話,扭過頭,虛弱道。
“尾花巷。”
猜你喜歡
-
完結2851 章
婚情襲人:前夫要複合
新婚夜,老公帶著她的閨蜜睡婚房,後來,他們又聯手將她送入監獄。五年牢獄,重回之時再見麵,簡然啐他一臉:“人渣!”向來不茍言笑、雷厲風行的男人,一把將她圈入懷中,腆著臉說:“隨你罵,隻要你做我兒子的媽!”簡然:“先生,你哪位?”男人勾唇,步步逼近,“昨夜你不是已經知道了?還是說,你想再認識我一次?”
262.3萬字8 56966 -
完結8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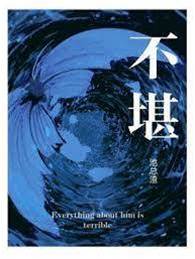
不堪
和他有關的所有事,都是不堪 【三觀不正,狗血淋頭,閱讀需謹慎。】 每個雨天來時,季衷寒都會疼。 疼源是八年前形如瘋魔,暴怒的封戚所留下的。 封戚給他留下了痕跡和烙印,也給他傷痛和折磨。 自那以后,和他有關的所有事,都是不堪。 高人氣囂張模特攻x長發美人攝影受 瘋狗x美人 封戚x季衷寒 標簽:HE 狗血 虐戀
20.2萬字8 6022 -
完結2391 章

南風過境,你我皆過客
沈姝自詡擁有一手好牌,可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會把這手好牌打得稀爛。墮胎,容貌被毀,事業一塌糊塗,聲名狼藉。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最後會變成這樣,大概是因為傅慎言的出現吧!畢竟,愛情真的能毀掉一個女人的一生。
217.2萬字8 16205 -
完結247 章

霍先生別虐了,夫人白月光不是你
放眼北城,沒人不知道霍斯年有個善解人意,懂事體貼的好太太。就連霍斯年本人也覺得霍太太體貼過了頭……“夫人,霍總今晚在夜總會。”“嗯,他工作辛苦了。”“夫人,霍總今夜不回來。”“告訴他注意身體。”直到某一天……“夫人,南梔小姐回國了。”“嗯。”溫情低頭,從包裏掏出了一紙離婚協議書,“那我祝他們白頭偕老。”……三年婚姻,他自以為自己的枕邊人早已是他所有物。可誰知那一雙溫柔多情的眸底溢出的深情是假,噓寒問暖也是假!終於,得知真相的霍先生瘋了!“溫情,我要你插翅難逃!”他以愛為名,親手為她打造出一幢夢幻城堡。可那摘了麵具的女人,褪下一身溫柔妝,渾身都是堅硬如鐵的刺。她不許別人靠近,他卻偏執瘋魔,甘願被刺的渾身是傷……
43萬字8.18 21873 -
連載176 章

偏對你服軟
【宴先生,我想跟著您。】 金絲雀靠這句話,拿下了京港太子爺。 宴先生養的低調,既沒珠寶首飾,也沒金子打造的鳥籠,聊勝於無的這麽養著。 而這隻倒貼的雀兒也不規矩。 愛挑事,心思多。 眾人想著,生於宮闕裏的宴先生心氣那麽高,大抵是不養了。 可誰知,宴先生不僅繼續養著。 還養成了京港最嬌,最媚,最得寵的一位。 直到有一天。 宴先生轉頭護青梅,奉若珍寶,兩個女人在京港鬥了個死去活來。 終是青梅勝利,把金絲雀的羽毛扒光,廢了四肢,丟進了監獄。 金絲雀拿著那支綴滿寶石的筆,在掌心寫下:【我不愛你了】幾個字,毅然捅進自己心髒。 那一夜,監獄到醫院全城封路。 宴先生跪在手術室外,虔誠祈禱。 他什麽都不要,就要在地獄裏把他的金絲雀搶回來!
43.6萬字8 2212 -
完結295 章

難哄,野痞太子爺要哭了
【豪門世家x強取豪奪x追妻火葬場xhe】【軟妹x野痞太子爺x1V1】 第一次見到周琮,是在新家的院中。 男人歪坐在藤椅,雙腿交疊,懶散道:“這麼可愛的妹寶,喊句哥哥聽聽。” 望著他耳廓淬出寒光的骨夾,許枝俏退避三舍,怕極了這位混天混地、又能掌控一切的魔王。 那天暖冬,許枝俏打開門,男人英俊逼人,耍無賴:“身份證被我扔了,收留一晚唄。” 一收留,許枝俏多了個男朋友。 直到那日,她在綠植后,聽見周琮玩味道:“玩玩而已,我寧愿不認識她。” - 都知道周家太子爺養了朵嬌花,給錢給權給時間,養的是矜貴又小心,不許外人多看一眼。 冷不丁一日,這嬌花失蹤了。 周家太子爺也跟著瘋了。 后來一場酒會,眾目睽睽,周琮單膝跪在地面,用衣袖小心翼翼擦掉女孩水晶鞋上的污痕,卑微求道:“回來唄。” 女孩當眾甩臉,小鞋尖踢開他手。 周琮握住她手腕,往自己胸口抵,嗓音嘶啞:“要算賬,往我心臟開槍,別不理我。” 多年后,兩人的寶寶跟小伙伴自豪炫耀:“我爸爸是我媽媽打獵打來的!” 周琮臭臉:“胡說,明明是爸爸死纏爛打,才把媽媽追到手的。”
47.2萬字8 34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