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魚陷落》 343
“還用不著你們多管閑事。”
“沒關系,尼克斯讓我轉達給你,你無法鏟除一切,無法給予任何種族失衡的公平,神明也只能默許黑暗存在,陸地白雪永不消融。”
言逸弓抓住厄里斯的手腕,他研究過厄里斯的構造,因此目標明確直取他前核心。
厄里斯揚起角,一縷詛咒金線纏上言逸的指尖,詛咒金線能分傷害,如果言逸強行拆他的核心,自己的腔也會遭到破壞。
僵持之時,言逸嗅到一龍舌蘭信息素。
他抬起眼皮,瞥見對面高臺上,人偶師臂彎中抱著一只人偶娃娃,正注視著他們,微:“后會有期,會長先生。”
人偶師的棋子替能力頓時籠罩厄里斯,言逸掌心一松,原本被牢牢鎖在手中的厄里斯被替換了一個小玩陶瓷娃娃。
言逸向對面,人偶師和厄里斯已經不見了。對方本無心戰,很難不讓人懷疑他們此行是否虛晃一槍,另有所圖。
他低頭打量手里的玩娃娃,發現娃娃背后有個拉環,言逸將它近耳朵,確定里面沒有安放炸彈后,謹慎地拉出了連著線的拉環。
隨著拉環自回去,人偶娃娃手腳擺,播放了一段錄音。
“八月十四日正午十二點,海陸談判,蘭波大概會帶來好東西,這是永久鏟除神使的最后一次機會了。”
這悉的聲線主人不是別人,正是典獄長李妄。
播放完這段錄音,竊聽人偶自毀裝置啟,肢分離落,散了一堆齒和陶瓷碎塊。
“好啊。”言逸早就有所懷疑,現在更是心中了然,清楚是誰在從中作梗。
他轉跳下了高臺,返回蘭波邊。
蘭波無心關注其他,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玻璃珠孵化的小獅崽上。
Advertisement
小獅崽還沒法站穩,上的絨也沒長齊,趴在水化鋼浮冰上凍得瑟瑟發抖,蘭波小心地收回尖銳指甲才敢捧起這易碎的小東西,可他掌心溫度太低,小獅崽一直冷得哆嗦。
蘭波有些無措,言逸把雙手過去捧碗形:“我比較熱。”
蘭波依舊不大信任言逸,但他也看見了珍珠墜地時言逸慌張沖出來的樣子,這才謹慎地讓他稍微捧一下,然后迅速褪去魚尾,變為人類擬態,盤坐在浮冰上,把小獅崽接回懷里,用人類的溫暖著他。
“破布娃娃敢來找我的茬。”蘭波終于有心思分神記仇,狠狠咬著這幾個字,“我記住了。”
“如果沒有小白,惡化期的厄里斯就是現存最強的實驗,白雪組織有恃無恐,也更加不想讓小白活過來。”言逸忍不住又手了小獅崽的頭,輕聲保證,“IOA終會拿下白雪,這只是時間問題。”
不過在此之前,還是要先除掉李妄那只暗中攪弄風云的老蝎子。
他下軍服披風,披在蘭波上,人類擬態無法抵海上浮冰的低溫,蘭波卻只顧暖著小白,毫不在乎快要凍得失去知覺的手腳。
小獅崽依賴地著蘭波,閉著眼睛嗅著氣味在蘭波前尋找,兩只前爪本能地在蘭波上一按一按,但蘭波又不像母獅一樣能給他產出什麼吃的,小家伙得直哼哼。
蘭波連忙夾了條小魚上來喂它,但抓到的最小的魚也比這小東西大上兩三倍,小白還沒長牙,本咬不。
好在言逸比較有經驗,安蘭波:“得喂羊才行,我去給你找。”
蘭波茫然揚起頭,眼前只見omega溫關切的臉。
言逸輕躍起,離開浮冰,落在地面上,拍了下李妄的肩:“去給我找盒羊,羊也行。”
李妄見厄里斯這一手竟沒把玻璃珠摔碎,心里已經在暗暗憋氣,沒想到竟然還把神使給摔出來了。看來那泯滅玻璃珠外包裹的珍珠質實則是供養靈魂的卵殼。
李妄只能面帶微笑,讓留在辦公室里的黑豹去食堂打點羊送出來。
他察覺到言逸的眼神里多了一層平和深沉的敵意,剛剛言逸跳上高臺與厄里斯手,距離太遠很難看得清他們是否有流,但不免令人聯想,言逸是不是知道了什麼。
李妄不聲地攥傘柄,指節發白。
黑豹依照命令送了一瓶羊和一個注出來,一走出監獄大門便敏銳地捕捉到了海面浮冰上的蘭波和他懷里小的獅子崽,以及站在言逸邊黑著臉被迫保持紳士微笑的典獄長。
他把東西給言逸,轉離開,與李妄肩而過時不明顯地笑了一聲。
聽見這聲滿帶嘲諷意味還有些痛快的笑,李妄又釋然聳了聳肩。
蘭波從言逸手里接過羊,遲疑地看了他一眼,自己先喝了一口,再灌進注里喂給小白獅。
“你可以先住在蚜蟲島,等小白長大一些再帶它回來。島上有食有醫生,房間也很暖和。你覺得遠嗎?我也可以讓南分會長在洪都拉斯為你安排住。”言逸言語,帶著恰到好的分寸。
蘭波了,垂下淺金眼睫:“不必,你們回去吧。”
他仰一躍,頭朝下翻水中,雙合并收攏為藍閃爍的魚尾,抱著小獅崽沒水中。
天空烏云盡散,一縷日撇開云層照在海上,海面的凝固封層自行開裂,大塊凝凍的平面斷開分離。
言逸讓人去清理海面上破碎的固漂浮塊,把浮塊打撈上來之后,海水遠比凝凍前干凈清澈得多,且海面也沒有再凝固,在午后太照耀下波粼粼,淺水白沙清澈見底。
參與談判的其他人也終于松了一口氣,但也有人不滿,覺得在海族首領面前姿態放得太低,會失了人類尊嚴。
“可他從未真正傷害我們。”言逸單膝蹲在海岸,撿起一塊骯臟黏手的海水固塊對著觀察里面的雜質,不再理會耳邊的聒噪。
渾濁固塊里凝著一個生銹的可樂拉環,像琥珀一樣記載著被故意忘卻的東西。
——
蘭波潛水中時,魚尾卷著飄來的蛛包裹一起下沉,吹了個氣泡把小獅崽放進去。
可即便有氣泡保護,海里的溫度仍舊太冷。蘭波在蛛包裹里發現了一個細的蛛網兜和一對蛛織的保暖手套,正好把小白放進蛛口袋里,再塞兩個手套來墊窩。
金縷蟲的蛛厚實綿,保暖極佳,小獅崽尋著暖意拱進手套里,團小小一團睡著了。
蘭波帶他返回加勒比海人魚島,順便去岸上的農場里順了一頭母羊回來,綁在沉船區甲板上用來喂小白。
蘭波一回來就躲進了寢宮,寢宮里擺了一個傾斜的華麗硨磲床,硨磲一半浸泡在海水中,另一半則翹出海面,小白獅就睡在干燥的那一面。
蘭波半個子浸泡在海水中,雙臂搭在硨磲中央的海水分界線上,歪著頭輕輕用手指挲小家伙的。
小獅崽翻了個,四只爪子攤開仰天昏睡,的爪墊一起對著蘭波。
“噢……randi……”蘭波一手支著頭,彎著眼睛輕白獅的爪心,忍不住喃喃自語,“我給你天賦、健康、容貌。”
蘭波指尖掉落藍星塵,隨著融白獅崽。
他看了獅崽太久,直到滴水的金發都晾干了,自己困倦得睜不開眼睛。
可他又怕小東西半夜跌落進冷水里,便用臂彎圈著他,一直盯著看到意識模糊睡著。
恍惚間,蘭波夢到玻璃珠炸碎,周只剩一片蒼茫,他突然忘記了最的人,渾渾噩噩尋找千上萬年。
在夢里,有人突然從背后抱了他,吻他的后頸和耳側,在他耳邊溫輕笑:“我也不許神忘我。”
蘭波忽然驚醒,昏昏沉沉發了下愣,臉頰邊已經積攢了一灘形狀不規則的黑珍珠。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茸茸的溫熱小地團在他頰邊,依賴地著他。
它上稀疏的絨變得蓬松雪白,看上去比自己睡著前稍大了些,了一些脆弱的易碎。
“randi!”小白的生長速度讓蘭波驚喜得沒了睡意。
小白半睜開眼睛,哼唧著在硨磲上蠕,嗅到了蘭波的指尖,開始賣力地嘬起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9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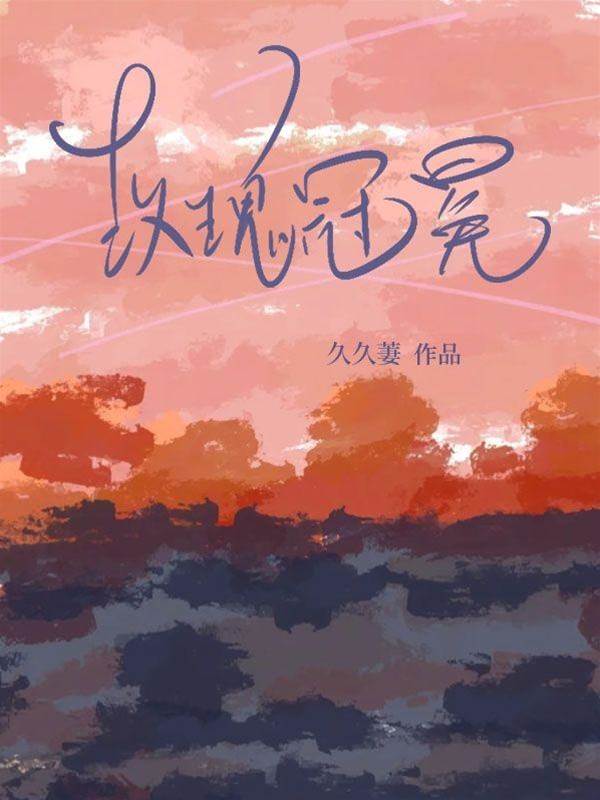
玫瑰冠冕
【先婚後愛?暗戀?追妻火葬場女主不回頭?雙潔】她是徐家的養女,是周越添的小尾巴,她從小到大都跟著他,直到二十四歲這年,她聽到他說——“徐家的養女而已,我怎麼會真的把她放在心上,咱們這種人家,還是要門當戶對。”-樓阮徹底消失後,周越添到處找她,可卻再也找不到她了。-再次相見,他看到她拉著一身黑的少年走進徐家家門,臉上帶著明亮的笑。周越添一把拉住她,紅著眼眶問道,“軟軟,你還要不要我……”白軟乖巧的小姑娘還沒說話,她身旁的人便斜睨過來,雪白的喉結輕滾,笑得懶散,“這位先生,如果你不想今天在警局過夜,就先鬆開我太太的手腕。”*女主視角先婚後愛/男主視角多年暗戀成真【偏愛你的人可能會晚,但一定會來。】*缺愛的女孩終於等到了獨一無二的偏愛。
33.4萬字8 61089 -
連載199 章

她一哭,他發瘋,京圈誰都惹不起
傅梟寒是A市權勢滔天的商業大佬,他手段狠辣,冷血陰鷙,禁欲高冷,不近女色,是無數名門世家女擠破頭,也觸碰不到的高嶺之花。唐星覓從小日子過的清苦,寄人籬下,舅媽為了16萬把她送給一個大腹便便的油膩男。她不想斷送自己的一生,拚命反抗,逃出狼窩,卻意外闖入他的房間,一夜旖旎,誰知,一個月後檢查出她肚子裏懷了寶寶。自從那夜嚐過她的“甜美”後,男人食髓知味,一發不可收拾,找到她,臉皮厚的纏著她非得要一個名分
27.6萬字8 5806 -
完結113 章

多雨之地
青春治愈 校園 情有獨鐘 HE 如果淋雨無法避免,那就一起變潮濕。陳準知道凌羽是誰。是開學遞給他一把傘的陌生人,是朋友口中有名的“怪咖”, 是舍友昔日的追求者,更是往他心口上插一把刀的騙子。
16.6萬字8 409 -
完結574 章

她發瘋,他兜底,團寵誰都惹不起
雙潔+馬甲+醋王暗戀+強寵酥爽+互撩拉扯+先婚后愛+虐渣打臉和渣男分手后,徐方梨準備回家繼承家業,結果家里的總裁哥哥可憐巴巴跪求:“家里要破產了,你去聯姻吧!” 聯姻就聯姻,可誰能告訴她不是破產了嗎?那個民政局門口開著跑車,載著美女,呲著大牙的狗頭怎麼那麼像她哥! 為兄弟兩肋插刀,為了妹夫徐方野直接插自己兩刀! - 韓二爺心底有一個埋藏近二十年的秘密。 他連跳數級出國深造,不擇手段掌控權勢,都是為了早一天站到那個女孩面前。 他最潦倒的那一年,她談了戀愛,他往返數次沒敢露面。 六年后,她分手,他果斷出現聯合大舅哥將人叼回家。 - 小糊咖搖身一變成了豪門團寵,隱婚闊太! 娛樂圈三料視后:從今天開始,這就是我親妹子! 國際頂流音樂天才:小梨子,再給我寫首歌怎麼樣? 買下一座山隱居的老爺子:小祖宗,趕快回家繼承家業! 人傻情多狗頭哥:老妹!給你買了個小島,你看起個什麼名比較好? 韓二爺將人按進懷里,低聲誘哄:果寶,還想往哪跑?
101萬字8 19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