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王霸寵:神醫狂妃要休夫》 第561章 又欺負我兄長
“什麼!”這個訊息,對邵家這三人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
邵承武隻覺得腦中驚雷炸響,整個人石化在原地。滿心滿腦,就隻冒出一句話。
“邵家,要亡啊!”
而邵張氏和邵離,也已經被驚得愣住在原地,大腦之中一片空白。
在他們驚愣之際,白公公尖細高的聲音已經傳了進來:“皇上駕到!”
這一聲,讓本就心驚膽戰的邵家眾人雪上加霜。
眾人俱都是渾抖了三抖。
接著,還冇等看到皇帝的影子,就“撲通”“撲通”的紛紛跪了。
於是,待皇帝走進鎮南將軍府,周圍地麵,七八糟在跪滿了人,個個都趴在地上一不,像極了一坨坨五六的牛粑粑。
皇帝滿心隻想著被邵家抓來的風軒戰神,當下神嚴肅,氣哼哼的往正堂走。
墨蕭璟與顧輕染跟在皇帝後,一邊走一邊看著邵府的這些人。
看樣子,他們都知道大禍臨頭了。
誰讓他們攤上這樣的主子呢?
“哎!”顧輕染歎了口氣。
腳步行正堂。
邵承武、邵張氏、邵離,都已經整整齊齊的跪在地上。聽到皇帝的腳步聲,立時開口高呼:“末將參見皇上!”
皇帝寒著一張臉,冷冷看過他三人,進門便是一句:“是你們抓了風軒戰神?”
邵離嚇得臉鐵青,趴在地上大氣都不敢出。
還是邵承武冷靜些,嚥了口口水,抖著回了聲:“是!皇上,是犬子不知天高地厚,末將代犬子跟您請罪!都是末將教子無方,請皇上責罰!”
皇帝咬牙切齒,再開口,一聲怒喝:“邵承武,邵離,是誰給了你們這麼大的膽子?連風軒戰神都敢抓,你們是嫌命太長了嗎?你們把風軒戰神關在哪裡,說!”
Advertisement
聽皇上大怒,邵承武聲音抖的更厲害了:“在,在地牢!”
“地牢?”皇帝的臉簡直難看到了極點:“你們竟敢把風軒戰神關在地牢?你們!”
話說到此,皇帝忽然捂住口,神顯得十分痛苦。
墨蕭璟趕忙上前將皇帝扶住:“父皇!”
邵承武見狀,亦是趕忙說道:“皇上息怒,保重龍啊!”
好在皇帝並無大礙,隻是捂著口緩了口氣息。待緩過氣來,又是怒看向邵承武:“愣著乾什麼?還不把風軒戰神給朕放出來!”
這架勢,果然氣得不輕啊!
顧輕染在一旁看著,心中都開始為邵家這幾口人默哀了。
邵承武哭喪著臉,一臉的無可奈何:“皇上啊,不是微臣不願放他,是風軒戰神他,他……”
那一臉的有苦說不出,看起來是有苦衷。
“他什麼?”皇帝心裡頭著急:“朕警告你,若是風軒戰神有個什麼三長兩短,朕絕饒不了你!”
邵承武是真的要哭了:“皇上,您想見他,就隻有一個辦法了。”
一聽這話,皇帝心裡冇了底:“該不會他已經!”
邵承武垂下頭:哎,吾命休矣!
邵府後院,暗的地牢。
冬天本就冷,這地牢之中就更是冷的刺骨,空氣中的寒氣直往骨頭裡鑽。
走在地牢之中,空氣泛著一子令人作嘔的黴味,眾人都是忍不住捂住了口鼻。
顧輕染這位嗅覺超常的人,就更覺難以忍,於是悄悄朝墨蕭璟邊靠了靠。嗅到他上淡雅的竹葉清香,頓時覺得好多了。
墨蕭璟留意到了的接近,看到在嗅著他上的味道,頓時明白了怎麼回事。妖孽般的揚了揚角,忽而抬手,攬住了顧輕染的腰。
這忽而被他收進懷中,顧輕染嚇了一跳。
皇帝就在前麵,墨蕭璟這作做得極其小心。微微俯,在顧輕染耳邊小聲說了句:“來本王懷裡,聞得更清楚。”
顧輕染頓時紅了臉。
還以為自己這小作神不知鬼不覺。
竟然被他發現了。
抬手捂著臉,頓覺冇臉見人。
走在一旁的白公公,看到了他二人親的舉,臉上出了欣的笑容。
很恩嘛!
此時其他人的心,就冇他們這般輕鬆了。
皇帝臉沉,想到風軒戰神竟然被邵家在這種地方關了好幾天,都恨不得立即把邵家這幾口人給砍了!
這麼刺鼻的味道,這麼惡劣的環境,還這麼冷。
是他疏忽了,怎麼能讓風軒戰神這種罪呢?
待會兒可該如何跟風軒戰神請罪纔好啊!
邵承武與邵離、邵夫人,正走在前麵,戰戰兢兢的帶路。越往裡走,心裡就越冇有底。
九五之尊竟親自下到他邵府的地牢。
這恐怕砍頭都不夠啊!
當下心裡就是後悔,十分後悔。
可後悔又有什麼用呢?
又是往裡走了一段距離,邵承武腳步停下:“皇上,到了。”
皇帝蹙眉:“到了?”
邵承武抬手往前一指。
這一眼看過去,皇帝眼前一亮,目驚訝之。
隻見左前方的一間牢房,牢周圍的牆壁掛著好幾盞油燈,照得那燈火通明。
牢房的地麵,不像其他牢房那般佈滿淩的乾草,不僅整理的乾乾淨淨,還鋪上了厚實的地毯。
地毯的中間擺放了一張長案,長案上,擺著滿滿一盤新鮮的水果,還有幾碟點心、一套茶盞。一盞香爐正嫋嫋升煙,香氣隔著這麼遠都聞得見。長案兩旁還燒著兩盆紅彤彤的火炭,看著都暖和。
而風軒和顧雲離這師徒二人,此時正麵對麵坐在那長案兩邊,對著長案上的棋盤,專注的下棋。
且牢房的門,正大大敞開著,門上的鎖鏈極其隨意的掛在門上,完全冇有上鎖的意思。
這一幕,看得墨蕭璟和顧輕染都愣了。
這哪裡是坐牢?
分明是度假嘛!
連坐牢都能坐的如此與眾不同。
不愧是他風軒戰神啊!
邵承武哭喪著臉走進牢門,對風軒恭恭敬敬、小心翼翼的說了句:“風軒大人啊,咱先彆下棋了,皇上來了!”
風軒卻是頭也冇抬,仍著手中的棋子,琢磨著往何落子。
此時皇帝等人,也跟在邵承武後,進了牢房的門。
風軒可以將皇帝視而不見,顧雲離卻不能。
於是抱拳跪地,恭敬道了句:“顧雲離參見皇上。”
皇帝抬手:“賢侄不必多禮。”
方纔顧雲離一直都背對著牢門,看不清臉。
現在他轉過來,顧輕染才發現,顧雲離這張俊臉上竟然滿了長長的紙條。
兄長向來是個木頭臉,這一臉的紙條與他的氣質大大違和,惹得顧輕染忍不住掩一笑:“哥,你這是?”
顧雲離皺了皺眉頭:“輸棋了。”
顧輕染忍不住笑個不停。
實在是很看到顧雲離這幅樣子。
一看就是風軒的主意。
“跟風軒下棋,不輸纔怪!”顧輕染看向風軒:“又欺負我兄長,我是不是該把兄長收回來了?”
風軒笑著看過來:“誰說老朽欺負他了?”
微微轉,往背後指了指:“喏,老朽也輸了一局呢!”
他的背後,確實也著一張紙條。
隻是這白的紙條在他的白上,實在難以察覺。
顧輕染雙手叉腰:“為什麼你在背上,卻要兄長在臉上?”
風軒笑得還是那般溫潤:“圖大事,莫拘小節。”
顧輕染抬手扶額。
真是拿這個老頑冇辦法。
一旁的邵家三人都快哭了。
都這時候了,您二位還有心思說笑呢?
人命關天吶!
此時皇帝抬步走到了風軒前,躬著子:“風軒前輩,都怪朕,今日才知道此事,竟然讓您在這種地方待了這麼多天。是朕疏忽,讓您苦了,還前輩息怒!”
隨即抬手指了指邵承武那三人:“都是他們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對您如此無禮。您說,要朕怎麼置他們!隻要您說,朕必定照做!就算您要朕殺了他們,朕都絕無二話!”
這番話說出來,牢氣氛瞬間凝重而抑。
邵家那三人,惶恐的將目看向風軒,隻等著風軒宣判死刑了。
而風軒,卻仍是那般瀟灑的坐在長案前,扶著下,一臉的若有所思。
他倒是輕鬆泰然。
邵家三人卻慌了。
風軒這是在思考怎麼弄死他們呀!
當下雙一,“撲通”一聲齊齊跪地,紛紛對著風軒連連磕著響頭:“風軒大人,饒命啊!”
猜你喜歡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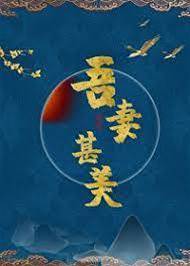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
完結2238 章

天下第一妃
她,二十一世紀Z國軍情七處的頂尖特工,一朝穿越成為懦弱無能的蕭家廢物三小姐!未婚夫伙同天才姐姐一同害她遍體鱗傷,手筋腳筋被砍斷,還險些被大卸八塊?放肆!找死!誰再敢招惹她,休怪她下手無情!說她是廢物?說她沒有靈獸?說她買不起丹藥?睜大眼睛看清楚,廢物早就成天才!靈獸算個屁,神獸是她的跟屁蟲!丹藥很貴?別人吃丹藥一個一個吃,她是一瓶一瓶當糖豆吃!他,絕色妖媚,殺伐決斷,令人聞風喪膽的神秘帝王。當他遇上她,勢必糾纏不休! “你生生世世只能是我的女人!
411.7萬字8 36333 -
完結1065 章

新婚夜和離,失寵醫妃冠絕京城
醫學天才穿越成淩王棄妃,剛來就在地牢,差點被冤死。身中兩種蠱、三種毒,隨時都能讓她一命嗚呼。她活的如履薄冰,淩王不正眼看他就算了,還有一群爛桃花個個都想要她的命。既然兩相厭,不如一拍兩散!世間美男那麼多,為什麼要天天看他的冷臉?……“我們已經合離了,這樣不合適!”“沒有合離書,不作數!”就在她發覺愛上他的時候,他卻成了她殺母仇人,她親手把匕首插入他的心口……真相大白時,他卻對她隻有恨,還要娶她的殺母仇人!“可是,我懷了你的孩子。”“你又要耍什麼花招兒?”
177.9萬字8.18 12197 -
完結274 章

醜女絕色,瘋批暴君夜夜囚寵
前朝覆滅,最受寵愛的小公主薑木被神醫帶著出逃。五年後她那鮮少接觸過的五皇兄平叛登基。她易容進宮,為尋找母親蹤跡,也為恢複身份……一朝寒夜,她忽然被拉入後山,一夜雲雨。薑木駭然發現,那個男人就是龍椅之上的九五之尊……她再次出宮那時,身懷龍胎,卻在敵國戰場上被祭軍旗,對麵禦駕親征的皇帝表情冷酷無比,毫不留情的將箭羽瞄準於她……他冷聲,“一個女人罷了…不過玩物,以此威脅,卻是天大笑話!”(注:此文主角沒有冒犯任何倫理)不正經文案:……獨權專斷的暴君為醜女指鹿為馬,即便醜陋,也能成國家的絕美標桿!恢複真容的醜女:……那我走?——————種植專精小能手,從人人厭憎的“禍國妖妃”,變為畝產千斤的絕色皇後!
49萬字8 26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