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總不肯離婚》 第十七章
落陷阱的獵一般都沒什麼好結果。
不管是滋味鮮的,或是模樣好看的。
下場凄凄,鮮有例外。
尤其像江景白這種,味甘如飴,靡膩理,被獵手活生生從里到外磋磨一通并不稀奇。
人一旦被上絕路,只要還留有一口氣在,潛能瓶頸總會被打破。
生命不息,殘不止。
江景白第二次從地獄煉場完一遭,的承能力明顯增強了不。
至他沒雙眼一闔,不省人事到下午兩點。
不過等他醒來,南鉞依舊上班去了。
江景白腰酸,四肢乏力。
整個人著裹在被子里,如同一白綿綿的,從湯碗里撈出來的面面條。
還被瀝干了水兒。
和上一回相比,該習慣的也習慣了,該后怕的,也更害怕了。
江景白手背搭在額頭上,雙眼放空的對著天花板。
好疼。
真的好疼。
他剛剛略回顧了一遍,越想越嚇人。
昨晚他難得沒有一開始就喪失對語言系統的掌控,心驚膽戰地央著南鉞慢慢來,南鉞也依了他,的確比浴室那次平緩很多。
由淺深,穩扎穩打。
可江景白,還是哭了孫子。
想到這里,江景白翻了個,抱住自己吻痕遍布的兩條胳膊,苦不堪言地發出一聲長長的悶哼。
準備做足了。
南鉞有了經驗,技也進了。
他應該……應該也卸去了心理防線?
江景白不太確定,但這會兒實在顧不上什麼防線不防線的,唯一毋庸置疑的,是他心理影更大了。
南鉞那尺寸太驚人,一頂進來,他就算是個妖也該被降魔杵捅得魂飛魄散了。
現在是上午十點,外頭鋪得正好,金燦燦地在床腳前投出細長的一道,將臥室的昏暗驅散大半。
Advertisement
主臥是雙層窗簾,外面是半鏤空的窗紗,濾和,氣通風,里面才是布層,沉重厚實,遮強。
江景白獨居慣了,最不喜歡一覺醒來,一個人面對滿室漆黑。
他搬來第一晚,睡前便將靠近床尾的那邊窗簾留出隙,后來跟南鉞一起休息,這才把窗簾拉得嚴實。
然而南鉞似乎從第一晚就揣測出江景白的習,但凡早起,肯定在他睡醒前把布層邊緣拉開一點,不影響睡眠,也不至于太黑。
今天同樣如此。
江景白坐起,對著斜在地板上的小塊發了會兒呆,下床開始換洗漱。
他打開柜,發現南鉞的那些正裝竟被移到稍稍靠邊的位置,昨天晾曬在臺上的那幾套反而掛到了桿中間。
江景白目微頓,向收納屜的手也停了下,半晌“噗嗤”一聲,被南鉞這種不分輕重的一不茍逗笑起來。
在家里穿的棉質常服哪需要掛著防皺?
他隨意了條套上,服則挑了負擔最輕的運裝。
上下都穿好了,江景白把南鉞的襯衫掛回原,將皺了也無傷大雅的家居服一一疊起,整齊放到另一端的隔板上。
廚房里照常備著粥點。
江景白盛出一碗,碗口覆好保鮮,端進微波爐加熱,又給自己炒了碟小菜,煮了小份的掛面,混著南鉞做的早餐一起吃了,順帶連午飯也簡單解決。
那天之所以和林佳佳詳細訂好預約事項,就是為了減待在花店的時間。
江景白這次將近中午才到店里,林佳佳不以為奇,沒再拿他說笑,擱下手頭的事把一沓小票遞過來:“昨天你接的單子,我已經幫你打印出來了。正面往上的是下午三點到五點要送的,往下的幾張是七點后,你自己注意時間順序。”
“好。”江景白應了聲。
他昨晚消耗大,起得也比之前早,可能在床上還沒歇夠,江景白出門沒走多久就發,撐著到了店里,暫時不想彈了。
林佳佳看他進店沒說兩句話就占去了自己的豪華“專座”,心里裝豆腐,上拋刀片:“怎麼了這是?別告訴我你也想當帶病上陣的拼命三郎,咱還沒窮到缺這點兒錢的地步吧。”
說著往江景白臉上仔細打量幾眼,自我否定:“得,您這春風滿面白里紅的,要說病了,全國醫生都能被你難為死。”
江景白窩在懶人椅里,把訂單小票一張張翻下去。
他能力強,做事踏實,更有天賦加,才看完客人提出的要求,心里就有了模糊的設計廓:“借我歇會兒,月底給你付租金。”
“行吧。”知道他不是生病了,林佳佳回過頭,繼續忙自己的,“江老板是看上我這塊風水寶地了,昨天才坐過一次,今天一來就惦記。”
江景白正渾提不起勁兒,沒心思再跟好友的尖牙利一較高下。
等大側的不繃發了,江景白站起來,讓學徒幫忙去取需要用到的幾樣花材,自己系好圍站到工作臺邊。
今天被來學基礎的學徒是個中專畢業的小丫頭。
年紀小,閱歷低,前腳剛離開學校的象牙塔,后腳就進了這種氛圍和睦溫馨的工作環境,不被罵也不跌跟頭,說起話來經常不過腦子。
孩子普遍心細,待在店長旁才記半頁筆記,眼睛直往江景白的運裝束上瞅:“店長,你今天是不是去晨跑了?”
江景白正給易折花做著保護工作,蔥白指間的朱頂紅大朵鮮紅,遠沒有手指主人的那張臉高調明艷:“沒有啊,為什麼這麼問?”
他來時走路都難,還晨跑?
不如殺了他。
“因為剛剛,你的在抖哎。”小丫頭天真道,“這不是運過量的表現嗎?”
江景白右手一偏,刀片沒繞到花切口,險些割他自己手上。
“我以前上完育課也經常這樣。”小丫頭認真記錄,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寫下“朱頂紅花易折,需用其他花材的口才便花”的字樣,“我們班的育老師可變態了,每節課都讓我們去雙杠那里拉筋。剛下課的時候還不覺得什麼,等睡完一覺,第二天起來,我的天吶,特別酸爽。”小丫頭擰起五,好似牙酸,“有的人上下樓梯都得扶著墻呢。”
江景白潛意識里自把雙杠換算書桌,只覺得更難了。
他換了個站姿,替調用雙支力,利落理余下幾枝花材。
“店長,鍛煉是好事,你可千萬不要突然勉強自己啊。”小丫頭關切道,“你這麼好看,就算沒有也是宇宙無敵大男神。”
江景白一時不知該在意“鍛煉”,還是該在意“沒有”。
他放下刀,將新西蘭麻的葉端扣卷起,到朱頂紅四周,苦笑道:“好,我知道了,我會注意的。”說著往旁邊挪開點位置,招手示意上前,“你先把筆放一放,過來自己試試手。”
小丫頭子單純,天真語錄一句一句地往外蹦。
江景白起初還因昨晚過于激烈的床事到害臊,聽著聽著倒不自覺笑開了。
他這一下午過得不算輕松,在工作臺上就耗了好幾個鐘頭,期間偶爾坐在椅子上休息,遇到新老客人找他說話,出于禮貌,還必須要再站起來。
等真正能上口氣,江景白調看起電腦里的詳細進賬,心說下次如果再醒得早,他說什麼也要多賴會兒床,不那麼著急出門了。
剛想通這點,江景白腦子突然鈍起來。
下次?
還有下次???
狼藉的桌面,不堪的大床,還有七八糟的胡鬧聲響紛至沓來,震得江景白連鼠標滾都滾不下去。
合法夫夫,共同經營一個小家,當然有下次。
江景白結了,關掉表格。
林佳佳腐齡高,上學時發現什麼好看的小說漫畫,也給江景白這個小基佬傳一份。
有的很清水,有的則帶有很強的元素。
江景白沒談,年輕氣盛的,自然對做有過向往,他藝細胞強,幻想的畫面都很唯。
現在婚也結了,也做了。
向往沒有了,唯被打破了。
最要命的是,江景白竟然還生起了瑟的念頭。
那覺太疼,如果可以,他不想再和南越滾到床上。
江景白嘆出一口氣,抬手往眉心掐了掐。
都說流是婚姻生活里不可或缺的潤劑,怎麼到了他這,覺就跟懸在頸后的砍頭刀一樣。
江景白正愁該拿砍頭刀怎麼辦才好,電腦右下角突然冒出來一個消息彈窗。
是后臺件自帶的那種,有時是實時熱點,有時是八卦營銷,總之毫無營養。
江景白下意識想去點叉,可余一瞄過去,眼睛頓時錯不開了。
今天彈出的這則比較近生活,標題那行話格外通俗易懂。
只見上面明明白白排著幾個大字:[離婚的理由千萬種,最終逃不出這十大理由。]
標題下還有白底灰字的容提示:[(1)家暴;(2)出軌;(3)婚前就無;(4)生活不和諧;(5)……]
江景白:“……”
第五小點往后是什麼,江景白沒留意去看,滿眼只有正中靶心的三四小點。
他心說不至于吧,握著鼠標的右手卻是有了自己的想法,作流暢地點開了網頁。
作者有話要說: 南鉞:突然有種不好的預。
放心啦不會,不會離功的,畢竟文名是不肯哈哈哈
猜你喜歡
-
完結814 章
一胎两宝:总裁爹地超给力
被未婚夫和堂姐聯手算計,她意外懷上陌生男人的孩子,還一胎雙寶!四年後,殷城第一豪門戰家大少強勢闖入她的生活,將她逼到牆角:“聽說你藏起我的一對雙胞胎?”奉子成婚,她被迫成為戰家少夫人。婚後,有記者發問:“戰太太,請問有個財雄勢大的金大腿老公是什麼感覺?”她隨意擺手:“也就關鍵時候拿來用用,just-so-so。”當晚,她就被男人逼進浴缸動彈不得,男人欺身而上:“夫人對我的服務似乎不太滿意,just-so-so?”她以為自己跌落深淵,卻不想在深淵底部遇到了他。從此春風是他,心底溫柔也是他。
141.3萬字8.18 159952 -
完結33 章
獨鍾
溫柔美人被老爹賣給別人還債,被迫嫁給攻,做好了一輩子受欺負的準備,結果被攻從頭到尾地捧在手心裡寵,一點兒委屈也不讓他受,的耿直甜文。 內容標簽: 情有獨鍾 搜索關鍵字:主角:方素│ 配角:唐橋淵│ 其它: --------------------------- 小妹有話說:意外的小品溫馨文XD
7.1萬字8 8529 -
完結118 章

引她放縱
[京圈大佬 滬圈千金×曖昧拉扯×追妻火葬場×雙潔]圈子裏的人都知道,應珩之是四九城裏最惹不起的人物,他矜貴自持,冷冽沉穩,雷厲風行。外交部的慶功宴,是周惜除了在1308房裏第一次見到應珩之。他姍姍來遲,卻坐在全場的主位上,連翻譯司司長對他都畢恭畢敬。周惜裝作不認識他,麵帶笑容,敬了他一杯酒。他氣場淩然,嗓音低沉慵懶,“章老帶的學生不會錯的。”宴會結束,他們心照不宣的進了1308的房門。—待周惜意識到事情脫軌時,果斷提出停止他們之間的關係。應珩之指腹緩緩摩挲她的下巴,麵色冷漠,聲音暗啞像是壓著怒火,“你把我當做什麼?”周惜扭頭,語氣平靜,“枕邊摯友而已。”他怒極反笑,緊握的拳頭狠戾砸在牆上,淩厲的冷風鋪過周惜側臉。他掀了掀眼皮,聲音陰沉漠然,麵無表情說,“好,別後悔就好。”—幾個月後的高級晚宴上,周惜盛裝出席,終於目睹了滬圈頂級豪門千金的姿容。拍賣會後,人人都聽說了京圈太子爺應珩之連續拍下數十個藏品,豪擲八十個億。身旁好友驚訝問他原因。他雙眸濃黑如墨,視線始終落在和旁邊人歡聲笑語的女人身上。他強壓暗癮,聲音晦暗低語。“哄人”
23萬字8 29987 -
完結212 章

偏袒
一夜之間,陳佳餚成了孤兒。 到處都是消毒水味道的醫院,陳佳餚第一次見到那個男人。 男人西裝革履,高挺鼻樑上架着一副金絲邊框眼鏡。 鏡片背後,是一雙深不見底的眼睛。 陳佳餚低聲問:“那我以後……” 男人擡手蓋在她腦袋上,說:“跟我。” “叫我周叔叔。” 男人擡手間,有風穿堂過,陳佳餚聞到了一股特別的菸草味道。 陳佳餚畢業那天,周延禮一身酒味地窩在沙發上,他有些不耐煩地扯了扯領帶,摘下高挺鼻樑上的金絲邊框眼鏡,掀眸:“長大了,想要什麼禮物?” 陳佳餚盯着他被酒精染紅的薄脣,聞到的不是酒精的味道。 是荷爾蒙。 - 周延禮自成年開始獨居,十年間從未帶回家過一個女孩子。 後來因爲陳佳餚,家裏逐漸多了女孩子用的東西。 好友來串門,看到當初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脫落成亭亭玉立的小女人,大傢俬下總愛調侃,“周教授沒想過把家裏那位收——” 周教授本人無情打斷,“我是教授,不是禽/獸。” 不久後,陳佳餚留學歸國。 朋友圈永遠只分享各種數理化競賽題的周教授難得發了個朋友圈,一個小紅本結婚證。 證件照上素來以高冷麪癱待人的周教授脣角微微翹起一抹弧度,溫柔之意幾乎要溢出屏幕。 朋友圈文案:謝謝,獸了。 朋友們:……就知道你是個人面獸心!
32萬字8 8561 -
完結19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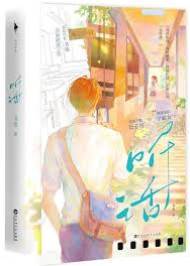
聽話
那不是程歲寧第一次見周溫宴。 她見過他意氣風發,見過他浪蕩不羈,見過他懷裏女孩換了一個又一個。 只是那次,她心動最難捱。 那天室友生日她走錯包間,偶然窺見他懶懶陷在沙發裏,百無聊賴撥弄打火機。 火苗忽明忽暗身旁女生和他說話,他勾着笑半天敷衍回個一字半句。 她回到包廂裏第一次鬼迷心竅主動給他發了信息,【今天聚會好玩嗎?】 下一秒,他回:【你不在沒意思。】 後來他們分手,多年後在風雨裏重逢,她被男友差遣輕視狼狽不堪。 他跨過一衆圍着他殷勤討好的人羣,不顧目光,拉住她的手,塞進一把傘。 冬夜昏天暗地光線裏,他垂眼看她,聲音淡淡:“撐傘,別淋雨。” 那一刻她這才知道,除了他以外都是將就。 朋友問那再後來呢?她淺笑着沒說話。 只是每年西園寺,雲蒸霞蔚煙火繚繞的銀杏樹下多了個虔誠的少女。 那天年初一,青衣僧人說有緣人贈了她一張紙條。 展開一看,字體熟悉,上面寫着‘一歲一禮,得償所願。’ 她下意識回頭,人海茫茫裏,一眼只看見他溫柔背影。
34.2萬字8.18 6369 -
完結227 章

揉碎風情
【表面禁慾實則身體很實誠男主+旗袍美人、清冷尤物女主+雙潔) 顏霧跟了傅北津三年,床上床下,無微不至。 傅北津一句膩了,毫不留戀將她踹開。 分開那天,傅北津最好的朋友湊過來,“北津哥,我惦記顏霧姐好久了,你不要她,我可要下手了!” 傅北津捏碎了手中的酒杯…… 所有人都認定,顏霧不過是傅北津的玩物。 那夜,人來人往,高不可攀的傅少單膝跪在她腳邊,求她看他一眼,大家才知道,原來,在這段感情中,他才是用
45.4萬字8 1223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