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霜》 第26章 十一萬,我上你
兩人雖然在一起幾年,但從沒有到那一步。
沈世霖說,他要在最幸福的那一晚給他。
他尊重。
他也真的。
可是啊,他們誰都沒想到相的兩個人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沈世霖拿掉溫諾的手,讓凹凸有致的暴在自己視線里。
材纖細,前凸后翹,該多的地方一點都不,不該多的地方也不會多,骨架小,長年累月的兼職,讓一點都不胖,反而線條極好。
正是熱烈的時候,大片的照在溫諾上,那撲了的皮似在發。
他恨啊!
恨不得殺了那個男人,殺了溫諾。
怒火讓沈世霖失了理智,他掐住溫諾的脖子,手上青筋突突的跳,“是不是只要給你錢,你就可以隨便讓人上?”
溫諾快不過氣了,但竟然沒有任何的痛苦,怨恨,相反的是平靜。
甚至溫諾還能去看沈世霖,看他暴怒的模樣,那雙赤紅的眼睛,里面是痛,是恨,是。
當初有多,現在就有多恨。
林可兒真的做的很好。
“你為什麼不說話?你說啊!劇組給你多錢?讓你看著被別人上,你說,我給你十倍,百倍!”
Advertisement
溫諾想哭,可哭不出來,即使現在結痂的心又被撕裂。
“十一萬。”艱難的吐出這幾個字。
瞬間,溫被沈世霖扔到地上。
“十一萬,好,很好!我現在就給你,你給我上!”沈世霖掏出錢包,把里面的卡,支票,錢全部扔到溫諾上。
溫諾沒看,掙扎著去拿浴巾。
看見了那邊有人。
可剛抓著浴巾邊角,就被沈世霖扯掉扔到海里。
沈世霖嘲諷的笑,“被那麼多人看你都不怕,現在沒人看你遮什麼遮?”
“溫諾,要賤就賤到底。”
沈世霖把西裝了,襯衫了,朝下。
溫諾沒掙扎,也沒,歪頭看著起涌的大海,那大片的藍落進眼里,清澈亮的像此刻的藍天白云。
遙遠,空茫。
“沈世霖,你真的不嫌棄我這?”溫諾問,眼睛看著沈世霖。
沈世霖頭上的青筋冒起來,撐在沙灘上的手握拳,一雙眼紅的像要流。
溫諾繼續說:“不介意的話,那我們做吧。”
手抱住沈世霖的脖子,眼里出市儈的,“剛剛你把那些錢和卡給我了,可不要反悔。”
說完閉眼,朝沈世霖吻去。
只是那閉眼的瞬間,羽扇似的睫了下。
但溫諾的快要到沈世霖的時候,沈世霖一把推開。
“你這麼臟,還想要錢,做夢!”沈世霖抓起溫諾走向大海,把的頭按到海里,“你想要錢,先把自己洗干凈了,你什麼時候洗干凈給我上了,我什麼時候給你錢!”
不知道過了多久,沈世霖累了,溫諾也昏迷了。
沈世霖坐在海水里,溫諾倒在旁邊。
他著氣,單曲著,手搭在膝蓋,潤的發尖滴下一滴滴的水珠。
好久,他看向旁。
海浪褪去,灑下,像條人魚,上是波粼粼的。
沈世霖癡迷了。
他從來就知道溫諾長的。
不僅長的,更有一顆善良的心。
他永遠都忘不掉看他的第一眼,明亮,清澈,堅韌,像開在懸崖的玉蘭,瞬間奪了他的心。
可為什麼,為什麼你要背叛我?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你?
我恨不得把我所有的都給你,只要你在我邊,只要你屬于我。
可你背叛了我,你背叛了我們的,你就該到懲罰。
溫諾,這輩子,我不折磨你,我心難安。
沈世霖的手落到溫諾臉上,繾綣溫的過臉上每一寸。
遠,林可兒看著這邊,涂滿丹蔻的指甲狠狠掐進掌心。
溫——諾——
沈世霖手機響了,他要低頭吻溫諾的抿。
一瞬間,眼里所有的收斂,除了恨,再無其它。
沈世霖起,撿起襯衫西裝離開。
只是走了兩步,他停下,拿著西裝外套的手握。
兩秒后,他繼續朝前走,再無停留。
溫諾,今天我就讓你自生自滅。
你如果死了,那說明老天爺都要懲罰你,如果你沒死,那好,我們繼續痛
很快,車子駛離,偌大的沙灘上便剩下溫諾。
像睡著了的花瓣,再也不會醒。
林可兒接到助理的電話,“真的?霖哥哥真的把仍在那?”
“是的,我親眼看著沈總離開,我才走的。”
“呵呵……哈哈……”
溫諾,這可就怪不得我了。
日頭越來越烈,但沒多久,滾滾烏云籠罩,似有一場大暴雨。
也因著天氣的影響,海邊的風更大了,那卷起的浪花幾乎把溫諾吞沒。
反復的浪,溫諾的一點點向海里移……
馬路上,一輛豪車疾駛。
副駕駛座,林看外面的天,對后座的人說:“傅總,這天好像要下大雨。”
傅庭琛翻過一頁文件,眉眼未,好似沒聽見林的話。
林收回視線。
也就是他收回視線的時候,傅庭琛抬眸,看向窗外。
噼啪——
雨說下就下,豆子似的雨傾盆而下,天瞬間暗了。
只聽呲的一聲,一輛黑豪車停在馬路邊,一個人下車。
猜你喜歡
-
完結268 章

掌上尤物
白天,她是許清晝的私人秘書,負責替他賣命工作處理他接連不斷的小情兒。晚上,她頂著他未婚妻的身份任他呼來喝去,為所欲為。訂婚八年,許清晝的心上人一朝回歸,江羨被踹下許太太的位置,落得個眾人嘲笑奚落的下場。人人都等著看她好戲,江羨卻笑得風情萬種,當晚進酒吧,左擁右抱,勾來俊俏小狼狗,愉悅一整晚。她肆意卷土重來,各大財閥集團為爭搶她而大打出手;日日緋聞上頭條,追求者不斷。釣系小狼狗:“今晚約?房已開好等你來。”純情大男孩:“親愛的,打雷好怕你陪我睡。”快樂是江羨的,只有獨守空房的許清晝氣得兩眼發紅,...
55.9萬字8 63404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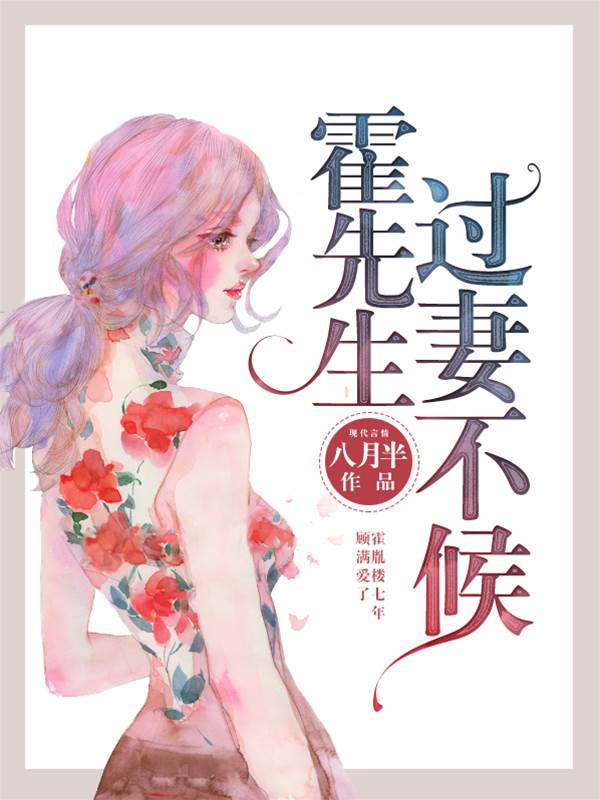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8451 -
完結108 章

哥哥他總想與我保持距離
曾經的他是一輪皎月,祈望驕陽;后來皎月已殘,又怎堪配驕陽?江歲和斯年第一次分別那年,她八歲,他十四。 彼時她緊緊地抱著他不撒手,口中歇斯底里的哭喊著:“年年哥哥,你別走!” 可他還是走了,只給她留下兩樣東西和一個約定。 十年后異地重逢, 他來機場接她, 他在她身后試探地喊她的名字:“江歲?” 她朝他不敢確定地問:“你是,斯年?” 兩個人面對著面,都差一點認不出彼此。 而此時他已跌落塵埃,卻依然對她痞笑著問:“呵,不認識了?” 匆匆一年,江歲像驕陽一樣,熾熱地追逐著他,溫暖著他。 而斯年卻深藏起對她深沉的感情,時刻想著與她保持好距離。 江歲可以忍受別人誤解她,嘲諷她,但她見不得有人在她面前羞辱和挑釁斯年。 斯年同樣可以忍受任何屈辱和諷刺,卻見不得江歲在他面前被人欺辱。 他竭盡一身力氣洗去泥濘,只為能站在她身邊。 然而造化弄人,他只能一次次親手將她推開。 江歲此生惟愿年年長相見。 斯年此生惟愿歲歲永平安。 前期:清純大學生女主vs多功能打工男主 后期:高級翻譯女主vs神秘總裁男主
29.4萬字8 1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