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產當天,我離婚了》 第1卷 第4章 我們離婚吧
霍九迅速反應,立馬撥了個電話,言簡意賅的跟對方說了兩句后掛斷,回過頭道:
“祁總,家庭醫生在路上了,馬上就到沈小姐那。”
“怎、怎麼辦,我好怕……宴禮,我的孩子……”人慌張的聲音持續的從手機里傳來,地攥著祁宴禮的心臟。
“楚楚,別怕。”祁宴禮語氣輕的安,“相信我,你和孩子都會沒事的。”
宋辭聽著平日里冷漠的男人此刻對另外一個人的聲安,心一點點的往下沉,全不自覺地繃,眼角酸得厲害。
原來,他也會這麼溫的哄人。只是,從來不會對這樣而已。
可是……祁宴禮,如果你知道我也懷過你的孩子,而你的孩子,因為你的冷漠離我們而去,你會后悔嗎?
很快,電話那端就傳來醫生匆匆趕到的聲音,跟沈楚語的慌神的哭音織在一起。
Advertisement
不多時,醫生檢查完,接過沈楚語的手機,道:“祁總,請放心,沈小姐應該是由于緒張導致的輕微出,只需要多臥床休息即可。”
祁晏禮聽完,蹙的眉頭這才松泛開。
坐在副駕駛座的霍九余不經意掃過后座眸底黯然的宋辭,他跟在祁宴禮邊五年,自然是知道沈楚語、宋辭和祁總三個人之間的事。
當年沈楚語出國,這才給了宋辭可乘之機,嫁祁家。如今沈楚語回國,宋辭早晚要讓出祁太太的位置的。
霍九忖了忖,問:“祁總,既然沈小姐那邊沒什麼事,還要先去那里嗎?”
“停車。”祁宴禮沉聲喝令。
‘哧’的一聲,邁赫急剎,猛地停在盤山公路。
宋辭沒有防備,整個人前傾,額頭咚的一下撞在副駕的椅背。
“下去!”
宋辭還沒從疼痛中緩過來,祁宴禮的命令就裹著森森冷氣砸了過來。
著腹部的指尖攥,緩緩直起,朝窗外看了一眼。
路燈昏暗不明,灑下微弱的芒,仿若風中殘燭,隨時都可能熄滅。周邊山林幽邃寂靜,那無盡的黑暗仿佛一只張著盆大口的巨,令人本能地生出恐懼。
宋辭下意識地想跟他商量:“祁宴禮,能不能先送我到市區?”
整段盤山公路,車程近四十分鐘,現在才剛過三分之一,而且周圍信號時好時壞,本打不到車,如果下車就只能走回去。
可以宋辭現在的狀況,連坐著都疼痛難忍。更別說走回去,那幾乎可以要走的半條命。
然而,祁宴禮毫不為所,無而厭煩地打斷:“宋辭,別讓我說第二遍!”
聞言,宋辭忽然自嘲一笑。
宋辭啊宋辭,你怎麼會天真的以為祁宴禮會關心你的死活?
剛剛那通電話,你明明聽的一清二楚。
他的溫、耐心,全都給了沈楚語,而留給你的只有冷漠與厭惡。
“霍九,把丟下去!”祁宴禮的聲音冷酷至極。
“不用勞煩,我自己下去。”
宋辭深呼吸,推開門,走下車。
還沒站穩,車門砰地被關上,邁赫猶如弦之箭,疾馳駛幽深的黑暗中。
宋辭被丟在原地,看著它越來越遠,最后消失在視線中。
抱著肚子蹲下,這兩天發生的種種猶如電影般,一幀幀的在腦海中回放。
泊、流產、他們并肩站立的報道、杜淑蘭的那句不配,還有祁宴禮的報復辱……
像是一把把利刃狠狠地刺進的心臟后,又被模糊地拔出。
“好疼……”
肚子疼,額頭疼,心臟也疼,疼至四肢百骸。
宋辭眼眶通紅,水汽彌漫,呢喃著疼,卻不知道究竟是哪里更疼些,只覺得呼吸都難。
就這樣蹲在那,不知過了多久間涌上來的腥味,拿出手機,指尖冰涼的在屏幕上敲出一句話發出去:
【祁宴禮,我們離婚吧。】
猜你喜歡
-
連載1504 章

夫人她A爆全世界
【甜寵,重生,虐渣,馬甲,團寵】“還逃嗎?”秦初使勁搖頭:“不逃了。”放著這麼好看的男人,她再逃可能眼睛真有病,前世,因錯信渣男賤女,身中劇毒鋃鐺入獄,自己最討厭的男人為替自己頂罪而死,秦初悔不當初,重回新婚夜,秦初緊抱前世被自己傷害的丈夫大腿,改變前世悲慘人生,成為眾人口中的滿級大佬。人前,秦初是眾人口中秦家蠢鈍如豬的丑女千金,人后,秦初是身披各種馬甲的大佬,某天,秦初馬甲被爆,全
135.4萬字8 16222 -
完結14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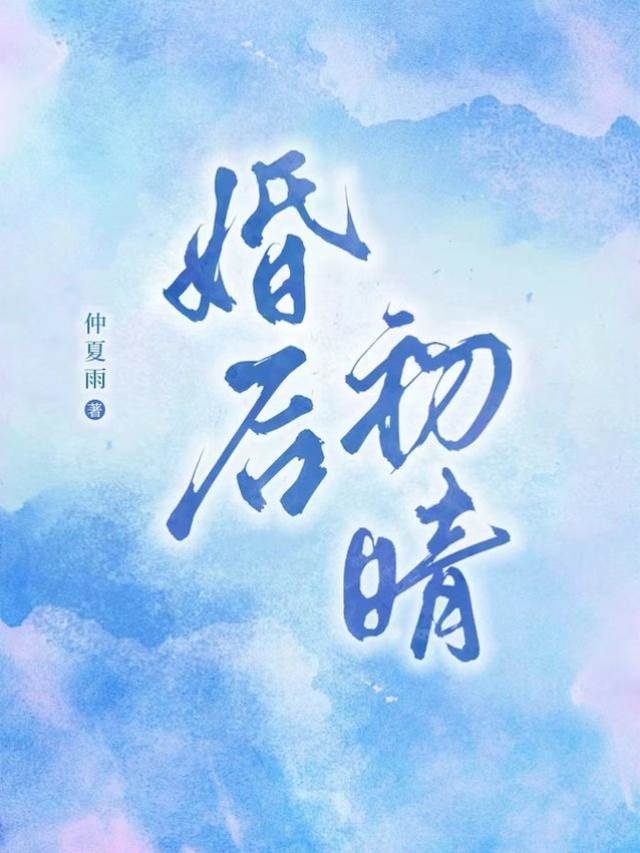
婚後初晴
沈頤喬和周沉是公認的神仙眷侶。在得知沈頤喬的白月光回國那日起,穩重自持的周沉變得坐立難安。朋友打趣,你們恩愛如此有什麽好擔心的?周沉暗自苦笑。他知道沈頤喬當初答應和他結婚,是因為他說:“不如我們試試,我不介意你心裏有他。”
27.2萬字8 4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