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寶喜歡野,甜喘陰鷙少年野爆了》 第1卷 第4章 聲音勾人
關閉手機,起往墨寒野的房間走去,絕對不是趁著他不在家, 去窺他的房間,而是他自己主說的, 藥箱在他房間里,只不過是去拿藥膏罷了。
簡潔的白房間,和房間的裝修差不多,只是,他房間的用料更朗。
白桌子上放著白藥箱,不著急拿走,而是起了別的心思,小心翼翼翻騰他的房間,其實也不知道翻騰什麼,但總覺在他房間里能翻到什麼東西。
好久后,發覺他是真干凈, 房間沒有一不堪。
站在原地,思索,既然他的房間里沒任何破綻,那麼是不是住的房間有問題呢?
溫汐汐拎起藥箱, 回到自己房間,進行地毯式搜尋,整個房間簡潔,一目了然,想要藏匿人,也不可能。
苦惱的坐在床上,眼眸冷不丁落在床頭的薰草燈,想到薰草有助睡眠的作用,若是薰草的劑量用量多,還可使人深度睡眠。
溫汐汐把薰草香薰燈拿下來,拆解,看到里面只有一些膏狀薰草,聞著味道沒任何問題。 可還是不敢掉以輕心,干脆將薰草燈的電源拔掉。
做好這一切,靜等夜晚的到來。
該吃晚飯的時間,墨寒野打來電話,說他晚上有應酬,無法回來,讓自己點餐吃,還說他報銷餐費。
Advertisement
溫汐汐聞言,眉開眼笑,點了平日里不舍得吃的日料,心滿意足飽餐一頓后,洗澡躺在床上。
夜里,溫汐汐是被墨寒野低沉嗓音吵醒,被他抱在懷里, 年眉眼出委屈,黑瞳里存著大顆珍珠,似要墜落,“寶寶,我很會賺錢,你不喜歡嗎?”
溫汐汐心驚,又跟白天的事重合。
眼球轉,床頭的薰草燈沒有亮起, 可依舊于似夢似幻,無法彈,只能任由墨寒野為所為。
晚上的墨寒野倒是跟小時一樣,很很乖很熱烈。
只是小時的他如此粘人,可以接。
他這麼大的人了,還如此。怎麼能了。
墨寒野手指癡迷的臉頰:“汐汐,好好漂亮, 我最喜歡汐汐了,汐汐可以嫁給我嗎?讓我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再這麼下去,要窒息。
試圖張開,呵斥他不要再自己,可是微微張開,發不出任何聲音。
“寶寶,是想被我親嗎?”
“寶寶,謝謝你小時候照顧我,那時候我就發誓,要娶你為妻,照顧你一輩子。”
溫汐汐:“……”
這個家伙胡說什麼?!
小時的墨寒野一副三魂六魄不歸位的樣子,跟小貓小狗似,整天只會跟在屁后面傻乎乎姐姐,明明八歲的孩子,卻只有兩歲的智商,怎麼可能會想著娶?打死都不信。
溫汐汐醒來,已是第二天。
昨晚的記憶清晰在腦海里留存,捂住滾燙雙頰,昨晚的墨寒野迫和他在夢里結婚,還說等真結婚那天,要舉辦中式婚禮,大紅嫁, 才會長長久久,生生世世。
溫汐汐竟也忍不住多想。
嗚,不會被夜晚的墨寒野給洗腦了吧?
溫汐汐在床上翻來覆去想許久,越想越不對勁 ,跳下床,檢查昨晚被自己拔掉的香薰燈,發覺電源是拔掉的,還有門窗依舊沒有打開的痕跡,從門窗里小心出昨晚臨睡前放下的長發,5長發,完好無損。
苦惱道:“我該不會遇到鬼了吧。”
可,雖說別墅很大很空曠,但這里可是墨宅。
如此大富大貴的風水寶地,應當不會有任何妖魔鬼怪敢靠近啊。
“啊啊啊,我是怎麼了?胡思想什麼,朗朗乾坤怎麼會有那些七八糟的東西。”
叮鈴鈴,溫汐汐手機響起,是好友林珊要約一起去看電影《大幻師》,說是劇超彩,講的是奇人異士,斗幻的故事。
“幻?”忍不住心驚。
林珊祖上是道士發家,對這種類型的電影極喜,激的說:“我聽我爸說,這個電影拍的超級真實,我們一起去看吧。”
“好。 ”溫汐汐答應下來。
臨出門,見墨寒野還在家,不免有點好奇:“你今天沒去公司?”
“嗯,專門休息一天,陪你。免得某人在我媽媽回來,告我狀。”
可讓墨寒野猜對了,早決定在墨阿姨回來后,告他的狀。
“不好意思呀,我約好友去看電影。”溫汐汐上說著抱歉,實際,臉上一點抱歉的樣子也沒。
墨寒野挑下眉,懶散道:“那祝你玩的開心,我正巧也要去見朋友,送你一程。”
“好。”有免費的車,是一定要坐的。
墨寒野將溫汐汐送到電影院門口,看到等待的人是個孩,表稍微輕松不,他笑道:“你的同學長的可。”
“哎哎,你別打我朋友主意,人很單純。”
“你哪點看出我不單純?”墨寒野忽然問,他帥氣面容干干凈凈,眉眼出清澈,整個臉上,赫然印著,單純,兩個字。
要是以往,溫汐汐絕對不會將他和別的聯系到一起,可連續三個晚上發生的事,讓的腦海里充斥著他眼睛通紅,的樣子。
“你這種長相,太招蜂引蝶, 怎麼可能單純。”
墨寒野干脆認真請教,“長的帥,也有錯?”
“嗯,你微信里那麼多,早晚有一天會犯錯。”
墨寒野拿出手機,遞給,“早刪干凈了,我說了,我對那些孩一點興趣也沒,并且我手機以后再也不會加任何生。”
眼睛直勾勾盯著,不放過任何細微的小作。
溫汐汐盯著他空的微信好有列表,赫然只有。
沒什麼底氣道:“其實,我們快要上大學啦, 談也沒什麼,只要不來就好,我還打算大學談個呢。”
“你不是要賺錢嗎?志向怎麼變那麼快?”墨寒野似沒打算放過的意思。
猜你喜歡
-
完結28 章

耳朵說它想認識你
蒲桃聽見了一個讓她陷入熱戀的聲音,她夜不能寐,第二天,她偷偷私信聲音的主人:騷擾你並非我本意,是耳朵說它想認識你。-程宿遇見了一個膽大包天的姑娘,死乞白賴逼他交出微信就算了,還要他每天跟她語音說晚安。後來他想,賣聲賣了這麼久,不當她男朋友豈不是很虧。一天睡前,他說:“我不想被白嫖了。”姑娘嚇得連滾帶爬,翌日去他直播間送了大把禮物。他報出她ID:“你知道我說的不是這個。”男主業餘CV,非商配大佬,寫著玩;女追男,小甜餅,緣更,不V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耳朵說它想認識你》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臉書和推特裡的朋友推薦哦!
6.6萬字8 5275 -
完結103 章

穿成大佬的聯姻對象
執歡穿書了,穿成了替逃婚女主嫁給豪門大佬的女配,文中女配一結婚,就經歷綁架、仇殺一系列的慘事,最后還被大佬的追求者殺掉了 執歡不想這麼慘,所以她先女主一步逃了,逃走后救了一個受重傷的男人,男人身高腿長、英俊又有錢,同居一段時間后,她一個沒把持住… 一夜之后,她無意發現男人的真實身份,就是自己的聯姻對象—— 男人:結婚吧 執歡:不了吧,其實我就是個不走心的渣女 男人:? 男人掉馬后,執歡苦逼的溜走,五個月后喪眉搭眼的頂著肚子回到家,結果第二天男人就上門逼婚了 父母:歡歡現在懷孕了,恐怕不適合嫁人… 男人表情陰晴不定:沒事,反正我是不走心的渣男 執歡:… 簡單來說,這是一個‘努力逃婚最后卻懷了結婚對象崽崽、兜兜轉轉還是嫁給他’的故事,沙雕小甜餅 外表清純實則沙雕女主VS非典型霸總男主
30.1萬字8 15224 -
完結147 章

鹿生
很多人說見過愛情,林鹿說她隻見過性——食色,性也。
28.9萬字8 9248 -
完結599 章

離職后我被前上司痛哭糾纏
她是他的特別助理,跟了他整整七年,他卻一把牌直接將她輸給了別人。藍星若也不是吃素的,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她一封辭呈丟下,瀟灑離開。坐擁一億粉絲的她,富二代和世界冠軍全都過來獻殷勤,全球各大品牌爭先要和她合作。可盛景屹卻發現自己整個世界都不好了。“回來吧,年薪一個億。”藍星若莞爾一笑,“盛總,您是要和我合作嗎?我的檔期已經安排在了一個月后,咱們這關系,你沒資格插隊。”某直播間里。“想要我身后這個男人?三,二,一,給我上鏈接!”
109.3萬字5 40916 -
完結19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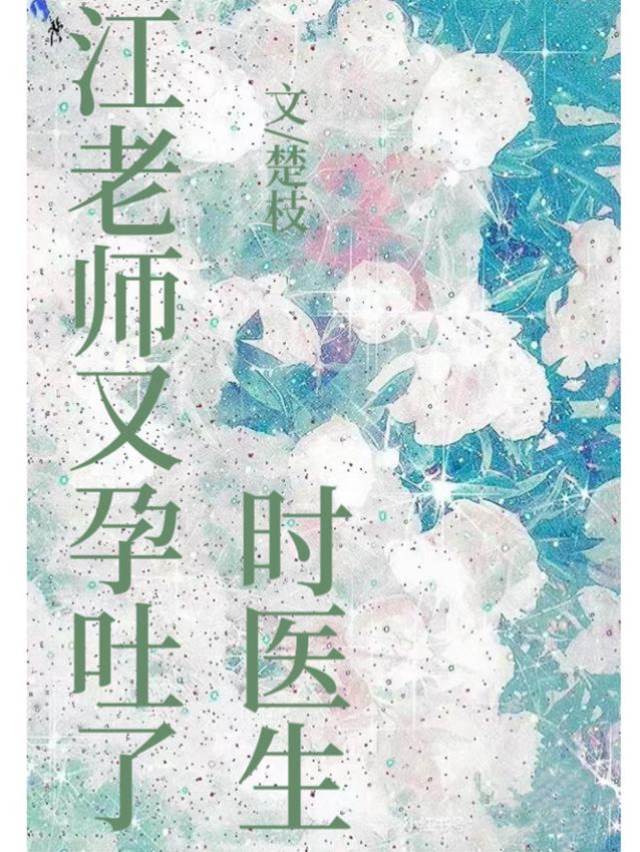
時醫生,江老師又孕吐了
【雙初戀:意外懷孕 先婚後愛 暗戀 甜寵 治愈】男主:高冷 控製欲 占有欲 禁欲撩人的醫生女主:純欲嬌軟大美人 內向善良溫暖的老師*被好友背叛設計,江知念意外懷了時曄的孩子,麵對暗戀多年的男神,她原本打算一個人默默承擔一切,結果男神竟然主動跟她求婚!*江知念原以為兩人會是貌合神離的契約夫妻,結果時曄竟然對她越來越好,害她一步一步沉淪其中。“怎麽又哭了。”他從口袋裏拿出一根棒棒糖,“吃糖嗎?”“這不是哄小孩的嗎?”“對啊,所以我拿來哄你。”*他們都不是完美的人,缺失的童年,不被接受的少數,讓兩個人彼此治愈。“我……真的能成為一個好爸爸嗎?”江知念抓著他的手,放到自己肚子上:“時曄,你摸摸,寶寶動了。”*堅定的,溫柔的。像夏日晚風,落日餘暉,所有人都見證了它的動人,可這一刻的溫柔繾綣卻隻屬於你。雖然二十歲的時曄沒有聽到,但二十五歲的時曄聽到了。他替他接受了這份遲到的心意。*因為你,從此生活隻有晴天,沒有風雨。我永遠相信你,正如我愛你。*「甜蜜懷孕日常,溫馨生活向,有一點點波動,但是兩個人都長嘴,彼此相信。」「小夫妻從陌生到熟悉,慢慢磨合,彼此相愛,相互治愈,細水長流的故事。」
35萬字8 30977 -
完結20 章

傾其所有去愛你(平裝版)
【霸道總裁+現言甜寵+破鏡重圓】落難千金自立自強,傲嬌總裁甜寵撐腰!【霸道總裁+現言甜寵+破鏡重圓】落難千金自立自強,傲嬌總裁甜寵撐腰!龜毛客人VS酒店經理,冤家互懟,情定大酒店! 酒店客房部副經理姜幾許在一次工作中遇到了傲驕龜毛的總統套房客人季東霆。姜幾許應付著季東霆的“百般刁難”,也發現了季東霆深情和孩子氣的一面。季東霆在相處中喜歡上了這個倔強獨立的“小管家”。姜幾許清醒地認識到兩人之間的差距,拒絕了季東霆的示愛,季東霆心灰意冷回到倫敦。不久后,兩人意外在倫敦重逢,這次姜幾許終于直視內心,答應了季東霆的追求。正在季東霆籌備盛大的求婚儀式時,姜幾許卻與前男友沈珩不告而別。原來沈珩與姜幾許青梅竹馬,在姜幾許家破產后兩人被迫分手。季東霆吃醋不已,生氣中錯過了姜幾許的求助……
28.4萬字8 1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