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乖入局,驕肆大佬無處不低頭》 第1卷 第14章 你就是看人家姜郁嬌軟可欺
掀開帳簾,撲面一夾雜汗味的熱,還有鐵板煎的油滋聲。
瞧著那個趴在地上的男人,賀斂淺笑著挑眉,順著踩在他背上的那只作戰靴向上看,對視到一雙如鷹隼般的眼。
這人重新拿起火盆里燒紅的鐵鉗子,在眼前端詳幾秒,猛地按在男人的背部,刺耳的滋啦響起,男人咬著是不吭一聲。
賀斂的視線隨之往右,看到謝輕舟。
他穿著一件黑的皮夾克,里是空的,蠻橫的上滿是猙獰傷疤,蹬了一下面前的桌子,震得那支格克手槍咯噔一聲。
謝輕舟:“賀斂,你膽子不小啊,孤營。”
賀斂將外套搭在一旁,在對面坐下,不疾不徐的挽著襯衫袖子,那散漫又泰然的模樣看的謝輕舟愈發不爽。
“和境外的悍匪勾肩搭背,姓謝的,你也比我想象的有本事。”
聞言,謝輕舟瞥眼:“佐賀是我的老朋友了。”
賀斂氣定神閑,拿起木桌上的煙盒掏了一顆,彎在火盆里點燃,隨后嵌進邊深深的吸了一口:“既然是你的老朋友,那就讓他把我的人放了吧。”
佐賀無聊的咂,扔下火鉗子,撲的火盆里涌出一刺鼻的燒炭味,隨后將腳下的男人踢向賀斂。
男人總算是呼了口氣,抬起頭,睜開腫脹的眼:“……會長。”
賀斂手,將他拽起來:“你先出去。”
Advertisement
男人明顯是擔心他的境,在那兩人看不到的地方輕輕搖頭。
賀斂見狀,了莊雨眠進來將人拖走。
“賀先生,我希你的人不要總是在我的營地外晃。”佐賀往里扔了一牙簽,“咱們當初可說好了,這片法外的灰地帶,咱們互不干涉。”
賀斂笑的肆意:“是嗎?臥佛金礦百里之,不許出現你們沙蟲的人,這也是你曾經承諾的,到底是誰不守規矩在先?”
佐賀嚼了兩下,將牙簽吐了,拍了一下謝輕舟的背。
那人往前伏,將一切挑明:“賀斂,你他媽離我妹妹遠點!”
賀斂吐了口煙,男人致的五被煙霧遮住,隨后又被口中的譏諷劃破:“這話你去和謝希苒說,又不是我求著給我的。”
謝輕舟濃眉倒豎,抄起桌上的格克手槍對準眼前的人,一想到妹妹為了賀斂要死要活的,他恨不得立刻開槍!
賀斂毫不懼,反而挑釁:“你想好了,你要是開槍的話,你那個癡的妹妹會傷心絕的。”
他甚至恣的發笑:“輕舟,你不知道有多喜歡我。”
‘砰!’
巨大的槍聲引得外面眾人一驚,子彈穿帳布而過,莊雨眠猛然回頭,帶著人沖了進來!
舉著手里的P229型手槍,張的環視帳!
“會長!”
謝輕舟氣的額頭青筋高鼓,也抿的發紫,旋即點點頭:“好啊,賀斂,你不愧是為了繼承權,連長房堂哥都能殺的人,行,算你狠!”
他說完繃起臉,將槍擲在一旁,踢翻地上的火盆往外走,臨了還狠狠地撞了一下莊雨眠。
人柳眉微蹙,看向賀斂。
男人著最后一口煙,墨發下的眼毫無波瀾,打出的彈孔距離他不到五厘米,進來的伏在他的耳尖,映出的紅。
“會長,差不多了。”
莊雨眠低嗓音。
賀斂將煙頭扔進木桌上的鋼制水杯里,拿起一旁的外套起,頎長的影子在佐賀的臉上。
他淡笑著:“既然事已經解決了,希佐先生以后遵守咱們的規矩,就算和謝輕舟關系再好,想必你也不想再和壁堡手了吧。”
佐賀了一下牙床,挑眉示意。
他的確是后悔了,這次收了謝輕舟的錢去挑釁賀斂的維和工會,結果損失了幾十個人和兩個集裝箱的彈藥,本不敷出。
還被大頭目痛罵一頓。
甚至連唯一一個抓到的下屬都還給賀斂了。
“賀先生。”佐賀起,出糙礪的手,“您慢走。”
賀斂掃了一眼他掌心的泥,轉出帳。
莊雨眠趕檢查他的況。
賀斂沒,被太曬得有些煩躁,抬起頭,微瞇著眼睛。
忽而想到洋城的霧靄茫茫,他推開莊雨眠的手,悶聲嘀咕。
“這金州,怎麼就不下雨呢?”
-
晚九點,壁堡。
賀斂在淋浴下站著,淡漠的視線盯著周遭升騰的霧氣,有些失神。
真是中了邪。
一看到白煙白霧的,他就會想起那個小傻子。
煩躁的關了水閥,他直接裹著浴袍進了休息室,沈津正端坐在沙發上等他,聞聲抬頭:“謝輕舟鬧得哪出?過去這麼多年了,怎麼又和沙蟲的人搞到一起了?”
賀斂趿著拖鞋,踩出一溜水痕:“為了他妹妹。”
沈津:“謝希苒?”
賀斂坐在他旁邊,仰頭手,修長的指尖還勾了勾。
沈津厭棄的拿起桌上的煙塞給他:“你就不能和謝希苒說明白?”
賀斂低頭點煙,碎發的水跌在掌背,順著鼓起的管落。
聽到這話,他擰眉道:“我還要怎麼說清楚?我就差拿槍頂著腦門了,結果說什麼,就算我賀斂是坨大便都不嫌棄!”
沈津:“……”
“天跟個蒼蠅似的在我耳邊嗡嗡,連話都說不明白。”賀斂嘀咕,“還不如一個……傻子。”
最后兩個字說的聲音漸小。
“。”
賀斂往后一靠,恨不得一口把煙吸到頭。
沈津在鏡片后翻了一個白眼,提到姜郁,他拿出一份鑒定報告:“對了,你讓我送去檢測的那罐料結果出來了。”
賀斂看也不看:“念。”
沈津:“我該你的啊,自己看!”
真把他堂堂的沈家大爺當小書了?
他把報告摔在桌子上。
賀斂紋不。
沈津深吸一口氣,將文件拿起來,罵了一句畜生,接著自己又檢查了一下,才說道:“就是普通的油畫料,只不過里面放了點東西。”
“什麼東西?”
“給種豬催的噴劑。”
“……”
賀斂角輕微一。
種豬。
給種豬用的,用他上了。
沈津倒是沒什麼反應,畢竟報告一出來他就和技員笑的差不多了。
“其實這種東西對人達不到同樣的效果。”他說,“就算劑量很大。”
賀斂睨向他:“你好像話里有話。”
沈津將報告摔在他上:“所以,承認吧賀斂,你那晚本就沒中招,你只是見到人家姜郁可欺,本能的大發了。”
“賀斂,你真他媽是個畜生。”
猜你喜歡
-
完結3579 章

韓先生情謀已久
“收留我,讓我做什麼都行!”前世她被繼妹和渣男陷害入獄,出獄後留給她的隻剩親生母親的墓碑。看著渣男賤女和親爹後媽一家團圓,她一把大火與渣男和繼妹同歸於盡。再醒來,重新回到被陷害的那天,她果斷跳窗爬到隔壁,抱緊隔壁男人的大長腿。卻沒想到,大長腿的主人竟是上一世那讓她遙不可及的絕色男神。這一次,她一定擦亮眼睛,讓 韓先生情謀已久,恍若晨曦,
354.7萬字8 57206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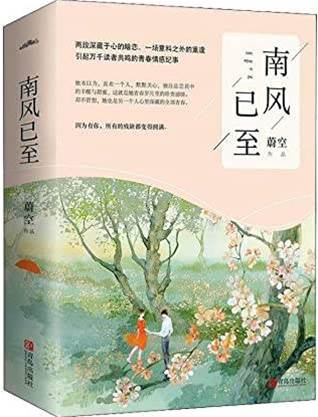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491 章

裴教授,你行不行啊
絕世小甜文,年齡差,先婚后愛,1v1雙潔,斯文敗類教授X古靈精怪富家女。劇情一:葉允澄可憐巴巴的看著裴修言:“老公,我作業沒寫完,你跟我們導員熟,你跟她說一聲讓她別檢查作業了好不好。”裴修言抿唇不說話。結果第二天,導員只檢查了葉允澄一個人的作業...下班回家的裴修言發現家空了一大半,葉允澄不見了...
97萬字8 44785 -
完結183 章

乖吝
【甜寵&雙暗戀&校園到婚紗&雙潔&救贖】(低調清冷富家大小姐&痞壞不羈深情男)高三那年,轉學至魔都的溫歲晚喜歡上了同桌校霸沈熾。所有人都說沈熾是個混不吝,打架斗毆混跡市井,只有溫歲晚知道,那個渾身是刺的少年骨子里有多溫柔。他們約好上同一所大學,在高考那天她卻食言了。再次相見,他是帝都美術學院的天才畫手,是接她入學的大二學長。所有人都說學生會副會長沈熾為人冷漠,高不可攀。卻在某天看到那個矜貴如神袛的天才少年將一個精致瓷娃娃抵在墻角,紅著眼眶輕哄:“晚晚乖,跟哥哥在一起,命都給你~”【你往前走,我在身后...
32.4萬字8 9635 -
完結872 章

誘捕玫瑰
五年前,溫棉被人戳着脊樑骨,背上爬養兄牀的罵名。 所有人都說她是個白眼狼,不懂得感激裴家賜她新生,反而恩將仇報。 只有她自己知道,這所謂的恩賜,只是一場深不見底的人間煉獄。 五年的磋磨,溫棉險些死在國外。 重新回來時,她煥然一新,發誓要讓裴家的所有人付出代價。 本以爲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死局。 卻沒想到,這個將她送到國外的養兄,卻跟個甩不掉的牛皮糖一樣跟在身後。 她殺人,他遞刀,她報仇,他滅口。 終於,溫棉忍不住了—— “你到底要幹什麼?” 而那隱忍多年的男人終於露出了尾巴:“看不出來嗎?我都是爲了你。”
84.4萬字8 21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