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后,夫人她艷殺四方》 第5章 需不需要送她一口棺材?
杜若心聽到急剎車,和一道悉的聲音喚那一秒,淚水忽的止住。
榮敬揚?
不想讓他看到自己的懦弱,迅速掉眼淚。
“你——”
榮敬揚扭過人,森寒的目在對上赤紅的雙眼時,神一滯,“哭了?”
杜若心別開眼,“沒有。”
打死也不承認自己那麼沒有骨氣。
杜若心心一橫,眼一凜,“榮先生這麼急急忙忙,艾薇是眼瞎了?還是死了?”
“好歹相識一場,請問,需不需要我送一口棺材?”
榮敬揚:“…………”
這人!
心底那一不忍瞬間煙消云散,他著的下,臉越發沉,“榮太太,注意你的修養。”
杜若心盯著男人完的俊臉,雖然他一副要碎了的可怕樣子,但還是不由自主心跳加快。
榮敬揚太帥了。
深邃似有魔力的黑眸,高的鼻子,冷冽而的……
不行,不能被他迷。
再多看一秒,杜若心毫不懷疑自己的節又會掉。
Advertisement
扭過頭,撇撇,“我的修養很好啊,我剛不是用了‘請問’?”
“還有,我決定了,跟你離婚。”
“再也不是什麼榮太太。”
離婚?
人的話榮敬揚眼底過一抹錯愕。
他——沒聽錯?
杜若心要跟他離婚?
這個他到失去自我,甚至為了他愿意去死的人,要跟他離婚?
錯愕只是一瞬,榮敬揚就否決了。
杜若心追他追了五年,用盡一切手段,甚至不惜毀了孩兒最看重的名節,睡他床上。
……
怎會離開他?
所以,杜若心這麼說,只是為了逃避懲罰,只是為了跟他耍無賴。
榮敬揚面冰冷而漠然道,“杜若心,鬧脾氣也看場合,你今天的行為——”
“是潑婦嗎?”杜若心苦的替他說道。
“怎樣?”
“有人勾搭我老公,我沒潑硫酸,沒找人服,沒往死里揍,就是我涵養高了。”
榮敬揚:“——”
怎麼聽著一子流氓做派?
……
不是一向優雅溫,善解人意,知書達理嗎?
榮敬揚被彪悍的模樣愕住了。
“榮敬揚我告訴你,我不止今天是潑婦,以后的每一天都是。”
“誰敢接近你一米,我削死!”
不是。
都下決心要離婚了,放什麼狠話?
杜若心努了努,有點厭棄自己的心直口快。
【往后余生,榮先生,你想跟哪個人好就跟哪個人好,我不在乎。】
【我——】
【放你自由。】
榮敬揚原本錯愕的目在聽到的話時,出鄙夷的眼神。
這個人心眼兒忒多,又在打什麼歪主意?
他強勢直視,“看著我說話!”
杜若心猝不及防對上男人深邃而冷冽的墨瞳,心突突跳了下。
不行啊,不能看他,一看他帥到不可思議的臉,瞬間就沒了脾氣。
七年來對他的,不能說戒就戒。
至,理智告訴要戒,但心不控制。
就像罌粟一樣,榮敬揚就是拔不了,摘不掉,一就痛不生的癮。
可是再痛,該斷也得斷。
杜若心做好了戒毒戒癮的準備,即使過程傷筋骨。
再度別開眼。
明明還是放狠話,但語氣了些,像是最后的掙扎,“不看,你那麼帥,我會口是心非!”
“……”
榮敬揚冷厲的眸因突如其來的表白變得和幾分。
果然,杜若心還是杜若心。
他勾了勾,嗓音磁而低啞,“我不計較你燒房子的事,但艾薇,你得跟道歉。”
杜若心口一震:榮敬揚,你夠了,總是知道怎麼踐踏我的尊嚴,怎麼我的心。
要不是打不過你……
手腕上那道不讓掙開的強勁力道杜若心清楚,榮敬揚是鐵了心要道歉。
深吸一口氣,制著噬心的痛,小聲道,“我走累了,上車吧。”
榮敬揚拉走向副駕駛。
杜若心蹲著,不讓他拽,“吶。”指向擱在一旁的行李箱,“你搬上車。”
榮敬揚掃一眼,沒有猶豫的走至行李箱前,搬到后備箱。
杜若心看著他的背影,再度深吸一口氣。
兩年多來,他說到做到,給,給錢花,給禮……真的是給了一個丈夫能給妻子的一切。
唯獨沒有心。
唉——
深深地看他一眼,杜若心坐上駕駛位。
別了,榮敬揚。
別了,我的婚姻。
別了,我所有的炙熱的。
待榮敬揚關上后備箱,杜若心油門踩到底,轎車像離箭之弦眨眼消失拐角。
榮敬揚:“……”
冷厲、愕然、詫異從眼底掠過,但最后,化作一抹探究。
他的妻子,在他面前裝了七年“溫恬靜”人設的乖乖妻子,好像,不一樣了?
氣息冷厲的掏出手機,他給管家打電話,讓管家開一輛跑車出來,隨即打開手機定位系統,追蹤杜若心。
猜你喜歡
-
完結2426 章

總裁的嬌寵妻
她本是名門千金,卻一生顛沛流離,被親人找回,卻慘遭毀容,最終被囚禁地下室,受盡折磨,恨極而亡。 夾著滿腔怨恨,重生歸來,鳳凰浴火,涅槃重生。 神秘鑰匙打開異能空間,這一世,她依舊慘遭遺棄,然置之死地而后生,她不會再重蹈覆撤,她要讓那些曾經踐踏過她的人,付出代價。從此以后,醫學界多了一個神秘的少女神醫,商界多了一個神秘鬼才....
243.7萬字8 214071 -
完結303 章

豪門盛寵之陸總寵上癮
他是海城最尊貴的男人,翻手可顛覆海城風雨,卻獨寵她一人。 “陸總,許小姐又有緋聞傳出。” 男人眼睛未抬半分,落下兩字“封殺。” “陸總,許小姐想自己當導演拍新戲。” “投資,她想要天下的星星也給她摘下來。” “陸總,許小姐不愿意結婚。” 男人挑眉抬頭,將女人強行連哄帶騙押到了民政局“女人,玩夠了娛樂圈就乖乖和我結婚,我寵你一世。”
67.5萬字8 27643 -
完結388 章

愛你日久彌深
叢歡只是想找個薪水豐厚一點的兼職,才去當禮儀小姐,不料竟撞見了自家男人陸繹的相親現場。叢歡:陸先生,你這樣追女人是不行的。陸繹謔笑冷諷:比不上你,像你這樣倒追男人的女人,只會讓人看不起。雙份工資打給你,立刻離開,別在這礙眼。叢歡:好好好,我這就走,祝你成功追美、永結同心。陸繹:就這麼將自己心愛的男人拱手讓人,你所謂的愛果然都是假的。叢歡忍無可忍:狗男人,到底想怎樣!
74.5萬字8 578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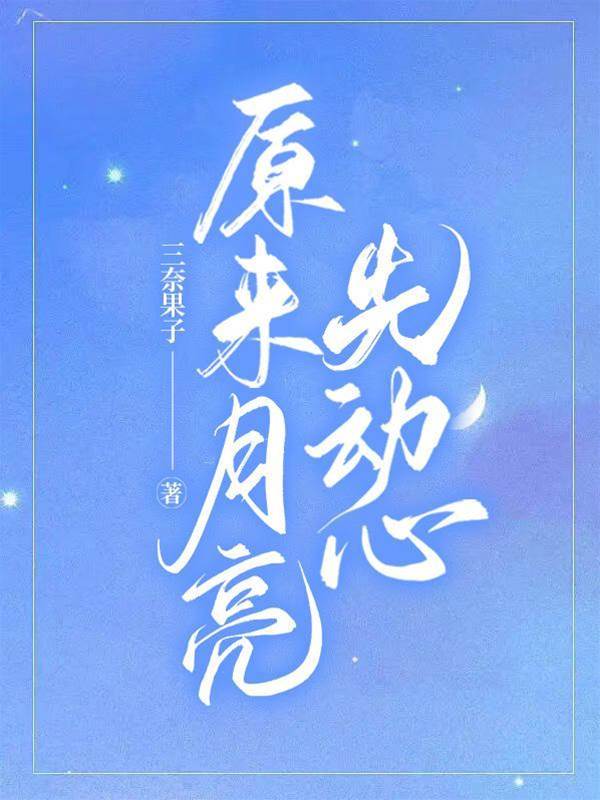
原來月亮先動心
【已簽約出版】原名:《喝醉後,我錯撩了閨蜜的小叔》【蘇撩 甜寵 教授 七歲年齡差 校園 救贖】【蘇撩腹黑小叔X古靈精怪少女】江落是十足的手控,為了一張手照,搭訕了一位帥哥,不料事後發現,對方居然是她閨蜜的小叔!江落腰板挺直,站姿乖巧:“小、小叔好。”……多年後,南大突然傳出生物學係的高嶺之花傅教授已經結婚的謠言。同事:“傅教授,這些謠言都是空穴來風,你別信……”“澄清一下,這不是謠言,”傅紀行冷靜補充,“我確實結婚了。”!!!江落跟傅紀行扯證時,她正讀大四。扯完證回去的路上,男人手裏拿著小本子,溫聲提醒:“喊了我這麼多年的小叔,是不是該換一下稱呼了?”“什、什麼稱呼?”“比如……”男人的吻落在她唇上——“老公。”
21.2萬字8 8278 -
完結506 章

離婚止損
兩人的娃娃親在景嶢這裏根本沒當回事,上學時談了一段張揚且無疾而終的戀愛,迫於家人的壓力,最後還是跟褚汐提了結婚。兩人結婚之後像普通人一樣結婚生女。外人看來雙方感情穩定,家庭和睦,朋友中間的模範夫妻。兩人婚姻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褚汐打小性格溫柔,品學兼優,自從知道自己跟景嶢有娃娃親的時候,就滿心歡喜的等著兩人結婚,總以為兩人一輩子都會這樣在一起。偶然的一天,聽到景嶢用一種意氣風發且張揚的聲音跟自己的母親說他談戀愛了,有喜歡的人,絕對不會娶她。此後再見麵,褚汐保持合適的距離,遇見了合適的人也開始了一段戀愛。兩個人的戀愛結果均以失敗告終,景嶢問她要不要結婚,衝動之下褚汐同意了。衝動之下的婚姻,意外來臨的孩子,丈夫白月光的挑釁,都讓她筋疲力盡。心灰意冷之後提出離婚,再遭拒絕,曆經波折之後達到目的,她以為兩人這輩子的牽掛就剩孩子了。離婚後的景嶢不似她以為的終於能跟白月光再續前緣,而是開始不停的在她麵前找存在感!
99.2萬字8.18 228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