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先生別虐了,夫人白月光不是你》 第14章 放過你,讓你去找別人?
溫走時拿走了房卡,此刻,屋子裏一片漆黑。
打開門板走進去,隨後背靠著門板,肩膀細細抖了起來。
厚重的窗簾遮住了窗外月,小小的房間裏手不見五指。
似乎也隻有在這樣的一片漆黑下,整個人融黑夜中才能放鬆下來。
淚水無聲過麵頰,吸了吸鼻子,正要抬手開燈,一道聲音驀地響起,驚地將整個人釘在了原地!
“溫,你知不知道我在這兒等了你多久?”
是霍斯年!
他怎麽來的,房卡被拿走了,他為什麽能進得來?
“別想了,隻要我想,沒有地方進不去!”
是啊,他是霍斯年!
他有份有權勢。
可他為什麽非要這樣出現!
原本還能製住的緒,此刻盡數崩塌。
“霍斯年,你太過分了!”
嗬……
他過分?
他為了在這兒等回來,一個姿勢保持不足足坐了快三個小時!
他過分?
“溫,你別得寸進尺!”
眼角淚痕未幹,溫無語的笑了:“我過分,我做了什麽?我有像你一樣不經過你的同意把你外婆帶走?”
“我外婆早歸西了!”
“我有像你這樣不經過你的同意著進你書房?”
“我……我有這樣嚇過你嗎?”
口劇烈起伏,溫嗓音尖銳。
“霍斯年,我以前怎麽就沒發現你這個人這麽可惡!這麽討人厭!”
Advertisement
“我可惡!我討人厭?”
霍斯年被溫吼的麵鐵青。
隻不過這些神再黑暗中看不真切。
他赫然起,角勾著冷笑,一步步朝著門口走去。
“你終於說了實話,我不披著沈喻寒的影子,就這麽讓你看不上!”
聲音近,連帶著那人不可忽視的氣息也寸寸下。
溫隻覺得不過氣來。
想後退,卻退無可退,想逃離,卻被他摁著肩膀圈。
方才巷子裏發生的事清晰的在腦海中的浮現。
眼眶紅的不像話。
可怕恐懼的事當做沒發生過的忘掉就好了啊。
可為什麽要重新發生呢?
“你放開我!”
溫緒激,忽地一把推開霍斯年。
霍斯年沒想過自己那向來溫,從未發過脾氣的小妻會吼他推他。
還被推開了。
他好生氣!
氣的想要將人一把死!
可又好難過,腔那躁起伏的異樣緒又是因為什麽?
“你就這麽不想我靠近?”
“是!”
“你討厭我!”
“對!”
“你找了其他男人?”忽然,霍斯年不知什麽時候又近,聲線低沉,氣息拂在溫脖頸間。
他瓣蠕,微涼的。
的。
一下一下的折磨人。
像是野在對即將口的餐尋找合適的下位置。
溫僵,整個人戰栗不止。
屏住呼吸,整個人連也不敢了。
“說,是誰?”
“你在說什麽,我聽不懂。”
溫穩著緒,想要手開燈。
卻被他殘忍的拽過來,他大掌牢牢握著的肩膀。
“是聽不懂還是不敢說?”
溫氣到發抖。
到底是做了什麽不敢說?
“霍斯年,算我求你了,放過我吧!”
“放過你?”霍斯年那眼眸沉沉如水,鼻息間嗅著溫上那帶著其他男人的氣息。
他眼底醞釀著狂風暴雨。
可有偏執的不死心,還抱著那樣一期待,想著能說幾句,為自己開一些。
可是沒有!
沒有!
“讓你去找野男人嗎!?”
盛著狂風暴雨的話語落下,上的男士外套被他狠狠扯下。
他舌尖頂著後牙槽,在溫的痛呼聲中毫不留在肩膀留下屬於自己的印記。
“霍斯年!放開!”
“你個瘋子!瘋子!”
“你放開啊……”
淚水奪眶而出,的哭喊打罵不起任何作用。
他太狠了!
出手沒有半分。
太痛了!
也許是置一片黑暗。
溫更加絕,耳邊一時間隻剩下黃三人的聲音!
為什麽!
為什麽要承這一切!
腦袋被大掌摁著,冰涼的門板幾乎要讓自己五變形。淚水越來越多,視線模糊,溫聽到了易鳴羨的聲音。
“溫,你睡了嗎?”
他在敲門,還出了聲音。
小旅館太劣質,毫無隔音設備。
霍斯年停下來,他修長白玉指尖纏繞著溫腦後一縷長發。
那海藻般的長發墜在一片冰玉骨中,呼吸間輕,的驚心魄。
他饒有興致的聽著。
門外,易鳴羨皺著眉未曾舒展。
他在將溫送到了樓梯口後便出門看著了。
他等了許久,一直未曾等到溫房間裏的燈打開。
那一瞬,他心底不安,總覺得溫像是發生了什麽。
他在樓下來回走,不經意間一撇,竟看到了路邊停著的那輛全球限量版幻影。
炫酷地黑車幾乎融黑夜,它就那麽低調無聲的停在黑暗。
可它價值擺在那兒,易鳴羨本無法忽視。
他確認後瞳孔驟,他心裏似乎明白了什麽……
那天,帶著溫蔥玫瑰莊園出來時他就明白了什麽。
先前給他打電話的人未曾告訴他全部,他隻知道溫在自己一無所知的況下嫁人了。
嫁人後過的不幸福,想離婚,但哪位。權勢份尊貴的丈夫不同意。
所以,要自由,要走。
易鳴羨聽了電話裏人的話,當時便一口答應下來。
其實,在知道了溫嫁人的那一刻。
所有不該有的心思都該停止。
他也不該卷這場是非趟這個洪水,可他發現自己本拿溫沒有辦法,他拒絕不了的任何求助。
所以,他幫了那個忙。
在看到玫瑰莊園時也猜到了那個人的份。
確實不是溫能夠抗衡的。
本以為走了便結束了。
可是沒想到那個男人能跟到這裏。
想到這兒,易鳴羨敲門的聲音更大了。
“溫,要是沒睡,你就出個聲!”
溫流著淚,哪兒敢出聲。
霍斯年忽然低頭湊過來,他親昵的吻著,作輕慢,整個人溫的不像話。
他角是勾起來的,可說出口的話卻沒半分溫度。
他說:“溫,讓他進來?”
猜你喜歡
-
完結2426 章

總裁的嬌寵妻
她本是名門千金,卻一生顛沛流離,被親人找回,卻慘遭毀容,最終被囚禁地下室,受盡折磨,恨極而亡。 夾著滿腔怨恨,重生歸來,鳳凰浴火,涅槃重生。 神秘鑰匙打開異能空間,這一世,她依舊慘遭遺棄,然置之死地而后生,她不會再重蹈覆撤,她要讓那些曾經踐踏過她的人,付出代價。從此以后,醫學界多了一個神秘的少女神醫,商界多了一個神秘鬼才....
243.7萬字8 214071 -
完結303 章

豪門盛寵之陸總寵上癮
他是海城最尊貴的男人,翻手可顛覆海城風雨,卻獨寵她一人。 “陸總,許小姐又有緋聞傳出。” 男人眼睛未抬半分,落下兩字“封殺。” “陸總,許小姐想自己當導演拍新戲。” “投資,她想要天下的星星也給她摘下來。” “陸總,許小姐不愿意結婚。” 男人挑眉抬頭,將女人強行連哄帶騙押到了民政局“女人,玩夠了娛樂圈就乖乖和我結婚,我寵你一世。”
67.5萬字8 27643 -
完結388 章

愛你日久彌深
叢歡只是想找個薪水豐厚一點的兼職,才去當禮儀小姐,不料竟撞見了自家男人陸繹的相親現場。叢歡:陸先生,你這樣追女人是不行的。陸繹謔笑冷諷:比不上你,像你這樣倒追男人的女人,只會讓人看不起。雙份工資打給你,立刻離開,別在這礙眼。叢歡:好好好,我這就走,祝你成功追美、永結同心。陸繹:就這麼將自己心愛的男人拱手讓人,你所謂的愛果然都是假的。叢歡忍無可忍:狗男人,到底想怎樣!
74.5萬字8 578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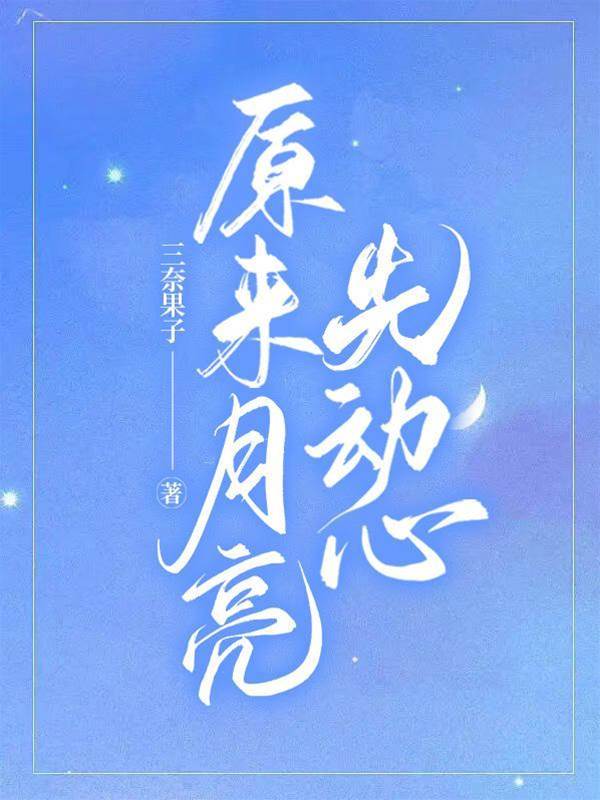
原來月亮先動心
【已簽約出版】原名:《喝醉後,我錯撩了閨蜜的小叔》【蘇撩 甜寵 教授 七歲年齡差 校園 救贖】【蘇撩腹黑小叔X古靈精怪少女】江落是十足的手控,為了一張手照,搭訕了一位帥哥,不料事後發現,對方居然是她閨蜜的小叔!江落腰板挺直,站姿乖巧:“小、小叔好。”……多年後,南大突然傳出生物學係的高嶺之花傅教授已經結婚的謠言。同事:“傅教授,這些謠言都是空穴來風,你別信……”“澄清一下,這不是謠言,”傅紀行冷靜補充,“我確實結婚了。”!!!江落跟傅紀行扯證時,她正讀大四。扯完證回去的路上,男人手裏拿著小本子,溫聲提醒:“喊了我這麼多年的小叔,是不是該換一下稱呼了?”“什、什麼稱呼?”“比如……”男人的吻落在她唇上——“老公。”
21.2萬字8 8278 -
完結506 章

離婚止損
兩人的娃娃親在景嶢這裏根本沒當回事,上學時談了一段張揚且無疾而終的戀愛,迫於家人的壓力,最後還是跟褚汐提了結婚。兩人結婚之後像普通人一樣結婚生女。外人看來雙方感情穩定,家庭和睦,朋友中間的模範夫妻。兩人婚姻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褚汐打小性格溫柔,品學兼優,自從知道自己跟景嶢有娃娃親的時候,就滿心歡喜的等著兩人結婚,總以為兩人一輩子都會這樣在一起。偶然的一天,聽到景嶢用一種意氣風發且張揚的聲音跟自己的母親說他談戀愛了,有喜歡的人,絕對不會娶她。此後再見麵,褚汐保持合適的距離,遇見了合適的人也開始了一段戀愛。兩個人的戀愛結果均以失敗告終,景嶢問她要不要結婚,衝動之下褚汐同意了。衝動之下的婚姻,意外來臨的孩子,丈夫白月光的挑釁,都讓她筋疲力盡。心灰意冷之後提出離婚,再遭拒絕,曆經波折之後達到目的,她以為兩人這輩子的牽掛就剩孩子了。離婚後的景嶢不似她以為的終於能跟白月光再續前緣,而是開始不停的在她麵前找存在感!
99.2萬字8.18 228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