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招惹》 第15章 chapter15
三天後的比賽恰好趕上沉的天氣,看樣子隨時是要下雨,不過這可能更加挑戰選手的專業素質。
比賽按照原計劃進行,許校程到的時候,陳雋已經著裝完畢,人坐進了車裏。
大老遠的,陳雋就看到了許校程,他衝他出大拇指,極為狂傲的勝利手勢。
為什麽整個車隊,許校程最偏陳雋,可能就是喜歡他上這子永不變的狂傲,有種年郎的覺。
許校程看著不遠銀vts裏陳雋的側臉,突然就想到了蘇印。
這種聯想讓他一時間有些猝不及防,等反應過來才曉得,蘇印是陳雋的朋友,他們正在鬧分手,之前往過。
許校程抿著,邁開步子,向賽車那邊走過去,車道的風有些大,吹起了他黑風的角。他表淡漠,走到陳雋麵前,角才帶上了一些笑意。
陳雋降下車窗打招呼:“程哥,放心,一定能拿個冠軍回來。”他一向狂傲,有什麽便說什麽,想要什麽也就說了。
許校程出手,進車窗,重新檢查了他的頭盔等,確定沒問題,才說:“輸贏重要,但安全是最重要的。”
陳雋從頭盔裏出來的眼睛裏麵染上了笑意,說:“曉得了。”
一會兒,又神神道:“這次比賽要是贏了,你們可得幫我一個忙。”
許校程笑笑,應允下來說:“好。”
比賽即將開始,許校程離開了車道,坐回了看臺。
一聲號令響,
賽車猛然一輛輛衝出去,可不一會兒,天空中就下起了雨。
遠遠看過去,銀的vts此時就像一隻剖開雨幕的銀箭一般朝那些紅隔離墩飛馳而去,這是讓人無法相信的速度,很多人目瞪口呆。
短短幾分鍾的時間,賽車之間的距離逐漸拉大,有三輛車在和陳雋的那輛銀vts角逐,漸漸地,剩下兩輛還在一前一後的超越追趕。
Advertisement
最後,隻剩下一輛紅賽車與之角逐。
幾十米的距離轉瞬即逝,而在vts即將撞上第一個隔離墩之前,vts那銀的車準確地切了第一個隙,輕盈地就像一隻翩飛的蝴蝶。輕打方向,練的跟趾作,此時的vts在陳雋的手中就像一位閑庭信步的舞者一般閃轉騰挪。
胎飛逝、水珠飛濺,強大的過彎離心力以及毫沒有降低的車速甚至讓看臺的觀眾產生了某種車即將要飛去的幻覺。
漂移,旋轉,近乎完的作。
賽車突破終點線,穩穩停下。
下一秒,歡呼聲不斷,掌聲雷鳴。
陳雋是冠軍,近乎完的冠軍。比賽幾乎是毫無懸念,陳雋太強了,這場比賽中沒有人能夠和他匹敵。
參賽的隊員都下車,彼此拳,比賽有輸贏,但友誼還是萬歲的。
陳雋摘下頭盔,就提在手裏朝這邊的看臺走過來,對著許校程沈然等人,十分張揚的一句:“看,我就說我是冠軍吧?”
語氣裏麵有些小小的得意。
許校程笑了笑沒說話,表示讚同。
沈然素來拆陳雋的臺,“是啊,是冠軍。但是有一個人你鐵定比不過。”
陳雋臉驀的冷下來,“誰?我會比不過?讓他來和我來一局,看我比不比的過。”
沈然目的達到了,笑的壞。
陳雋去問許校程,“程哥,我是不是最強的”
問完,又轉頭對沈然說:“你不服,就讓那人來和我比,認慫我就是孫子,趕明兒你爸爸。”
沈然占便宜似的應了一句“哎。”
陳雋拿眼斜他。
沈然瞅著陳雋,開口道:“怕是沒機會比了”
陳雋下意識問:“為什麽?”
沈然目飄向一旁的許校程,“賽車手退出賽車界,估計這一輩子都不會再賽車。”
陳雋有些憾的“哦”了一句,將頭盔丟給沈然,人一會兒就跑的沒影了。
沈然把目投向許校程,眉眼帶著笑問:“是不是一輩子都不賽車了?”
許校程看著沈然十分欠揍的臉,隻一句:“無聊。”
_
蘇印果真在t大有個講座,原本是給與設計學院的學生開展的,但是後來改全校開放。
地點在很大的一個禮堂裏,可以容納幾百人的禮堂竟然坐滿了人,站在主席臺看下去,底下都是攢二十歲上下的人頭,略帶青的臉。
講座由原來的四十五分鍾擴展到一個小時,蘇印大多講的是繪畫,最擅長用的用跳躍的筆法表現出變化的效果,極為鮮活的變化讓的山水畫有一種難言的生命活力。
到最後留出來二十分鍾的提問時間,剛開始臺下的一群烏的學生還顯得有些拘謹,問的問題大都是關於繪畫的。
第三排的一個生問:“蘇老師,您是幾歲開始畫畫的”
蘇印答:“四歲。”
剛能拿穩筆的時候就已經拿起畫筆畫畫。
那姑娘又問:“是家裏有繪畫的環境,藝熏陶嗎?比如你親人是也是畫家。”
蘇印握著話筒的手不自然的一,眼睛低垂著,彎彎的睫掩飾了眼睛裏的緒。“沒有親人是畫畫的,我是家裏唯一一個。我父親是警察,母親是……”停頓了片刻,說:“母親是老師。”
主持人控場,打著幽默的語調問:“還有下一個人提問嗎?”
有人舉手,坐在第一排的一個男生,高高的個子,穿著白的衛,滿臉溫和,但問出的問題卻令人咂舌。
他問:“蘇老師在大學時候談過嗎?”
這問題一出,人群裏一陣笑,又是一陣“哇”聲。
二十歲左右的年輕男,對這是頂興趣的。
蘇印看了看底下坐著的人,又看了眼提問的那個男生,他倒是不像來搗的,眼神裏麵都是期待,來認真問問題。
蘇印笑了笑,回答說:“沒有。”
接著說:“我沒上過大學。”
所以自然不存在大學談一說。
一時間底下人議論紛紛,似乎沒想到這個繪畫天才,竟然連大學都沒上過。
固化思維讓他們覺得,厲害的人,至至應該大學畢業吧。
蘇印明白他們的想法,說:“當然,沒去驗大學生活,這一點再現在看來也有些憾。所以你們要努力了,珍惜自己時間。”
話說的客套方,想結束掉這個問題。
可那男生又問:“為什麽啊,沒去大學是有特殊原因嗎?”
這屬於私問題,蘇印可以不答的,主持人也開始巧舌如簧試圖化解問題。
蘇印說:“生活總有那麽一些變故的對不對?”
……
講座還算順利,結束時是下午。
向恒有事去了趟校辦,蘇印一個人慢慢悠悠的逛著校園,等他一起回去。
如果不是這次講座,可能沒這個機會來這裏,當時有講座的時候蘇印還是拒絕的,但現在,深秋季節,銀杏葉子落了一地,微分輕,湖麵波粼粼。這裏的風景還不錯。
蘇印上穿著一件剛才講座時的長,走到外麵才發現有些冷了,將臂彎裏的風套上,雙手兜,沿著湖繼續走。
風景愜意的,偶爾還有三三兩兩的學生路過。
也有手牽手的。
不遠放了個座椅,蘇印走過去坐下來,看風景,也……看人。
職業習慣,不管走到哪裏,喜歡觀察。
對麵斜側的地方有個亭子,後麵栽植的是的叢竹。很好的繪畫素材。
看了一會兒,蘇印又把目移向別。
這一移,才發現這世界有多小。
不遠公用停車場那裏,從車上下來的一個人,是楊舒。
隻是掃了一眼,蘇印別開視線。可視線還來不及移開,就看到副駕駛的車門被推開,一個小小的雕玉琢的孩子跳下來。
一個小男孩,穿著件褐的絨服,孩子十分歡,抱著楊舒的撒。
裏一句句清脆“媽媽”。
楊舒哄著孩子,一手攔著他,一手關車門,牽著孩子往前走,
也看到了蘇印,靜靜地看著座椅這邊,略微有些吃驚,似乎是沒想到蘇印會在這裏。
過了片刻,牽著孩子,朝著朝著蘇印的方向走過來。
一大一小的影慢慢走近,那孩子確實很歡,一路蹦蹦跳跳到蘇印的麵前才安靜下來,也不怕生,盯著蘇印看,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水的,白的小臉,格外可。
楊舒先開口:“你在這裏是……”
蘇印說:“有講座。”
楊舒反應了一會兒,才道:“原來學院的那個講座邀請的是你啊。”約聽別人說過。
蘇印低頭看著孩子。
孩子也在看著,見到漂亮阿姨也不怕生,充滿靈氣的眼睛盯著蘇印瞅。
一張小臉白可,眉眼之間,更像楊舒。
楊舒說:“小象,阿姨。”
孩子立馬乖巧一句:“阿姨~”帶著音。
完倒不好意思了,小小的躲在楊舒後,出圓圓的腦袋來看人。
楊舒說:“今天小象沒人帶,又粘著我,沒辦法就帶來學校了。”
又補了一句:“我在這裏工作。”
蘇印低聲“嗯”了句,客套話向來很說,何況是對著楊舒,這個堂哥之前的朋友,這會兒卻了許校程的妻子,還連孩子都這麽大了。
關係,的有些離譜。
放在兜裏的手機響了,有電話進來,蘇印看了眼,起朝另一邊接電話。
而後楊舒也牽著孩子進了辦公樓。
蘇印聽著電話,回頭看了一眼一大一小的影,蹦蹦跳跳的小孩格外惹人注目,他比照片上還要可一些。
這是許校程的孩子。
電話那頭陳雋還在說:“那明晚約定好了,還是文津會所,你一定要來,我們好好談談。”
“非得談談嗎?”蘇印問。
那頭愣了幾秒,“談談吧,總不能一直拖著,都不甘心。”
到底是誰一直拖著啊,在心裏,這件事已經結束了。
蘇印應下來:“好。”
陳雋心中一喜說:“蘇印,就見一麵,給我一個機會,也給你一個機會。如果真的不適合在一起,那我今後就不纏著你。我發誓。”
蘇印低聲應了一句,“嗯。”
陳雋掛完電話,差點沒蹦起來,按捺著興,又去給沈然打電話,組酒局。
給沈然打完又給許校程打,說:“明天六點有酒局,來不來?”
許校程好像在翻文件,沙沙的響聲,“明晚?”他看了一下時間安排,說“沒時間。”
“程哥,別啊。我明天有重要的事要辦,你帶著嫂子來吧。”陳雋又張,又神。
聽說他有重要的事,許校程應允下來:“好。”
陳雋又叮囑:“別忘了帶著嫂子。”
許校程也應允:“嗯。”
猜你喜歡
-
完結397 章

深情入骨:裴少撩妻套路深
要問蘇筱柔此生最大的幸運是什麼,她會說是結緣裴子靖。那個身份尊貴的青年才俊,把她寵得上天入地,就差豎把梯子讓她上天摘星星。可他偏偏就是不對蘇筱柔說“我愛你”三個字,起先,蘇筱柔以為他是內斂含蓄。直到無意間窺破裴子靖內心的秘密,她才知曉,那不…
112.5萬字8 16872 -
完結623 章

豪門危婚
臨近結婚,一場被算計的緋色交易,她惹上了商業巨子顧成勳,為夫家換來巨額注資。 三年無性婚姻,她耗盡最後的感情,離婚之際,再遭設計入了顧成勳的房,莫名成為出軌的女人。 一夜風情,他說:“離婚吧,跟我。” 她被寵上天,以為他就是她的良人。 她不知道,他的寵愛背後,是她無法忍受的真相。 不幸流產,鮮血刺目,她站在血泊裏微笑著看他:“分手吧,顧成勳。” 他赤紅著雙眼,抱住她,嘶吼:“你做夢!” 顧成勳的心再銅牆鐵壁,裏麵也隻住著一個許如歌,奈何她不知......
103.9萬字8 117371 -
完結1609 章

一胎三寶,爸比好厲害!
因失戀去酒吧的阮沐希睡了酒吧模特,隔日落荒而逃。兩年後,她回國,才發現酒吧模特搖身一變成為帝城隻手遮天、生殺予奪的權勢之王,更是她姑姑的繼子。她卻在國外生下這位大人物的三胞胎,如此大逆不道。傳聞帝城的權勢之王冷血冷情,對誰都不愛。直到某天打開辦公室的門
149.4萬字8 55852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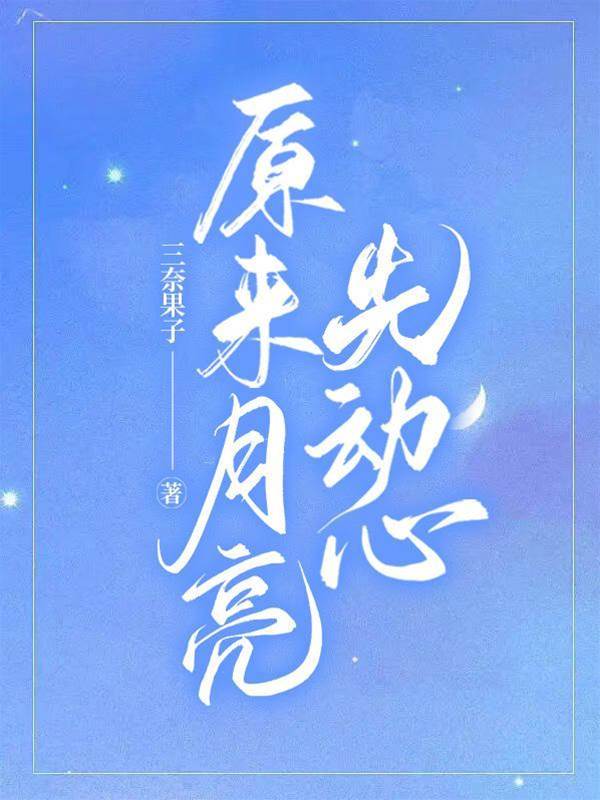
原來月亮先動心
【已簽約出版】原名:《喝醉後,我錯撩了閨蜜的小叔》【蘇撩 甜寵 教授 七歲年齡差 校園 救贖】【蘇撩腹黑小叔X古靈精怪少女】江落是十足的手控,為了一張手照,搭訕了一位帥哥,不料事後發現,對方居然是她閨蜜的小叔!江落腰板挺直,站姿乖巧:“小、小叔好。”……多年後,南大突然傳出生物學係的高嶺之花傅教授已經結婚的謠言。同事:“傅教授,這些謠言都是空穴來風,你別信……”“澄清一下,這不是謠言,”傅紀行冷靜補充,“我確實結婚了。”!!!江落跟傅紀行扯證時,她正讀大四。扯完證回去的路上,男人手裏拿著小本子,溫聲提醒:“喊了我這麼多年的小叔,是不是該換一下稱呼了?”“什、什麼稱呼?”“比如……”男人的吻落在她唇上——“老公。”
21.2萬字8 82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