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她作天作地》 第4章 龍輦(哪家的小孩兒...)
祁瀚帶了些松子回府,誰曉得這東西比瓜子還要難剝。
“殿下!”一旁的小太監驟然驚了一聲。
祁瀚驟然回神,不悅出聲:“何事?”
小太監聲道:“殿下的手……怎麼好像出了?”
祁瀚他一說,這才覺得的疼。
他忙低頭去看。
手指微腫,指裡卡住了一點。
祁瀚眉心隆起,有了些許的惱怒。
他那表妹喜歡的東西,怎麼都這樣麻煩?他堂堂太子,何苦去這樣哄誰?還是該隨便買些東西送到府上去的。
但心念轉來轉去。
祁瀚的面很快又舒展了。
鍾念月看上一眼他的手,還有什麼脾氣發得出來?
他自然沒有一一毫對不起了。
之後可再容不得這般驕縱,隨意使喚他了。
祁瀚吸了口氣:“你們幾個,一起剝。”
小太監苦了臉,死活也想不通這中間到底是哪裡出錯了。
昨個兒還像是要撕破臉就此老死不相往來了,今個兒卻是連帶著他們這些人,都得一塊兒給鍾姑娘剝松子……
這……這什麼事兒啊?!
鍾念月用完早膳,錢嬤嬤已經急得不行了,忙問:“姑娘,我他們備馬車去?”
鍾念月點了下頭,卻是先出聲問了:“我父親和兄長,已經都出府了?”
香桃不明所以地點了點頭:“是呢。老爺一早便應卯去了,大公子這會兒應當也在太學了。”
橫豎全家上下,就鍾念月最懶。
但是毫不見臉紅的。
鍾念月慢條斯理了手,還是由錢嬤嬤和香桃跟在側,一並出了府。
古時候的娛樂對鍾念月來說,實在是乏善可陳。從鍾府到皇宮還有一段不短的距離,乾脆就靠著又打了個盹兒。
Advertisement
香桃醒的時候,正夢見自己穿回去了呢。
“姑娘,到了。”香桃低聲道。
錢嬤嬤也跟著出聲:“咱們得下去走了。”
這會兒外頭響起了聲音:“表姑娘,奴婢已經在這裡恭候許久了。”
那話音落下,簾子被人從外頭卷起來,一張四十來歲正顯乾的面容出現在了眼前。
鍾念月的腦海中很快浮現了與之對應的名字。
這是在惠妃跟前常伺候的宮,人稱一聲“蘭姑姑”。
蘭姑姑請下了車,見了先是一愣。
有些日子不見,這鍾家姑娘倒好像氣更好了?來到皇宮,也不見臉發白了。
蘭姑姑揚起笑容,給一旁的守衛出示了惠妃宮中的宮牌,這才領著們往裡走。
鍾念月抬眸一——
四下寬廣。
這得走上多久啊?
換,也不進宮。
鍾念月穿越前就沒吃過什麼苦,家世不錯,父母恩,長輩也很寵。
倒也不想委屈自己,當下便出聲問:“蘭姑姑,有轎子麼?”
原宮的時候,每回宮,再有什麼脾氣也都老老實實下去了,如鵪鶉一般,自然也不會嫌這路累。
蘭姑姑一頓。
這到了皇宮門前,任是再大的兒,出再好的貴,也得下馬的下馬,下轎的下轎。
宮中只有皇帝、太后和執掌印、六宮的娘娘,才能賞得了轎子。
這巧不巧……
上月還是惠妃管后宮事務,這月便到敬妃了。
蘭姑姑委婉地道:“哪裡好去攪擾敬妃娘娘呢?”
鍾念月聲道:“我這兩日子不大舒坦,走不的。”
蘭姑姑從來沒見過這鍾家姑娘這麼難纏的時候。
誰都曉得傾心太子,在惠妃這個姨母面前,一向都是扮乖做大方的。
蘭姑姑咬咬牙,道:“那姑娘等一等,奴婢派個小太監去向敬妃娘娘請個賞。”
“何苦這樣麻煩?”鍾念月盯著,“你背我罷。”
蘭姑姑聞聲,頓時有些氣上湧,臉上的不可置信之幾乎藏不住。
在惠妃面前得臉,莫說別的,隻說那些份位低的妃嬪,都還要衝賣好呢。
這鍾家姑娘為了向太子示好,為了與姨母更親近,也沒結。今個兒鍾家姑娘怎麼敢這樣同說話了?
“快些。”鍾念月道,“莫讓姨母久等了。”
這話一出,蘭姑姑倒擔不起這個久等之責了,隻好憋悶地在跟前躬下了腰。
鍾念月一拎擺,趴了上去:“走罷。”
錢嬤嬤心中暗暗了聲“老天”。
姑娘近日的脾,怎麼好像狂放了許多?
鍾念月到底年紀還不大,算不得如何沉。但蘭姑姑背著走上一段路,也已經夠要命的了。
大冬天的,蘭姑姑竟是出了一腦門兒的汗。
一旁的小太監都看傻了。
還沒人敢這樣使喚蘭姑姑呢!
就算是惠妃娘娘都對惜得。
從皇宮門口到惠妃宮裡,那距離還當真不短。
得虧尋了個人背。
鍾念月心道。
蘭姑姑走著走著,卻是突然停了,上氣不接下氣地道:“姑娘……且等一等。”
“嗯?”鍾念月將兜帽往下扯了扯。
這會兒太高照,日灑下來,好似為那紅牆綠瓦都披上了一層金。
而這倒並不是最引人注目的。
那遠最扎眼的,是一行緩緩走過的人。
錢嬤嬤與香桃了一眼,就匆匆埋了下頭,本不敢再多看一眼。
那是龍輦。
蘭姑姑心中積蓄著不快,便想著要瞧鍾念月瑟瑟發抖的樣子。
艱難地扭了扭脖子,抬眼一覷,卻見鍾念月神不變,正著那遠,津津有味著呢。
蘭姑姑:“姑娘,那是陛下的行輦,還是莫要胡看了。”
鍾念月:“哦。”
應聲應得相當敷衍。
這四下寬闊,除卻守衛和三兩宮人,隻龍輦一行和他們格外顯眼。
蘭姑姑避讓的時候,那廂也一眼瞧見了他們。
“哪家的小孩兒?倒是蠻。”
說話的是個頭戴金冠,著玄裳的年輕男人。
他倚坐在龍輦之上,發如,眉如墨描,鼻梁高而微薄,生得竟是極為俊,仿佛水墨畫中走出來的人。
他模樣尊貴,周並無凌厲冷銳之氣,但一垂眸,一扶手,自有不怒自威,讓人覺得在他跟前大聲點說話都要本能地。
一旁的大太監孟勝聞聲,這才敢跟著出聲說兩句:“奴婢不認識那是誰家的姑娘,不過背的,那分明是惠妃娘娘宮裡的蘭姑姑。”
他也忍不住暗暗嘀咕呢。
哪兒蠻呢?這膽子大了。
那些王公貴族之後如何驕縱,都是在自個兒家裡,誰敢在皇宮裡,皇帝的眼皮子底下這樣大展驕縱之態呢?
男人淡淡應了聲:“嗯。”
也不知他們是要往何去,眼看著龍輦竟是漸漸近了些。
蘭姑姑這般在宮裡素來風的人,這會兒脖子上的汗都出來了。等再近些,就猛地側,且狼狽地低下了頭,像是生怕多看一眼。
這一倉皇倒好,頭也暈了,眼也花了。蘭姑姑差點將背上的鍾念月摔下去。
鍾念月往上竄了下,一把牢牢抱住蘭姑姑的脖子。
這一抖,兜帽也落了,出兩團微微垂落的發髻,上面一邊別了一團白絨絨的簪。
這是丫鬟心給梳的,方便打盹兒不硌腦袋的發髻。一垂下來,就跟兔子耷下來的耳朵似的。
孟公公見狀心說,年紀還真不大。
瞧著就是個的小姑娘。
這時卻見龍輦上穩坐的男人,斜裡出手,一把拎住了鍾念月的後頸子。
跟拎上月在圍場裡那打中的兔子似的。
鍾念月:?
男人的指骨有力,袖向後去一些,出一截養尊優的如玉石般溫潤的手腕。
蘭姑姑都嚇傻了,想跪又因為背著鍾念月跪不下去,隻哆哆嗦嗦出聲道:“奴婢衝撞了陛下……”
鍾念月也想扭頭去看,奈何後頸子被人揪住了,扭也扭不過去。
實在是可惡!
這看起來分外顯得年輕的男人,正是當今的晉朔帝。
晉朔帝改揪為托,托住鍾念月的後頸,輕輕往前送了送,更好地伏在了蘭姑姑背上,蘭姑姑也順勢站得更穩當了。
只是蘭姑姑那顆心卻依舊七上八下著。
晉朔帝沒有出聲說一句話,那龍輦很快便又繼續往前行去了。
隻孟公公淡淡道了一聲:“慌張什麼?惠妃娘娘宮裡怎麼出了個這麼膽小的?倒不如你背上這位小主子得。”
蘭姑姑囁喏兩下:“是,公公教訓的是。”
這會兒鍾念月才終於扭過了頭。
不過也就瞧了個皇帝的背影,倒是拔如松,氣質出眾。
書中對晉朔帝的著墨不多。
因為太子不敢抬頭看他,主見了他更是嚇得要死。
所以作者有對他的正面直接描寫。
不過大抵、興許……是個可怕的人就是了。
這樣一位牢握皇權的帝王,不可怕才奇怪。
鍾念月的心依舊輕松,就是忍不住反手理了理自己的後領子,小聲道:“將我領子揪皺了。”
蘭姑姑聞聲都再度嚇傻了。
錢嬤嬤也出了一層薄汗。
孟公公卻是愣了下,隨即哭笑不得地瞧了瞧。
這一瞧。
才是又發覺,原來這驕縱的主兒,生得是分外漂亮,眉眼晃人得。
“敢問是哪家姑娘?”孟公公出聲問。
雖說陛下不過那麼隨口一說,但底下做奴婢的,總要聰明些,時刻把那答案準備著。
免得下回陛下再說,誰家的小孩兒,他也只能答上一句不知。
孟公公問起,蘭姑姑哪裡敢不答?
蘭姑姑忙道:“這是鍾家姑娘。”
孟公公又一次愣住了,似是不敢置信地盯著鍾念月多瞧了兩眼,隨後才斂起目,笑道:“原來是鍾大人家的姑娘。”
“去吧,免得娘娘久等。”
如此說完,孟公公才轉過,快步跟上了龍輦。
蘭姑姑長長舒了口氣,頓時有些力,但又怕將鍾念月摔了,一會兒惹出靜,把孟公公再引回來。
孟公公是陛下跟前常伺候的,他的一舉一,難免讓人惶恐,不由得去猜測是否有聖意摻在其中。
這一路上似乎是生怕再出點什麼意外,蘭姑姑憋著一口勁兒,一口氣把人背到了惠妃宮中。
進了門,鍾念月從上下來,頭髮都不見。
宮迎上來,本要按照慣例請先到偏殿洗一二,清爽些,才好見娘娘。
這會兒見了,卻也不免一愣。
那蘭姑姑像是從水裡撈出來的,鍾姑娘卻依舊優雅著呢。
“領路吧。”鍾念月出聲。
宮本能地應了聲,全然沒發覺到,這回宮的鍾姑娘不知不覺就將主權抓在了自己手裡。
惠妃等得都有些不耐了。
與太子一般的子,實則都沒什麼耐。但后宮,這表面上自然更會扮一些。
為了維持一如既往的好姨母的模樣,生等了好久,終於才聽到宮人說,姑娘來了。
“我的月兒,過來讓姨母瞧瞧,是不是病得小臉都白了?”
等人進來,一瞧。
面頰浮著一點緋,氣正好,於是更見眉眼人。
反倒是後頭的蘭姑姑臉蒼白,滿頭大汗,虛弱得像是站不穩。
“奴婢……奴婢向娘娘複命。”
惠妃宮裡誰也沒見過這般狼狽模樣。
惠妃呆了片刻,扣了扣指甲:“……什麼樣子?還不快去梳洗?”
實在丟了的臉。
蘭姑姑點點頭,連多看鍾念月一眼都覺得說不出的嗓子疼頭疼。
匆忙扭退下,小宮走在側,討好地問:“姑姑這是怎麼了?”
蘭姑姑張張又閉上了。
是個得意人,好臉面,往日都是鍾念月結,指著多和太子、惠妃說好話。
哪能說這般模樣是被鍾念月折騰出來的呢?
只能吃個啞虧了。
蘭姑姑恨恨想。
那廂祁瀚好不容易剝了大半松子,跟去了半條命似的。他忍著疲,這才宮。
等到了上書房裡。
高大學士正垂首立在晉朔帝跟前,這人活像隻脖子折了的老公。
等祁瀚到了,他才尋回了聲氣,盯著祁瀚就先問:“太子的手怎麼了?”
祁瀚連頭都不敢抬,就覺著他父皇那目輕飄飄地落在了他的上。
明明也不冷,也不厲,卻就是他渾僵得厲害。
猜你喜歡
-
完結1099 章
鳳女重生:侯爺夫人要複婚!
前世,許瑾瑜將豺狼虎豹當成了良人,闔府被斬首,自己也落得個葬身火海的下場。最後她才知,那個冷心冷情的人將自己愛到了何等地步。重活一世,許瑾瑜想要馬上上了花轎,跟那人和和美美的過完這一生。可是還冇走兩步,就看到了那人,一本正經的說道。“雖家父與叔父早已有言在先,可婚姻大事並非兒戲,既大姑娘不願,我亦是願意就此解除婚約。”許瑾瑜握緊了自己的小拳頭,眼裡起了一層薄霧,直接噠噠噠的走了過去。“侯爺戰功顯赫,為世人敬仰,理應知道流言不可儘信,現如今又怎可因為流言就要解除婚約呢?”孟敬亭冷心冷情,從未對任何人動過心,可是卻被這眼前的小姑娘給軟了心腸。
131.7萬字8 50226 -
完結77 章

奪金枝(重生)
虞莞原本是人人稱羨的皇長子妃,身披鳳命,寵愛加身。 一次小產后,她卻眼睜睜看著夫君薛元清停妻再娶,將他那個惦記了六年的白月光抬進了門。 重活一次,本想安穩到老。卻在父母安排的皇子擇婦的宴會上,不期然撞進一雙清寒眼眸。 虞莞一愣。面前此人龍章鳳姿,通身氣度。卻是上輩子與薛元清奪嫡時的死敵——模樣清冷、脾氣孤拐的的薛晏清。 迎上他的雙目,她打了個哆嗦,卻意外聽到他的一句:“虞小姐……可是不愿嫁我?” - 陰差陽錯,她被指給了薛晏清,成了上輩子夫君弟弟的新娘。 虞莞跪于殿下,平靜接了賜婚的旨意。 云鬢鴉發,細腰窈窕。 而在她不知道的上輩子光景里—— 她是自己的長嫂,薛晏清只能在家宴時遠遠地看她一眼。 再走上前,壓抑住眼中情動,輕輕喚一句:“嫂嫂。” 【又冷又甜薄荷糖系女主x內心戲起飛寡言悶騷男主】 1V1,男女主SC 一些閱讀提示:前期節奏有些慢熱/女主上輩子非C,介意慎入 一句話簡介:假高冷他暗戀成真。 立意: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20.2萬字8 39694 -
完結139 章
我以為我拿的救贖劇本
一朝穿越,虞闕成了修真文為女主換靈根的容器。好消息是現在靈根還在自己身上,壞消息是她正和女主爭一個大門派的入門資格,她的渣爹陰沉沉地看著她。虞闕為了活命,當機立斷茍進了一個不知名的小門派。入門后她才發現,她以為的小宗門,連師姐養的狗都比她強…
62.6萬字8.33 16859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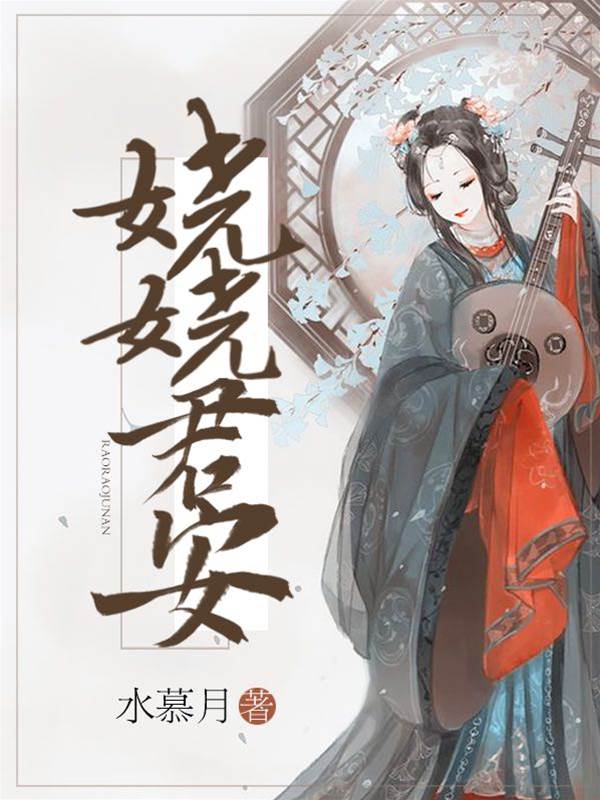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