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魚陷落》 6
“隨便打打”。
白楚年:“giao,這你起的隊名?”
蘭波指了指屏幕上的語音條,剛剛他在領名牌的時候,自助場機要求語音輸隊名,那時候白楚年剛好在旁邊說“隨便打打嘛。”系統自識別了前四個字。
陸言邊套隊服邊過來領名牌,順口問:“我們隊伍什麼名字?”
白楚年攥著名牌藏到背后:“呃……”
atwl考試場地遼闊,場地分十個區,以希臘數字一到十作為標號。
口安檢極為嚴格和繁瑣,每個人都必須經過黑箱全掃描,以檢查是否嵌有武金屬,之后要逐個驗,確定本人未注興劑和腺供能類藥。
白楚年四人小隊被隨機分第十區,監考人員依次為他們戴上一副形眼鏡,引導四人分別進類似獨立電話亭的小隔間。
白楚年再睜開眼睛,發覺自己已經在一間陌生臥室中,他蹲下來了腳下踩的木制地板,的確是木頭。
臥室里有一面落地鏡,白楚年看看鏡中穿著黑武裝隊服的自己,再看看自己的雙手,均無異樣。
他嘗試著對著鏡子把眼睛里的形眼鏡摳出來,鏡片摳出來的一瞬間,周圍的一切都恢復了原樣,還是剛剛工作人員領他們進來的小隔間考場。
突然,自己所在的隔間亮起紅燈,刺耳的警報把監考人員招了過來,監考不耐煩地拿出一片新的形眼鏡給白楚年戴上,并且嚴肅警告白楚年再犯規一次就按擾考場秩序理。
重新戴上眼鏡的白楚年再一次回到了剛剛所見的那個臥室。
“哎呀?”白楚年愣了一下,看著自己的雙手,攥了攥拳,“我……實形vr,這考試這麼先進的嗎?”
Advertisement
他嘗試著走了幾步,從臥室走到臺,再從臺走到客廳,坐在的沙發上和冰涼的地板上,和現實世界沒有任何區別。
仔細照了照鏡子,發現上的黑隊服不僅掛著一枚印著“隨便打打”隊名的亞克力牌,腰間多了一條有十個金屬凹槽的腰帶,前還嵌著一條二十厘米長的橡膠管,管注滿了紅。
白楚年打開窗戶向四周了,自己一座普通居民小區,周圍都是外觀相同的居民樓,有人在臺曬服,樓下還有遛狗的老太太站在一起聊天。
看來這個考試不僅模擬戰場,還完全復制了現實世界的況,估計傷害到這些普通人還會扣分。
有點意思。
白楚年沒有貿然走出房子,而是在各個角落仔細搜尋了一番,在電視櫥屜里找到了一張地圖和一個圓形紐扣小零件。
“考生您好!”
突如其來的一聲電子音廣播讓白楚年嚇了一跳,仰頭看了看天花板上的音響。
“歡迎參加高級團隊作戰等級考試,下面播報考試規則——”
“本次您選到的地圖為【城市】,考試時間48小時,在考試中請勿摘下模擬眼鏡,否則以棄考理。”
“考生前紅條為模擬量條,擊時由系統計算傷害,量條清空時考生當即淘汰,場地彈藥箱會放置恢復針劑,避免擁有恢復類分化能力的考生惡意打消耗戰影響考試公平。”
“為避免考生消極避戰,考生腰部均裝有一條炸彈帶,每隔一小時自落一枚阻,阻全部落后腰帶自,考生當即淘汰。”
“每個考生需要完三個隨機任務,結算績時,功存活48小時,績評為三星,四人小隊最終只需有一人存活則視為全隊存活,在此基礎上個人每功完一項任務則個人評級追加一星,滿編隊存活通過時,所有隊員評級加一星,每擊敗十名對手考生,績加一星。”
白楚年邊聽邊計算,活到最后能得三顆星,完三個任務得三顆星,全隊都活著再加一星,也就是說這考試在完全不打別人的況下,最高績是七顆星,那按錦叔的意思,不能太出風頭,又得拿個好績,所以讓那只小兔子拿個五或六星就可以。
“考生所在房間有一張任務書,任務書背面為【城市】地圖,地圖上標有固定彈藥箱位置,彈藥箱隨機放置槍械、近戰武、恢復針劑、阻等資。”
“考生所在房間有一枚阻,請在十分鐘找到并安裝在腰帶凹槽,否則將直接自淘汰。”
“考試開始。”
白楚年掂了掂手里的圓形金屬紐扣,按進了腰帶凹槽中,腰帶扣亮了一下,顯示炸倒計時一小時。
“嘖,弄得我還張……”白楚年了手,這考試容聽著有點難啊,得盡快找到隊友,再晚估計要死了。
他沒有走門,一腳踹開窗口的防盜欄,雙手扣窗框上沿,僅憑手臂力量翻上遮雨棚,攀著引流排水管飛快爬上樓頂,將整座城市一覽無余。
果然同隊隊員相距并不遠,白楚年俯視周圍,很快找到了蘭波。
很明顯廣播播報考試規則時蘭波本沒聽,此時正趴在噴泉水池里用尾掃水玩,白楚年銳利地捕捉到花壇外一閃而過的黑影,兩個穿紅隊服的alpha佩戴著“死刑犯”隊伍名牌,各拿一把戰匕首,緩緩接近蘭波,襲意圖明顯,大家都想要人頭分。
匕首寒乍現,兩個alpha配合默契,同時從左右方向夾擊蘭波,一個攻擊蘭波下腹,另一個直接背后鎖一刀斃命。
水可以傳遞地面的震,蘭波察覺到危險靠近,本能促使他瞬間躍出水面,藍半明魚尾頓時蓄滿電。
“魚……?人魚?!”
蘭波從高空俯沖落地,單手扣住alpha的鎖骨,細長手指扣進了alpha中,利用慣將自己的向空中一,纖細的小臂從背后直接勒斷了alpha的頸骨。
那人前的量條立刻清空,蘭波順手奪下尸手中的戰匕首,長尾纏繞在背后的alpha脖頸上,用力朝天一甩,alpha慘著被拋到高空,下落時毫無還手之力,被蘭波的匕首輕易穿后心,量條同時清空至零。
蘭波將金發掖到耳后,從尸上出鮮淋漓的戰匕首,在手中一拋,一拋。黑戰斗服前的電子數字從“0”跳了“2”。
城市上空廣播隨即播報:
“【隨便打打】蘭波 擊殺【死刑犯】鄭糾。”
“【隨便打打】蘭波 擊殺【死刑犯】莫非。”
第7章
“別。”
白楚年起噴泉池中的水幫蘭波洗凈臉頰和上的跡,把他手里的戰匕首拿過來在自己隊服的武裝帶上,從兩尸腰帶上摳下兩枚阻,迅速安裝到蘭波的腰帶上,自倒計時才從一分零九秒增加至兩個小時。
蘭波坐在噴泉的大理石外圍,半瞇眼睛仰著頭,浸的金發緩慢滴水,水滴消失在脖頸裹纏的繃帶中。
他剛剛結束了一場戰斗,腺外溢量信息素,上依稀殘留著白刺玫淡香。
原本想罵這條魚不服從指揮,可嗅著這悉溫馨的信息素氣味,白楚年像到安一般,輕輕了蘭波的頭發,蹲下來細細地為他講了一遍規則。
“我讓你打架才能打,其余時候找個沒人的角落坐著發呆就可以了。”
蘭波抿著思考,很努力地張了張:“a。”
白楚年煩惱地了頭發,幫兔子拿個五六星很簡單,但如何防止蘭波拿到七星以上是個大問題。
煩惱這事兒的同時,白楚年忽然發覺蘭波的發音比之前清晰了不。
“你跟我說,白,楚,年。”
“bai……”
“白楚年。”
“bai shu……ni……”
“算了換個簡單的,楚哥。”
“chu chu……”
“楚哥。”
“楚……ge……哥。”
“乖,多練。”
幾分鐘后,陸言和畢攬星到達噴泉與二人會合,分別攤開自己的任務書,放在一起對照,看有沒有容相似的任務可以一起完節省時間。
猜你喜歡
-
完結434 章

離婚後冷她三年的陸總膝蓋跪穿了
【誤會賭氣離婚、追妻火葬場、豪門團寵、真千金微馬甲】確診胃癌晚期那天,白月光發來一份孕檢報告單。單向奔赴的三年婚姻,顧星蠻把自己活成一個笑話。民政局離婚那天,陸司野不屑冷嘲,“顧星蠻,我等著你回來求我!”兩個月後——有人看見陸司野提著一雙小白鞋緊跟在顧星蠻身後,低聲下氣的哄:“蠻蠻,身體重要,我們換平底鞋吧?”顧星蠻:滾!陸司野:我幫你把鞋換了再滾~吃瓜群眾:陸總,你臉掉了!
43.2萬字8 210740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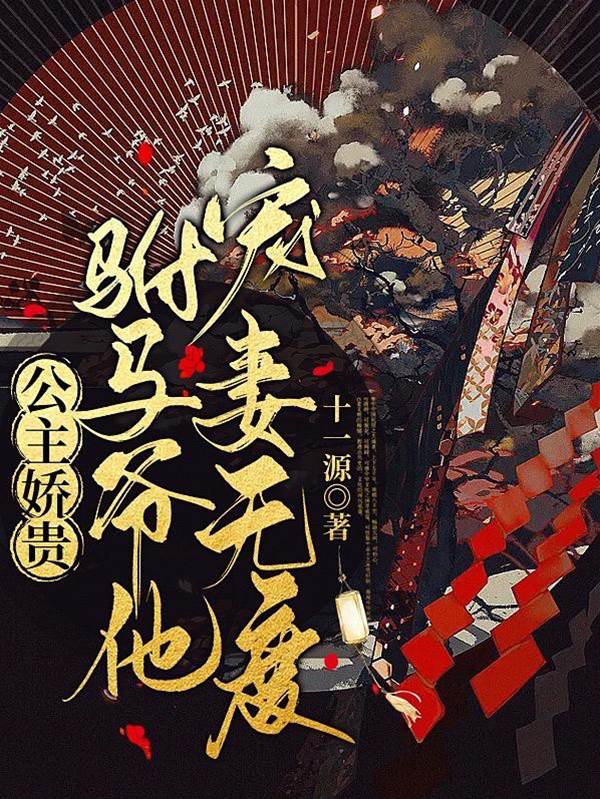
公主嬌貴,駙馬爺他寵妻無度
【1v1 、甜寵、雙潔、寵妻】她是眾星捧月的小公主,他是被父拋棄的世子爺。幼時的他,寡言少語,活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是小公主一點一點將他拉出了那個萬丈深淵!日子一天天過,他成了溫文儒雅的翩翩公子,成了眾貴女眼中可望不可及的鎮北王世子。可是無人知曉,他所有的改變隻是為了心中的那個小祖宗!一開始,他隻是單純的想要好好保護那個小太陽,再後來,他無意知曉小公主心中有了心儀之人,他再也裝不下去了!把人緊緊擁在懷裏,克製又討好道:南南,不要喜歡別人好不好?小公主震驚!原來他也心悅自己!小公主心想:還等什麼?不能讓自己的駙馬跑了,趕緊請父皇下旨賜婚!……話說,小公主從小就有一個煩惱:要怎麼讓湛哥哥喜歡自己?(甜寵文,很寵很寵,宮鬥宅鬥少,女主嬌貴可愛,非女強!全文走輕鬆甜寵路線!)
21.6萬字8 12884 -
完結380 章

插翅難逃之督軍請自重
她,是為姐姐替罪的女犯。他,是殺伐果決、令人生畏的督軍。相遇的那一刻起,兩人命運便交織在了一起。顧崇錦從來沒想過,一個女人竟然成為了他最大的弱點。而偏偏那個女人,卻一心隻想逃離他。宋沐笙也沒有料到,一心隻想保護姐姐的她,早已成為了男人的獵物。他近乎瘋狂,讓她痛苦不堪。為了留住她,他不顧一切,甚至故意讓她懷上了他的孩子,可誰知她居然帶著孩子一起失蹤......她以為她是恨他的,可見到他一身軍裝被血染紅時,她的心幾乎要痛到無法跳動。那一刻她意識到,她已經陷阱這個男人精心為她編織的網裏,再也出不來......
64.9萬字8.18 8586 -
完結488 章

醫妃兇猛,帶著殘王風風火火搶天下
特種部隊軍醫的莫云茱穿越成將軍府大小姐,原本要做太子妃的她被陷害后捆綁病嬌殘王。女主強勢破陰謀,帶著腹黑病夫君開啟虐渣打臉模式,斗奇葩,撕白蓮,踩綠婊,搞生意,財運滾滾來,桃花朵朵開。一不小心,名滿天下,不料離奇身世暴露,仇家蜂擁而來,既然有人不讓她躺平,那她就帶著美人夫君奪了這天下又何妨!
87.4萬字8.18 14789 -
完結73 章

致命解藥
謝錢淺十歲那年被送去沈家,老太爺對謝家這個女娃娃甚是喜歡,當場決定讓沈家兒女好好養她,以後就是沈家孫媳。 老太爺放完話沒多久蹬腿了,那麼問題來了,沈家孫子有三個,她是哪家孫媳? 那年,謝錢淺平xiong,個矮,瘦骨伶仃,沈家二孫和三孫每天以捉弄她爲樂。 只有沈致在他們鬧得過分時,默默往她身後一站,嚇退衆人。 幾年後,謝錢淺被養得越發明豔動人,玲瓏有致。 就在沈家二孫和三孫爭得頭破血流之際, 遠在外國的長孫沈致突然歸國,將謝錢淺單手一抱放在沈家廳堂老太爺的遺像前,俯身問她:“什麼時候嫁我?” 謝錢淺瞄着遺像中老太爺迷之微笑,心頭髮毛地說:“內個,我還沒到法定年齡。” 沈致淡然一笑:“三天後是你二十歲生日,我會再問你。”
27.3萬字8.18 731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